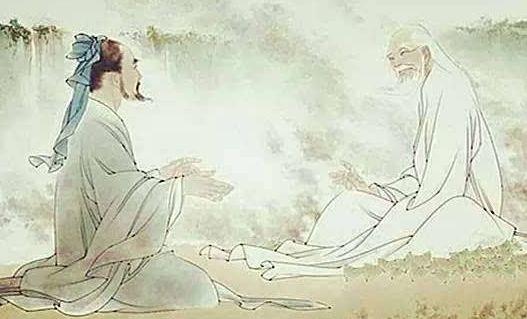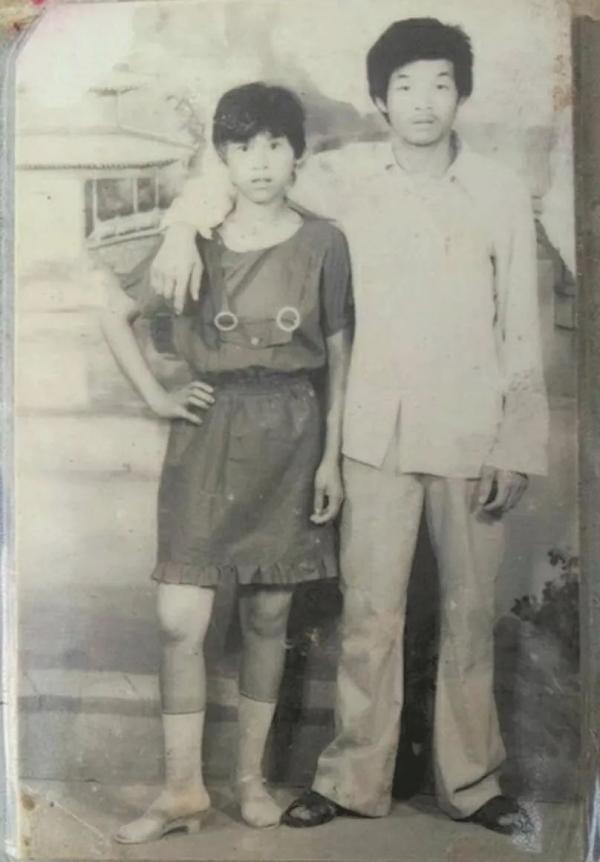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王风.彼黍》
[黍:黄米。谡:粟。靡靡:走路缓慢徘徊的样子。摇摇:心神摇晃。噎:梗阻,不能呼吸。]
诗好解。
稻菽成行,风吹麦浪。蔓草在傍,行于陇上。
今我漫游,踯躅蹀躞。心有所思,神有所涣。
人群中,会有那么一个群体,性格有差,身份迥异,彼此生活命运也没有交集。然而会产生一种类似的共感。
这种感觉,在怒马鲜衣,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时代,是不会真正明白的。哪怕天赋再颖悟,才华横溢,或者所谓天生“忧郁深沉”的气质。
只有黎明晨昏地熬过一些岁月,起起落落经过一些事情,眼光从自身往周边四维,上上下下的看一看。等哪一天心有一个广阔世界,而做事平常,与人淡语话桑麻,风来了紧一紧衣服,该吃饭吃饭的那个时候。才可能,真正地,仔细听一听,听出一点不带怨气和油腻的厚度。
像新焙出的好茶,摆在时空的维度里经过一些自然的变化,消一消烟火气。熬出来的茶汁,入口下喉,酸度适宜,辅舌生津。吞之一团凝聚不散,细品无迹可寻,只有微微的汗意沿脊椎上行,两腋清凉,五脏暖,眼神明。
但前提是,茶质要好,人的境界或感受,也得具备能提炼的素质才行。
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一只千年的老龟,无法跟朝生暮死的蜉蝣,解释清楚,天地之间还有季节这回事。
懂的人会懂,不懂的人,时机未到,就不用霸蛮去解释了。
急什么呢。解释清楚能证明什么呢?想做的事做就是,想去的地方去就是。一个人在别人嘴里的样子,在别人心里的样子,远没有自己跟自己能交代得过去,来得重要。
所谓想帮助别人,这个心理投射也要适可而止。你不能改造任何人,让他满足你心里的期待,那是一种控制。即使出于良好的愿望,即是没有什么私心杂念,注意,想让别人“好”,也是你心目中的那种版本。
削足适履,强迫人家穿上水晶鞋。人家的脚趾流着血裹着布,而你在欣赏“步步生莲”,欣慰自己的三寸小鞋又卖出去一双。
有尊重,有自由,再奢谈帮助。控制自以为是上帝的自以为是,才有资格谈明智。
心流理论,是心理学家米哈里·齐克森米哈赖,在观察了艺术家,棋手,攀岩者,各种普通职业而乐在其中的普通人……经过研究之后提出来的。
心流的定义,就是一种将个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换句话说,心流,就是人在海量资讯中,经过自我训练,将专注力运用在某一点上,产生的洪流感受,高原体验。
心流是一种体验心理学,这种感受我们称之为“精神负墒”。“墒”是物理上的无序。宇宙中所有的运动,如果不加干涉,都会往散乱的方向行进,杂乱无章,就是“墒”。而“负墒”,是逆流而上。
类似于儒家的“慎独”,道家的“虚室生白”,
佛家的“成住坏空”,禅修的“禅那”。
而任何一种长期专注到“忘我”的活动,都可能获得这种体验。比如,阅读,写作,绘画,烹饪,园艺,研究,远足……
体验过了,就懂。
在这个过程里,自己徘徊感悟,而他者看起来,投射出种种猜测,又有什么关系?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不患人之不知,患己不知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