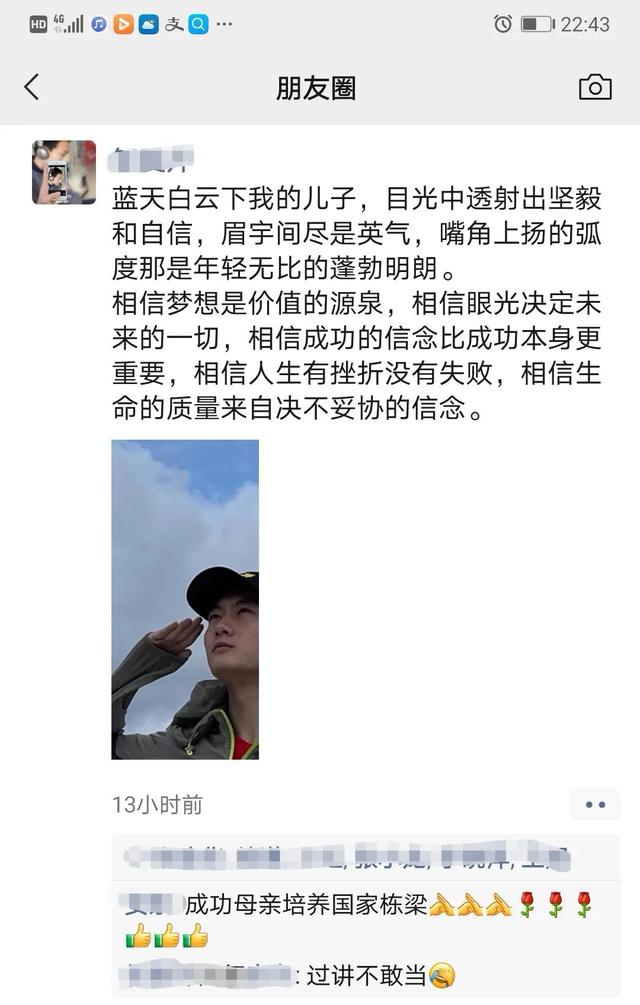回味大学寝室里的每一小片时光,都心动怦然。

刚认识的六位室友,集资买了一个木座温度计,它在寝室的墙上一挂就是四年。1982年毕业离校前,同学义烈请求收藏,并让我们五人在背面签名。
回味大学寝室里的每一小片时光,都心动怦然。斗室中个个精英,虽根植于同一国度,但来路有别、年岁不一,他们天性中的斑斓光芒,曾让我目迷五色。
床位的安排,是辅导员事先定好的,报到那日,毫无纷争。六个床客支起六顶蚊帐,同窗之谊开启序章。时长四年,彼此间不自觉的精神探入,缓慢而深刻。
囿于篇幅,我只能先拿义烈说事。
来自江西的义烈,有个令人吃惊的本事,你请他看一篇万把字的习作,一年半载后,他竟能整段背诵出原文。唐诗宋词、千古名篇,只有你说不出来,没有他不知道的。义烈在文字上的默记才能,如有神助,遍数中文系,似无出其右。
1978年入学时,义烈已过三十,谢顶多年,看上去要持重一些,但他又是个分分钟会羞涩的主,为本班老三届中仅存的单身。义烈以那年江西省高考文科总分前四,入读本校中文系78级。
老天爷让义烈具备某项天赋,也给了他几样恶毒的缺点,比如,他的平脚板。这样一个腼腆的人,走起路来,肩膀左晃右摆,一副狠三狠四的样子,和他内心如履薄冰的调性,完全撕裂。
义烈的父亲早早病故,全家由九江市区迁入庐山一带村落,母亲也从城市女眷,变一介村妇。义烈六岁上学,去学校的路上,背个竹篓,回家带回满满的猪草。后在庐山中学住读,周末仍不忘背回猪草一篓。来来回回的上学路上,年年岁岁的山间盘旋,义烈默诵着形形色色的古诗古文,用以打发行路的寂寞。
斯文如义烈,三餐不离剧辣。每次寒暑假回来,都会从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灰色人造革旅行袋里,捧出一个二十多厘米高的广口瓶,里面是满满的泡菜,一律以赣州的小米椒腌制。一截相貌老实的白萝卜,我只轻轻一咬,就像在嘴里点着了一只电光鞭炮,半边脸颊由内而外早已麻木。那种具有超级渗透力的剧辣,对我的味蕾,是一次丧心病狂的施虐。很有趣,本室垂涎者五名,是排好队凑上去领教九江泡菜的。真是五个贱骨头啊,只在瞬间,室内大乱,咳呛、捶胸顿足,五个人同时嘴上不停地呸呸呸和嘶嘶嘶,泪眼相对,不知南北。眼看着我等被辣翻,义烈煞有介事地很男人起来,笃定地双手一摊,风风凉凉地说,人家吃了几十年了,平常的东西嘛!

班副老高相貌堂堂,是鲁西南版高仓健。他的铺位在我头上,入校前是菏泽的一位村支书。他喜欢在蚊帐中捧读,穿着宽大的花布裤衩,双腿插进印满牡丹朵朵的棉被里,“梁山”牌卷烟一夜半包。高支书的蚊帐,入学三月已然熏黑,在五顶白色蚊帐的包围下,特别醒目。而那时,人们对尼古丁比现在要宽容。冬日凌晨,从上位的蚊帐里,会伸出一截热烘烘的玉臂,怒而不言地在黑暗中推开气窗,将满室烟气导向室外。这条玉臂,是义烈的,他绝不放弃对自己的爱惜。每天气窗哐当一响,便是凌晨四点。
记得,有次现代文学课期末考试,让大家当堂就文学史中的一位著名女性形象,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短评,比如祥林嫂、瑞珏等。考试后,老师要做一次评卷分析。那天,四个班在一起上课,老师请义烈站了起来,问道:这次考试,你是唯一选了没有编入现代文学史的小说人物,作为分析对象。你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义烈低着头,耳根热红,声音含糊,说,老师,1942年,属于现代文学史的时间范畴吧,我们所能看到的现代文学史,略去很多著名的民国小说,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老师不易被察觉地愣了一下,老练地避开了义烈设的辩论陷阱,说:那天你是在认真答卷吗?义烈说,是的,我认真到,连及格不及格,都不在乎了。
老师微笑着说:那你觉得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成绩呢?义烈嘟囔地说:除了优秀,还能是什么呢?大家都笑了,甚至有人鼓掌。
那次考试,义烈鬼使神差地谈了周天籁写的《亭子间嫂嫂》中女主人公的形象,这部民国时期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两位风尘女子的生存状态。我再次看到该书名,是二十年后,电影导演彭小莲在一篇随笔中提及,复旦贾植芳教授曾向她推荐过此书。
试卷发下后,义烈把试卷塞进书包,低着头,不回复同学对他成绩的询问。直到三十多年后,本寝室同学来我家聚会,大家再次问起,义烈用食指蘸着白酒,在餐桌上,写了一个字:优。
义烈的不世故,市面上已少见,大学毕业后,义烈分在九江一所院校教授古文。他简化了人际关系,日常活动宽度,仅到实用的边界。他为自己选择了隐沦的生活。

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庆典,各地同学从四处赶来上海,义烈是带着使命来的。本班同学聚会,筵开三席。义烈无心饮食,双眼一直锁定在任一家大出版社社长的同学身上。义烈终于站了起来,向社长边上的一个空位走去,迟了一拍,座位被占,他窘迫地在原地打转,不知所措,勉强找到隔开社长两三人的一个位置坐下,等着说话机会,他手上还有个塑料袋。
时间起码过去了十五分钟,交际手段僵硬的义烈,无计可施地坐等着,一点都插不上话。他的犹豫不决让我心酸,我不得不走到社长跟前,把他请到义烈边上,让他们单独在一边聊了起来。我看见义烈拿出一袋皱巴巴的庐山茶叶,社长极为明智地收下了,义烈又拿出了一包文稿,社长也收下了。我移开目光,不让义烈发现我在看他。
一周后,社长把我叫到他在福州路的办公室,把义烈的作品给我看,是类似箴言录格式的文字,确实缺乏卖点,义烈和市面的互动,已经几乎没有。社长说,由你转寄,帮我宽慰几句。我将原稿和社长所赠的一册精装版《叔本华哲言录》寄给了义烈。
约二十天后,一个快递纸箱出现在我面前,是义烈寄的,里面是二十本自费印刷的简易读本,书名是《感思录》。他把那个退稿印成了小册子,让我在同学中传发,真够执拗的。
义烈终身未娶,当年,我曾对他说,你或许没有恋爱的能力吧。他脸红了,并没有反对。
毕业后,两地相隔,来往有限。几年前,义烈在家中突发心梗离世,被学生发现,已是七日之后。查了一下,在那几日内,我是给他打过两次电话的,他应该就在铃声边上。
那只破旧的木座温度计,当时仍挂在他修葺一新的教授公寓里,我们寝室五人的名字,静静排列在义烈告别人世的地方。(邬峭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