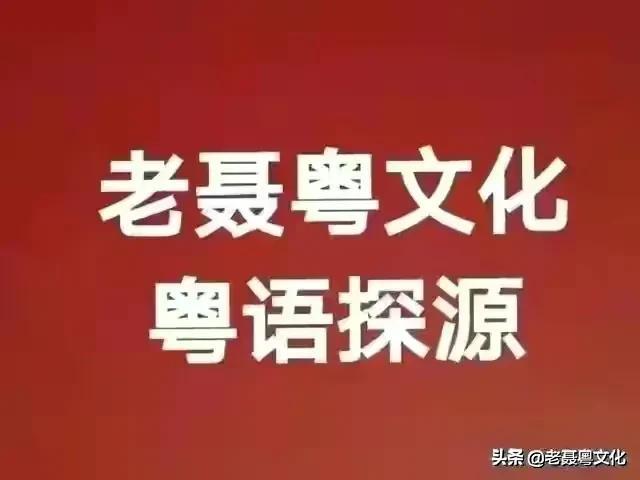1899年,甲骨文“从天而降”!
但是甲骨文的定义却很难给出,《辞海》在“甲骨文”条目下的解释是:
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
第一句话问题不大,但是第二句话却有很大的问题,一是“都是”这两个字的强调,二是确认了甲骨文的功能是“占卜”。占卜是指根据人工干预所形成的现象来预测凶吉祸福的自古至今都普遍存在着的人类活动。神并不存在,绝大部分的人在绝大部分的时候是这么认识的。人类存在占卜活动,是因为对不可知不可控的未来的严重关切。满足人类这种关切未来的需要,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就是被认为能够沟通神意的人——巫。
甲骨文是怎样变成“卜辞”的?
在普通人的知识体系中,往往认为远古的人更容易迷信,因为古人驾驭自然的能力有限,所以把占卜当作重要的决策手段,同时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抚慰。有人甚至认为一个政权掌握者,一个领袖都会去以占卜作为行事的手段。这样,商朝的人,甚至朝廷的主宰——商王(帝),也是必须占卜的。
1908年罗振玉发现了甲骨文出产地之后,由于缺乏政府保护,甲骨文开始更大规模地流向民间,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发掘现场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利益驱使,农民们纷纷以锄头上马,在自家田地和院落中大举挖掘,所得甲骨“往往盈数车”。

罗振玉(1866—1940年),浙江上虞人。曾任清廷学部参事及京师大学堂农科
监督,后又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他是近代金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甲骨四堂”之一。
全国的古董商人,包括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一些学者或古董商人,都加入到搜求甲骨的大军中。据胡厚宣和李济的分别统计,1899年至1928年,私掘且流向民间的甲骨数量高达10万片。这10万片甲骨虽然有不少著录出版,但大部分未能著录,且今日不知何所终,几乎所有甲骨都没有地层关系信息、出土位置信息,就更谈不上考古发掘报告了,给甲骨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这种局面在1928年彻底结束。
当时,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正负责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派遣董作宾考察小屯,董作宾迅速给出了明确结论——甲骨挖掘确犹未尽,且痛陈:“长此以往,关系吾国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之世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1928年,对于甲骨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捩,其功臣就是董作宾,董氏也将甲骨学作为其毕生投入的学问,是甲骨文研究者中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学者,当然,也是受到诘难最多的学者。

董作宾(1895—1963年),河南南阳人。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在考古学、殷商史、文字学、书法及篆刻艺术等方面颇有贡献。
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组织了15次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果丰硕。
获得甲骨25000片(其中著名的YH127坑,一坑出土甲片达17000余片、完整龟板300余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殷墟的发掘,中国终于引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甲骨片的出土已经与其他的相关考古发掘形成一个整体,甲骨文的研究也摆脱了古文字学的范畴,而成为甲骨学。

中书汇游学团参观殷墟
这一时期,甲骨学成为一门时尚学问,人才济济,为数不少的研究者还具备了西学修养,创造性的认识层出不穷,堪称甲骨学的黄金时代。董作宾、郭沫若、唐兰、商承祚、容庚、陈梦家、胡厚宣,成为这一时期甲骨学者的代表。
1937年至1949年,战争使得国人自主的科学发掘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的春天,中科院考古所(后转入社科院)即展开了新的科学发掘。最大批量的收获分别是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和1991年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出土。建国以来,共出土甲骨6000多片,其中有字的完整甲骨400多片。另外,新中国在殷墟以外的其他地方还发掘出商代甲骨,并且,还发现了早于和晚于商代的甲骨。
甲骨文研究也持续深入。
首先是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册从1979年到1982年间陆续出版,与其配套的释文和材料来源表也先后出版。而事实上,这部采用董作宾五期分类说编排的著录,也许隐藏了潜在的问题,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分期是合理的甚至是正确的。其他一些大型字典、类书也纷纷出版,比如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这些集大成的甲骨文巨制在80年代前后的集中问世,标志着甲骨文基础研究的逐步淡出。因为很显然,人们已经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句式、文法、习卜、甲骨学史等方面。当然,考释文字还是兴奋点,只是令人兴奋的发现越来越少,或者说,当一个体系稳固之后,这个体系的“掌门人”已经没有能力接纳所谓的新发现。
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后,甲骨学虽由私学转换为公学,但已经由一门“显学”转化为一门“绝学”,问津者逐步减少,老学者纷纷谢世,不少资深学者也退出此研究领域,转向其他更容易说清楚、有成果、有用的、能够商业化的领域,甲骨文专家变身为青铜器专家的李学勤先生即为一例。
甲骨文是怎样一直被当作“卜辞”的?
• 第一,确实有占卜痕迹和典籍记载的文献根据。
当人们发现了大量的出土甲骨后,结合《周礼》、《左传》的典籍记载,就认定甲骨上的痕迹应当是占卜的痕迹,再参以《史记》中对占卜技术的详尽记载(太史公有《龟策列传》,但有录无文,文为唐人补记),进一步证实甲骨文就是商代帝王占卜的记录。
• 第二,没有形成科学的研究体系,甲骨学先天营养不良。
即使考古发现了商以前的卜骨(这也很难说,因为占卜这种行为很多元化,不能看见一根有钻凿烧灼痕迹的骨头就断定这是古人的占卜行为遗迹),周代以后又有占卜的典籍记载,也无法断然下结论,甲骨文就是卜辞,因为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
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讲甲骨学界已经具备科学思维体系和科学方法体系,遑论甲骨学早期阶段。早期建立起的非科学体系,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甲骨学,以至于后来无法撼动业已形成的框架。

• 首先,早期的甲骨文研究仅被当作文字考据之学,仅被当作私学。
• 其次,早期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缺乏现代科学支撑。

王国维(1877—1927年),浙江海宁人,号观堂。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由于对甲骨文研究的重大贡献,与罗振玉(雪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并称“甲骨四堂”。
相当多的早期研究者,对古文字学浸淫深厚,或者说,当时释读甲骨文,就是古文字学家的事情。面对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他们所能使用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字形类比法,也就是调动大脑中、书本中储备的《说文》小篆和两周大篆,来比照甲骨文的字形,从而考释甲骨文。这种考释方法当然在很多场合都会生效,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大前提,甲骨文字是先秦汉字的源或者至少是上游,它们之间应该有形体上的一致性或者相关性,至少在造字方面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或者相关性。
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文字使用场合、文字载体、书写工具的截然不同,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很难呈现,相关性也隐含模糊。事实上,甲骨文与小篆相比,少有形体一致者,即使与两周大篆甚至商鼎短铭相比,也很少有形体一致的。因此,用形体类比法释读甲骨文,必然有疏漏。如果疏漏出现在关键位置就问题大了。
比如,因为金文中的“卜”与甲骨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卜”字形体较像,故将其认定为“卜”,假如是错的呢?我们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吗?再比如“贞”,如果不是“贞”而是“鼎”呢?甲骨文字的传统辨识体系恐怕就会因为这两个字的误读而垮掉。因此,字形类比法是一个起点或者契机,它可以引导出假设,但绝不是系统的、科学的方法。甲骨文最早被认定为商王卜辞,也许就是因为早期学者用字形类比法认出了“王”与“卜”这两个字,再后来,就很少有人怀疑这两个字。于是,商王卜辞的大轮廓、大语境就顺理成章而少有人怀疑了。再次,陈陈相因的师承关系
在中国,学生推翻导师的学术体系,很罕见,他们能做的往往是阐发和维护、最多是完善导师的学术体系。师徒相授是其时私学乃至公学的基本路数。到了今天,学生更要维护师承关系,因为,你不维护,就不能过答辩,不能升职称,那你还在学校里怎么混?和你一起做研究生的,人家10年前就升教授当博导住教授楼了,你呢,还是骑自行车回你的讲师楼,丢不起这个人啊。
同时,甲骨学需要很长的时间积累,等到把自己的青春全部投入之后,才可能看到一点皮毛;等到对这个体系有了深刻认识,已届不惑之年;可能已经发现了很多破绽,但是不能揭开它,因为这很有可能造成原有体系的彻底瓦解,不仅毁了导师也毁了自己,因为很难再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
可见,目前已经看上去很成熟的甲骨文体系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
总之,因为时代所限,虽然甲骨学是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标本,但早期甲骨学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研究体系,天生营养不良,却已经长成为一个老人,让我们今天在甲骨学的科学化道路上障碍重重。
新的见解之一——黄奇逸先生
黄奇逸教授执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是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门派正宗。黄氏在参与编纂《甲骨文字典》的过程中,就发现了甲骨文研究旧体系的种种矛盾,按照黄先生的说法,就是强硬的约定,混乱、困惑。他在《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国古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一书中,举出了四十多个甲骨单字,分别给予了剖析,最后指出:
就是这四十多个字,已足以说明甲骨学旧体系的约定与虚假、空浮的破败事实了!在此我们要告诫学者的是,不要因为另外的甲骨文单字暂时逃脱了反驳与批评,那些文字的考释与字义就是可以接受下来的,这才是刚刚开始。另外,若真正熟习甲骨文与旧体系的学者,一定会知道,我们对这四十多个甲骨单字的讨论,已是根基性的与毁灭性的,有许多字只需一个字的毁灭,就是整个旧体系的毁灭!何况四十多个字呢?
黄先生列举了旧体系在文字考释中经常甚至故意犯下的错误。
比如生拉硬拽。旧体系中有不少单字,被隶定为很多的字,只要读音相同或近似,就拿来用。试举一例。包含“有”字的条目,在著录中超过了1000条,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字。以前很难读通,而只要通假为又、侑、尤、祐,就都可以读通了。很显然,黄先生不认为这个字该释读为“有”,他甚至认为,在甲骨文所处的文字发育阶段,甚至都不该出现假借。
再比如释读出一个字,用在其他文句中不通,就采取各种方法让它硬通。例如重新句读,用标点断句的方法,让整个意思看上去勉强通顺;或者完全靠自己臆想,硬把它读通;或者就说古人刻写时也有错讹。最后实在不行,就采取鸵鸟政策,置之不理。笔者按:事实上,目前被置之不理的甲骨文单字至少在3000个以上,占到了甲骨文单字总量的60%左右,未能读通的条目也许就更多了。在已经认出的1000多个单字中,只有大约500至700字是被公认的,其余一半左右各家有各家的认识,这一家也经常反对那一家,而且都言之凿凿、有理有据。
换一句话说,甲骨文实际上总体未能读通。当然,有些专有名词,比如人名、地名、特殊的器物名确实很难读通,它只属于甲骨文时期的特别约定,后来这些语词包括所指与能指都不用了。这些字,当然读不出来,也无需去硬读。但是,考虑到文化传承,考虑到那些特殊约定往往也是从原有体系中派生出来的,出现那么大量的不能释读的单字与条目,确实不正常。
黄先生给出了不是卜辞而是“录辞”的核心结论。
他认为甲骨文的功用是记录备忘,记录什么备忘呢?黄先生认为,日常的生产生活是不需要文字的,只有在处理相关于神的事情,比如祭祀,才需要文字的记录,因为害怕搞错。甲骨文上所记录的也是一种卜问结果,只不过是卜问将要举行的祭祀中关于时间、祭品、祭法(祭祀过程)的安排。这是谁给的呢?当然是神。也就是说,甲骨文仍旧是卜辞,只是不是卜问未来会这样还是那样、是吉是凶、是福是祸,而是卜问我们什么时候、以什么方法程序来祭祀列祖列宗。因此,甲骨文上的文字,都是文字按照祭祀时间顺序的自然叠加,本身不是什么句子,没有完整的语言逻辑,这也是读不通也无需读通的原因。
这样,黄先生的体系就很难动摇了。因为,它的每个字,都代表了一个(一组)物件或者会意了一个(一组)行为,能认出来的,比如鼎,那就是鼎,认不出来的,就是商代的一种器物,或者一种特别的行为,或者二者的结合会意,而由于时代久远,我们已经无法指认它们了。所以,在这个体系里,在甲骨文性质的研究领域中,没有必要读出的完整语句,甚至没有必要去考释那些没有认出的字。
黄先生还认为,人类之所以产生文字,不是庸俗的唯物史观所理解的来源于日常生产与生活,而是来自于祭祀。在中国上古人类的知识体系中,祖先就是神灵。神灵有支配万物的能力,把神灵(死去的祖先)伺候好,是必须的,绝不能因违背神意而遭致灾祸。祭祀就是一种对神灵的膜拜与贿赂(与神灵做交易)。所以必须按照神灵的提示,将未来祭祀的日期与贿赂物品(那时候没有人民币和美金)记录清楚,一点也不能出错。所以要用到文字,文字不是拿来作信息交流的,而是让巫师们作为备忘录的。

新的见解之二——璩效武先生
首先,他认定,没有典籍表明在周以前,人类有过占卜的行为。(不过,这一点确实面临很大挑战。虽然先秦典籍没有记载商人占卜,但东汉那些经学家众口一词所说的周人占卜难道会没有继承,凭空而出?而且,司马迁的《龟策列传》开篇,总算是一重根据吧。另外,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早在夏商之交,就有龟卜现象,因为出土了有钻凿烧灼痕迹的龟甲。这可以算作铁证吗?)
其次,璩先生认为,最应该做的事情是,考释出这些单字,然后放到所有出现这个单字的句子中去读,能够读通才行。读不通,说明字认错了,再认。璩先生通过近四十年的释读,终于能够像读报纸那样,把绝大部分甲骨文整句读通了,不仅符合逻辑,而且有一些得到了典籍的印证。璩先生反复强调,传统的方法之所以遇到很大障碍,文句考释错误百出,就是因为把甲骨文当作卜辞的错误观念。如果把甲骨文当作一般的文字记录,对文字进行合理的辨释,就可以很容易读通。璩先生甚至认为,他已经考释出70%到80%的甲骨文单字。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在业内,今天还在做考释单字这种基础研究的人绝对已经是凤毛麟角。
璩先生对甲骨文字的考释,认定甲骨文是商王朝的文字档案,它记录了朝廷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办事信息,而绝非什么“卜辞”。
在璩先生的描述下,一幅幅商代历史画面就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王子们是怎样最终被确立为鼎主(即商王)的;长儒(官衔名称)是怎样因为收受贿赂而被撤职查办、最终被鼎王取消了这一官职的;商帝、商王、领主们是怎样任命各级官员的,是怎样与政府部门进行对话并且发号施令的;农业活动、手工业活动是怎样开展的;乃至更具体到皇家驾车的车夫是怎样因为车祸肇事而受到囚禁的;妲己如何下令抓捕箕子的等等事件。
甲骨文字的研究,必须使用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的自我纠错机制。假设,验证(必须是逻辑和实践的统一),再扩大应用范围,发现问题,再重新完善理论,直到能够解释相关领域内的全部问题。
如果发现有些理论只能用在解决局部问题时,就说明,我们还无法全面认识这个领域,此时,我们对这个研究对象的定义就要做更高一级的归纳抽象。
基于以上的基本认识,笔者对甲骨文的定义是:
以龟甲和兽骨为载体的古代(主要指已发现的商周两代)文献。
那么怎样辨释甲骨文呢?
前辈已经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讨,比如字形类比法、偏旁推认法、借音法等等。实际上,这些辨识方法都仅仅是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不能形成科学的文字辨释体系。如何能够正确辨释甲骨文,学理上应该非常清楚——所辨认出的字应该与被检验文句的内在逻辑相一致,同时,相同的字,用在其他的地方也应是通顺不悖的。
具体说,首先是试错,先猜出一些常用字的意与音。这个“猜”,应该回到文字创造的根本而不仅仅根据字形类比,因为我们无法简单地由后断前,由周铭文推商甲文,更不能简单地由小篆去推测甲骨文。
文字创造的根本,主要是象形。尽管一切符号加以约定都可以最终抽象为文字,甚至我们完全可以把八卦的符号延伸为一种文字体系——64卦象再排列组合一次就是4096个卦象,每个卦象代表一个字,这已经足够了。
今天的计算机里,汉字输入编码不就是靠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实现吗?早一点的电报码就已经实现了数字编码。但是,在人脑记忆和手写文字阶段,这样的文字体系是不可能成立的,最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望文生义、明义识字。
抽象出一匹马的形状,就是马字;一只狗的形状,就是犬字;一头猪的形状,就是亥字。这样,自然界中的可视物相,就能被抽象为相对应的文字,比如日月、水火、草木、人兽、家居、衣着、食品、用品等。也有一些动作行为可以用稍复杂的会意方式表达出来,比如,两个人背靠背,就是“背”;两个人朝向同一个方向就是“从”;三个人在一起,就是“众”;耳旁有口,即为“听”;天空落点即为“雨”。
在使用文字的实践中,通过对文字记录符号的局部形态加以改动和增删,则能够反映出更为丰富生动的信息,比如手分左右,人分为站立的和跪坐的,二者又有形态(非常形象的姿态)的不同,从而表达出身份地位的不同。比如在璩效武先生的释读体系中,同为人形,却细致地分为中央级高官、子级官员、基层官员,以及卫士、士、民众、仆役等多种。
这些拟定、这些试错、这些猜测,最终要拿到文句中去检验。有的时候需要若干组试错的候选文字去排列组合,目的是达到句意晓畅,既符合客观现实,也符合语法的内在逻辑,所谓“能指”和“所指”的统一。
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试读出一定量的文字、语句之后,还要拿到其他出现相同图形符号的语句中去检验,必须做到在其他语句中也能通顺,既符合现实,也符合语句逻辑,这样才能确认释读的正确性,不应该在这里读成这个字,取这个意,在另外的地方又读成那个字,取那个意。
应该可以肯定,出现频率高的字,它们所组成的语句,假如释读正确,不会出现读不通读不懂的情况。假如有这种情况,说明释读有误,就要重新再来。就在这种反复试错和检验的过程中,文字的训读就会慢慢沉淀下来,集字成句,集句成篇。最后,如果发现有些篇章恰好符合典籍的记载,就更能够确认释读的正确性,然后用这种正确的训读再去检验更广泛的语句,逐渐地,完成对甲骨文字的全面释读。

朱书龟板
在反复释读过程中,我们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造字方法,了解古人是怎样造出这个字的。这种造字方法的得出,来自于释读的正确性。随着对造字方法的深刻了解,就可以更有效地释读新的不认识的字。还有造句方法(语法)、文章体例(文法)、文章性质(陈述、抒情、疑问、命令或者祈使),等等。
必须重新将甲骨文“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商代文献,而不是商王占卜刻辞,才能够揭开甲骨文之谜。
甲骨文是商代文献这一定义的提出,非常重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
1、用“文献”取代“卜辞”,内涵的特征减少,扩大了外延,意味着甲骨文有着更多的可能性,以此可促进甲骨文研究跳出原有的框架。
2、用“文献”取代“卜辞”,明确地展示了甲骨文更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使甲骨文研究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跳出文字学的框架,直接与历史学接壤。以下一些要点是无论如何应该给予重视的
• 第一,甲骨文从理论上讲是绝对可以被全面释读的。
• 第二,文字考释是甲骨文研究的根,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 第三,有了完整的原始图像信息资料,就需要一一验证多种假设。
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从1899年被发现时,它就向世人彰显着无穷的远古信息。然而,四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也许尚未掀开这部历史宝藏的帷幕,这一切,都因为我们不认识那些字,更可怕的是可能认错了那些字。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走错了路,没有构建起科学的研究体系。
不怕,一切都可以重来。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从来不会输掉什么。
更多好文,科学学书法。关注中书汇书法学苑微信公众号。zshsfx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