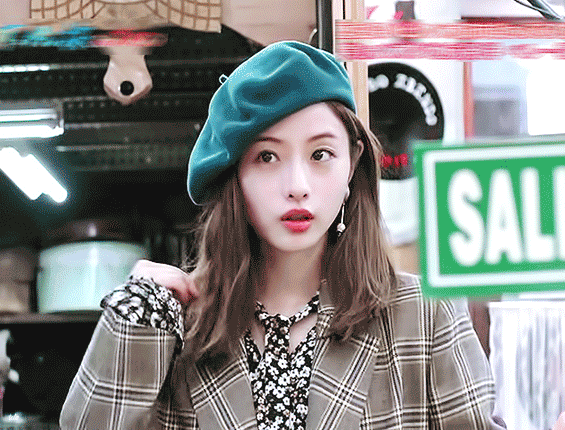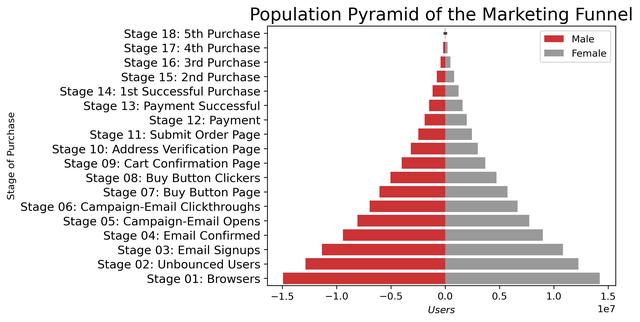云也退/文
词语不仅命名事物,而且记录我们对事物的感受。我们在小学里就懂得,热的反义词是冷,暖的反义词是凉,说“凉”的感觉要比“冷”缓和很多。存诗很少的唐代诗人王之涣,写有一首《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奇崛的意象,仔细分辨就可以发现“凉州”一词的来历:“京”是高大的建筑,城楼之类,在塞外的寒荒之地,在群山上下,人们建起一座城、驻扎军民以抵御凶悍的游牧民族,不让羌笛接近中原的杨柳。那正是“凉”的感觉:高寒、孤独,身体和心灵同时感到冷飕飕。
“cool”这个英语词,也和中文的“凉”异曲同工,是属于感受性的。“cool”的本义就是温度低,可是,“温度”很早就成为象征性、隐喻性的概念了,一个人的心理和情绪状态,都可以用温度词语来表示。像是我们中国人讲某人“头脑一热”,是说他莽撞爱冲动,英文里讲急躁、莽撞的人的词则是hot-head——“热头”;中文讲“冷眼相待”,英文叫“coolreception”。莎士比亚说,cool用在人身上,是说这个人有一种“不为冷静的理性(coolreason)所理解的智(wit)。”
而在“酷”的意义上,cool的变化还要比上述的象征化、隐喻化走得更远。不管是谁,被他人称呼“酷”的时候,心情总是会很不错的,似乎在那一刻,他的生活、行为和存在的方式得到了一种确认,他显然是年轻的,个人主义的,也是有吸引力的,他选择呈现给他人的样子,超越了“可接受”的层次,达到了值得羡慕和模仿的境界:他比众人更加放松,充满了自信,同时带着一丝疏离感;他充分地展示自己,对此不仅自知,而且不太关心他人怎么想。
但“酷”也不能仅以一个概念行世,它一定会由少数人来代表。在《酷的起源》这本书中,作者迪纳斯坦最初提到的一个名字,是迈尔斯·戴维斯。这位黑皮肤的音乐人,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音乐舞台中亮相,宣布了一个转变,同样的乐器,乃至同样的乐曲,在他的演奏与其他人之间有细微的差别。
迪纳斯坦从戴维斯在巴黎度过的时光开始,写他朱丽叶特·格雷柯的爱情故事,也写到了让-保尔·萨特和戴维斯的一次对话。格雷柯是战后法国最红的文化群落里公认的缪斯。格雷柯唱的香颂,声音有一点啥呀,流露出一种时人都能体会的共同心境,从而成了战后塞纳河左岸的一块招牌。人们不能自禁地转头,去看向格雷柯那张完美的脸,完美到无可挑剔,是百废待兴的巴黎城内人们众望所归的城市象征。她的爱情也势必要经受舆论的考验。迈尔斯·戴维斯出现了,在路易斯安那酒店客房墙壁上,就贴着一张他的照片。两个人的情缘颇为动人:1949年,初到巴黎的戴维斯相识格雷柯,他爱她爱得发狂,却没有跟她求婚。《酷的起源》记录了萨特和戴维斯的一次对话,萨特提议戴维斯留在法国,戴维斯则担心自己会毁掉朱丽叶特的演艺事业。
巴黎是自由的,爵士乐在这里也被看作是缪斯一般的艺术,“我的生活中从未有过那样的感受,那种在法国的自由感,那种真正被视作人的感受,真正受到重视,像一名艺术家一样”——戴维斯如是说,但他也知道,回到美国才能留在他熟悉的艺术潮流里,他不能“与同好、自己的国家乃至曾哥爵士乐圈失去联系,进而丧失自己的种族自豪感”。矛盾的是,在那时的美国,朱丽叶特已被称作“黑鬼的婊子”,但戴维斯的“种族自豪感”却只能来自那个对有色人种充满了偏见的国家。
虽然爵士乐起源于1920年代的美国,虽然在1924年,卡尔文·柯立芝(Coolidge)还用“保持冷静,保持柯立芝(Keepcool,keepCoolidge)”这个诉诸文字游戏的竞选口号让“cool”一词成为流行语,但要到战后与存在主义的巴黎相遇时,爵士乐才算是确立了它的“酷”的招牌。存在主义相信,世界根本上就是失常的,人在其中的行为无法控制后果,命运是绝对的无常,但是人可以对自己负责,也可以诚实地认识自己,最关键的是要活在并专注于每一个时刻。
这些认识完全兼容于爵士乐的创作和表演理念,从非洲黑人文化衍生出的爵士乐,是一种彻底鼓吹“为当下而活”的音乐,诺曼·梅勒准确地总结说,对黑人来说,生活就是战争,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所以天然就能吸收“存在主义的突触”。在最具影响力的美国黑人作家如佐拉·尼尔·赫斯顿和理查德·赖特的书中,黑人主角使用的直接而泼辣的俚语,往往可以直接进入摇摆风格爵士乐的歌词,这种音乐把语言彻底变成了玩物,操持这种语言的人显然是脱离于主流的,在不被多数人理解的情况下我行我素,并乐于继续传达对此无所谓的态度。
当然,存在主义单单在思想上显“酷”,或者单单凭着萨特的《理智之年》或加缪的《反叛者》来宣示它的“酷”,那还是不够的,它必须得有阿尔贝·加缪这位具有外形上的充分说服力的旗帜人物。对于加缪和亨弗莱·鲍嘉的相似,几乎每一个为他写传记性文章的人都不会忽略不提:
“1946年,阿尔贝·加缪在《时尚》杂志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被几位女性称为‘年轻版的鲍嘉’——他经常听到这个比喻,并且总是引以为豪。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加缪经常在时髦的黑帮西装外套上一件风衣,驾着一辆黑色雪铁龙车行驶在左岸地区。……当加缪穿着租来的晚礼服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时,‘每个人都说……他看起来像鲍嘉’。”
迪纳斯坦的记述常常流于八卦味。不过他还是指点道,加缪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他的朋友同学认为是“pudeur”的人,这个来自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口语的词可以理解为“cool”,“指的是一种安静、强烈的自负,翻译过来就是‘不愿表达内心的秘密’。”当他在《战斗报》工作的时候,编辑同事认为他的人格魅力是复杂而独特的,他“微笑中透着悲伤,双目低垂,眼神带有讽刺”,但是“表情坚定……又总是令人心碎和心动。”不管怎么讲,加缪是一个让人一接触就难以忘怀、甚至于迷恋不止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
加缪沾了鲍嘉的光,由于有鲍嘉在先,加缪也被打上了一个可辨识的标记。但鲍嘉的走红也是搭乘了电影技术起飞的翅翼。美国是战后世界诞生各种奇迹的地方,其中最大一个奇迹是关于电影的,有声电影的问世、好莱坞的迅速经典化,以及特写镜头的出现,等等。在黑白片的时代,男人要在特写镜头里让人过目难忘,表现出冷酷无情的样子是绝佳的选择,于是,能靠着沉默寡言地板着一张扑克牌面孔露出让人着迷的魅力的鲍嘉,以及加里·库珀、罗伯特·米彻姆,再到詹姆斯·迪恩这样的演员,自然“出圈”成为至少三代人眼里的时尚的化身。鲜为人知的是,似乎一贯冷静尖刻的萨特也是为好莱坞电影着迷的人之一,他在日记中,这样抒发看加里·库珀电影的感受:
“我心中有着强烈的、难以言喻的怒火,我多么想躁动起来……我的美国工人(例如加里·库珀)能够感同身受并付诸实践。我想象着他坐在铁路路堤上,疲惫不堪,身上满是灰尘;他正等着运牛的卡车,然后趁人不注意时跳进去——我真想成为他这样的人。”
在本书的第五章中,迪纳斯坦把上述三种“酷”——爵士乐、黑色电影和存在主义做了一次综合。对后世鲍嘉的众多评价中,有一个比喻非常到位,它说鲍嘉就像一个手套,准确合体地戴上了他那个时代的正直坚韧的手。看鲍嘉的表演,不能不连带着对爵士乐中的烈酒款——“蓝调”产生神往,也很难避开存在主义的影子。如果说,1920年代的爵士乐是为一战后的美国打开了自由发泄的通道,那么二战后的爵士乐就是“诉诸声音形式的存在主义”,它是在欧洲支离破碎,种族主义与日俱增,两个超级大国霸权初现,而核武器的威力已经震慑到世人的情况下呼喊出的“个人生存的声音”。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酷的起源和发展中有着深刻的城市因素、种族因素,以及性别因素:酷是城市人的专享,只有城市才能聚集起足够多的陌生面孔,才能有足够多的橱窗、海报、杂志、电影院、书店,才能有街头摄影师以及街头弹唱。酷是非裔人带到美国的东西,他们带来了新的语言,新的旋律,让人狂奔并在荣耀中喊叫,在同种族主义的拉锯中繁荣:1947年,查理··帕克四重奏录制了《酷炫蓝调》,被《纽约客》文章评价为“比波普人有了自己的语言”,两年后,迈尔斯·戴维斯发布了《酷的诞生》,开创了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爵士乐风格。在乐评家眼里,“酷”正是黑人与白人社会接触的副产品。
同样是在战后伊始,黑人爵士萨克斯风手莱斯特·扬首创了“我很酷”这一短语,从此它就进入了美国口语,再也不曾被冷落。迪纳斯坦认为,鉴于当时种族歧视的大环境,“我很酷”一语是在表示一种自我的坚实: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是在压迫性社会力量之下的一个坚实存在。萨克斯风之所以引领了一场革命,不是因为技术上如何高超,而是因为节奏上有惊喜,旋律上有自己的想法,他的乐曲特立独行,有着自设的规则,它比其他爵士乐更克制,从而被称为“酷爵士”,仿佛是在本已很酷的爵士乐世界里凝集出了一个耀眼的尖端。而扬的革命里同样少不了视觉的一环,是他把戴墨镜上台的形象率先展示给了嘈杂欢乐的观众,而他又在一片喧腾之中、在鲜明的节奏之中保持超然和冷静。他让人明白,墨镜就是要在夜间戴出来,那样才叫面沉似水,冷若冰霜。
扬也是以音乐发迹的黑人。那时,黑人艺人把自己“汤姆化”的倾向极盛,也就是说,以一副笑嘻嘻的自我嘲讽的脸面对白人观众,以迎合他们对黑人的偏见来博取自己的名声。而扬却不通,不仅他的演奏风格是不在乎观众的,而且他台下说话的方式也是极尽特别,用一些难以理解的“臀部俚语”来打法他人的问话。很多俚语由他而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扬和他的“酷”阵营里的其他人物为美国人留下了一笔厚重的西非遗产。正如加缪的酷有一个阿尔及利亚法语的“pudeur”根源一样,扬的酷也被追溯到了约鲁巴语里的“ititu”,这个词的本意同样跟“cool”的本意——凉爽有关,它比凉爽更凉爽,比一般所说的酷更深刻。
扬的墨镜风格后来被鲍勃·迪伦继承了,被地下丝绒乐队继承了,当约翰·卡尔说“我们在舞台上戴墨镜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无法忍受观众的目光”时,他已经把疏离感的真正起源——非裔美国人在一个种族主义盛行的国家的切身体会——给遮蔽了。扬式的酷在电影界的最佳继承人则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伊斯特伍德十分崇拜那种独行侠、反叛者的气质,他曾说,莱斯特·扬在一张空白的听觉画布上自发创造艺术的做法是纯正的英雄主义。著名的电影评论家大卫·丹比是这样评价伊斯特伍德的:他的“酷“源于那些爵士乐音乐家,它"稍显冷漠,为了内心满足而扣押其他一切”。
爵士乐像火种撒在各处,也因此而不幸地被人遗忘,因为摇滚乐、嘻哈乐你方唱罢我登场,它们都模仿爵士乐,从而淹没了它的本来面目。音乐及其周边文化改变了美国和更广泛的工业化世界,爵士乐完全成了过去时,等待文化史家来重拾线头。
酷也跟性别有关,它集中体现于男性。不过迪纳斯坦也分析了几位女性,例如蓝调先驱贝西·史密斯,还有比丽·霍勒黛。迪纳斯坦对霍勒黛的评价是,霍勒黛能够在身体放松的情况下,进入复杂的情感状态,她是靠了这种能力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的,同时,霍勒黛以一种原创的、标志性的表演风格,来推举出一种仅属于她一个人的艺术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表达。女性的酷,和男性一样,也要呈现出自负的、个体的反抗精神。
迪纳斯坦把酷完全视为美国制造,欧洲的存在主义酷也得依托美国的电影明星和爵士乐才能成型。但无论怎样,酷都意味着个体的高贵,对社会的集体化管控、对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提出抗议。1945年8月之后,打倒了法西斯的世界并没有迎来真正的解放,尤其对美国黑人而言,他们时刻都面对“战争”,不得内心的安宁。乔治·奥威尔在战时为英国广播电台工作,他依托这段体验创作了举世闻名的反乌托邦小说,这个事实往往被人忽略:奥威尔是从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而不是从法西斯或苏联的身上)预见到了权力高度集中下,社会将会沦为怎样的“大洋国”景象。因此,非裔美国人对集体痛苦的坚忍反应,启发了那些在战争中看过了无法想象的恐怖,同时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约束的人们。对酷的拥抱,是以孤独、疏离、冷漠的方式进行反叛的需要。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嘻哈文化出现了,迪纳斯坦对它兴趣并不很大,他认为爵士乐的黄金时代在里根时代开始时就彻底结束了,结束的原因在于,人们重新重视起拥有财富的前景,渴望进入上层阶级,而把昔日的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孤立为“文艺青年”的选择。每个人仍然想变酷,但酷这道密码不再能让一个人进入一种不同一般的成功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