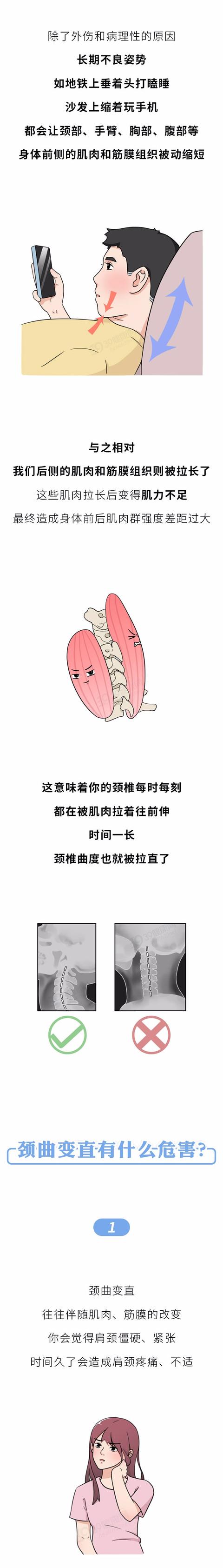作 者 | 方斯远(暨南大学法学院教师)
法学背景知识部分基础文献
1. 黄 卉:《一切意外都源于各就各位——从立法主义到法律适用主义》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2. 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3. 何美欢:《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4. 邓 峰:《走出封闭的体系:求知时代的挑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5. 汤文平:《民法教义学与法学方法的系统观》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法学院
导 读
当年我初入法学院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说,法学院不是培养法官的,不是教你如何审理案件这种工匠之学,而是培养思想家。听完这句话,我感觉自己顿时浑身充满了洪荒之力,仿佛成为圣贤国师思想家就在明天。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逐渐发现,诸如民主、自由、正义这样高大上的词汇,并没有给自己的思考带来什么帮助,面对具体的问题,哪怕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纠纷,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去分析。有时候被外专业的朋友问起对某个法律问题应该怎么看,我无言以对,只好拿些正义衡平之类的大词去搪塞一番,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真是无颜以对。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如果那位老师的说法是对的,法学院的学生应当着眼于高深学问的思考,终极问题的解决,那法学院有必要存在吗?让哲学系、经济系、社会学系或者中文系的高年级学生选修法律,效果不会更好吗?如果我们学完之后,满口大道理,面对真实的案件却无能为力,难道不会很尴尬吗?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曾经说过,“忙于处理本身方法论的学科,是不健康的学科”。而一位我非常尊重的老师也曾经善意提醒我,不要沉溺在所谓的方法论的争议中,方法本身是为解决问题而存在的,应该将目光着眼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能够体会到方法如何运用,正如在切菜的时候,就会自然发现倚天剑不好用,菜刀才管用。
这两位前辈说得都非常对,但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尴尬局面是,我们这门学科,到现在还在方法论层面有根本的争议。这样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很多同学遇到问题,不愿去梳理现行规则,不知如何解释现行规则,也不去搜集相关的案例,而是直接依据自己的理解去解读课堂上接触过的法律条文,最后直接推出“这个问题我国立法没有规定/规定得不好,应当加强立法”的结论,于是每逢论文季,总能看到无数立法建议。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和社交媒体上那些一说到社会问题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立法”的普通民众有啥区别呢?我们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呢?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是不是意味着把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全部编入人大,出一个问题就立一部法,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对比域外,不可否认,英美德法等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比我们历史悠久很多,也完善很多,但他们的法律在起点上就是完美的吗?他们的制度一路发展过来,靠的都是立法吗?
希望诸位阅读了本部分节选的五篇文章之后,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判断。
第一篇文章是北航法学院黄卉老师的《一切意外都源于各就各位——从立法主义到法律适用主义》。
这篇文章是当年开启我法学之道的钥匙。还记得我在书摊上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立马被开篇的追问吸引了,“南希猛地越过茶几向我倾过身来,凑到我跟前,慢慢地但重重地说:你们的法已经够多了,重要的是要认真对待(我还记得“enough”和“ take seriously”)。
她长篇大论,但总结起来,好像就是说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问题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我们的法律够多了?我们现在没有认真对待自己制定的法律?这是不是一种不了解我国国情的“友邦惊诧论”?在文章的其他部分,黄卉老师针对“为什么立法迷信盛行,而法律适用主义在我国得不到推广”进行了解释。诸位在阅读时,请注意黄老师谈到的几个问题,成文法的优点和缺点各自在哪里?立法之后就可以直接适用到个案了吗?如果说从抽象的立法到个案的适用之间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应该如何完成?法律概念在这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面对经济学、社会学、哲学这些高大上的学科的知识,如何将之并入我们的法律思维?
第二篇文章是北大法学院葛云松老师的《法学教育的理想》。
或许有同学会问,法学教育的问题难道不是应该你们做老师的才关心吗?为什么我们这些新鲜人也要关注?实际上,“教”与“学”本身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位资深教授对教育的思考,本身就是立足于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离不开与学生的互动,学生学习情况的总结以及学生毕业之后的反馈。而也只有基于这样的双向思考,才能观察到法学学习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因此,葛老师这篇文章,主旨谈的是法学教育的问题,却对学习也有极大的助益。在我最初看到这篇文章摘要的时候,内心很震撼,因为葛老师就旗帜鲜明提出我国“应当借鉴德国经验,将中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在法官能力之培养,即培养学生掌握我国主要实体法、程序法的基本知识,并具备法律解释与适用的能力”。
一方面,据我的学习经验,尽管我国自从清末变法以来,就走上了大陆法系的道路,但是旗帜鲜明提出法学教育要走德国路线的,似乎并不多,而从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来看,似乎也在两大法系之间摇摆不定,在形式上,我国这种从本科开设法学院并相应设置法学硕士博士的做法与是沿袭大陆法系的,但在法学硕士和博士的招生上却没有区分本科专业是否法律,这又接近英美法系的做法,而为非法学本科开设的法律硕士(JM)学位,借鉴的却是美国法学院的LLM,但从2007年开始新设立的法律硕士(法学)学位,定位于给法学本科出身的学生进行实务性的研究生教学,却又颇具中国特色。
另一方面,葛老师明确强调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当定位于法官能力的培养,这也与我之前所听到的大部分观点大相径庭。当时我就觉得,本科以来很多困扰我的问题,或许能在本文中找到答案。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葛老师对法学教育的现状做了评估,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尽管研究对象是我国的顶级法学院,但当中提到的问题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如“拿到一个具体案件(哪怕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件)时常常手足无措,最常见的就是将自己仍然基于普通人的公平感而获得的粗浅结论,包装在似乎从天而降的法律概念而非现实的法律制度之中,却没有掌握分析案例的结构、思路。面对一个抽象法条或者一个理论命题时,只能拼命地在记忆中寻找书本知识,如果还幸运地记得,就开始复述。希望其加以进一步解释时(包括提示了需要解释的问题时),则茫然无措,或者只能凭感觉谈自己的观点。至于理由,大体上就是感觉本身,或者祭起基本原则的大旗,用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来处理问题”。
从第二部分开始,葛老师集中分析了在大学本科有限的时间空间之下,为何法学教育应当以培养法官能力为目标。在阅读过程中,大家不妨带着以下问题思考,强调专业教育是否意味着排斥通识教育,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法律从业人员的范围很广,为何要以法官能力作为在有限的时空之中重点突破的能力?如果未来想做的是诸如公司并购,IPO这样的非诉业务,这种法官能力培养的意义在哪里呢?法官能力包括哪些方面?如果说审判工作主要包括事实认定(如小王是否杀人)和法律适用(如小王是否应当判刑?判多重的刑期)两方面,在本科学习中是否应当二者并重,抑或有所侧重?
从第三部分开始,葛老师讨论的是法学本科课程设置的问题,这似乎与同学们关系不大,但这里可能需要告诉大家的一个背景知识是当前我国法学教育课程设置的一个特点,即由十六门必修主干课程和若干选修课程组成,前者是有关部门规定的,后者则由各法学院自行安排。课程设置本身的科学性,我们没必要太关心(说了没用),但葛老师对课程设置的理想状态的探讨却可以对大学四年的自我学习规划有所帮助,在本部分,大家可以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说基础知识比前沿理论更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法律实务中出现了相当多的新问题,法律市场也产生了很多新的业务,法院也需要处理很多新类型纠纷,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法学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的质疑,不止一次有人表达过,在学校学习的法律知识用处不大,如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民法上的意思表示理论、公司法上的企业理论,在实践中解决不了问题,不如直接在大学多开设实务课程。真的如此吗?不妨留意葛老师如何用企业法务的例子来说明。
从第四部分开始,葛老师讨论的是案例教学的改革,在这里大家不妨看看例子里的“王先生洗车案”,先用自己的常识去判断一下结果,再看看葛老师用的规范分析,由于诸位还没有进入专业学习,因此对解题思路不太了解是很正常的(实际上绝大部分学过专业知识的,也未必能掌握这个解题思路),或许有同学会疑惑,用常识可以轻易判断的问题,干嘛要那么大费周章啊?这个问题在第三部分许德风老师的一篇文章里面会有分析,此处按下不表,但大家可以仔细读一下葛老师所提的案例教学的七个意义,这些意义转化一下,难道不是对我们学习的要求吗?
在第五部分,葛老师勾画了他心中理想的法学教育完整路径,或许,这能成为我们学习与自学的一张地图?
第三篇文章是清华法学院何美欢老师的《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
实际上,本文写作于葛老师的文章之前,而葛老师也在文章多处有与本文观点的呼应或商榷。我将本文编在后面,是考虑到何老师接受的是英美法系的教育背景,在文中更多强调了一种以精英律师养成为导向的教学理念(何老师在本文中将广义的精英律师界定为精英法律人,把政策制定者、法官都涵盖在内,但文中主要探讨的还是狭义上的精英律师),但目前我国整体接受的是更接近大陆法系的学制和课程设置,而在毕业的去向上并不限于律师业,因此葛文相对来说更具普适性一些。
但何文同样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在一定程度上,对同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而且,有相当多的地方尽管是在讨论教育问题,但如果细心考察,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学习的操作手册,希望大家认真阅读。在文中,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各位格外留意。
首先,何老师归纳了英美业界执业律师所应当掌握的技能,对于初入法学院的新鲜人来说,这些或许有些遥远,但却可以作为未来学习中检验自己的目标。
其次,何老师运用了布卢母分类学,生动地描述了学习认知过程的六个部分,这个归纳,有助于我们在学习中“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尤其是对于新鲜人来说,总会把高中的学习方式沿袭下来,但根据何老师的归纳,这样最多也就是到达了“知识以及某种程度的理解”,却没有高层次的了解,最后可能的结果就是“高分低能”,在学习中,大家可以有意识地参照这六个部分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第三,何老师专门强调了学习能力的培养,这里要注意的一是终身学习的理念,法学本身就与社会变迁紧密结合,一招鲜吃遍天是不会再有了,二是对基础知识的强调,据我所知,很多同学在毕业之后都会埋怨读书无用,在实践中学校学的基础理论一点都用不上,但何老师在此给出了最完整的答复,
“一方面, 同学们忽视扎实根基的重要性。他们 ( 甚至一些没有执业经验的教授们) 往往追求最新的, 最前沿的知识 , 而不屑学习基础知识。例如, 没有学 习好公司法、合同法、财产法, 没有学习过证券法的同学却选读证券期货法。他只可能从这个课程学习到一堆术语 , 一堆期货的名称, 现有简单的期货内容 , 但精英律师执业所需的改造、创造新期货的技能 , 肯定与他无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 除了对知识的非理性渴求外, 这种行为可能是建立在对知识、其运用及其价值的误解上。当同学发现在现实生活里 , 他很难直接原装使用在法学院学到的法律概念 , 同时又发现现实生活里有很多在法学院里没有接触 过的新事物的时候 , 他可能会得出法律知识不重要, 或者法学院应该教授最新 知识的结论。其实, 法律知识是很少有原装、直接使用的。如果问题这样简单, 它根本就不会出现在律师面前, 出现在他面前的问题需要运用不同的法律单元的组合来解决 , 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找出并组合适用不同的单元。有一肚子的法条但找不到适用的是学习( 教学 ) 不到家的现象 , 而不是知识无用的例子。关于新问题, 以为新问题需要新知识来解决的想法 , 其前提仍然是认为知识可以直接套人并解决问题的误解”。
我想告诉诸位的是,每每遇到质疑基础知识,感叹学习无用的朋友,我都会把这段话给他们看一下,而他们往往会恍然大悟,特别是一些毕业后从事高端业务,其实务工作的理论研究要求并不亚于学术界的朋友,基本都深表赞同,其实这个道理,他们在工作中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但何老师的论断却是完整地解开了他们心中的疑惑。希望诸位也能藉由这篇文章,在日后的学习中“活得明白”。
第四篇文章是北大法学院邓峰老师的《走出封闭的体系:求知时代的挑战》。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葛文与何文都强调了法学院的学生必须要有多学科的知识,并不能固守传统教条,而邓老师的文章,则进一步强调了这个求知时代应当如何自处。现在科技发达,各类社交媒体上可谓众声喧嚣,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引来大段大段的讨论,但,人们的认知水平真的经由讨论而提高了吗?
在文中,邓老师不无忧虑地表示,“这种缺乏真正的反思和学习能力的问题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通病,价值上的冲突,立场的选择,压倒了对解决细致、具体和复杂问题的关心。知识、学问、思想的交流、辩论和讨论,变成了主张的宣示、重申和强调。”大家不妨对照看一下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想必会深表赞同。价值观、世界观乃至政治立场的选择,更多属于个人的事务,但是个人的选择是否应当建筑在正确的认知上呢?如果接受了系统的大学教育,但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是“定体问”、“中必输”,难道不是一件挺悲哀的事情吗?那我们应当如何避免沦落于此呢?邓老师告诫大家,不要把任何现象的分析和评价都简化为标签式的立场分析,而要多思考何种法学,何种法律,何种解决方式,何为合理或正确,如何实现,如何做这些更为具体、深刻而棘手的问题。
在此邓老师以“司法独立”举的例子,大家可以多关注。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司法独立四个字仿佛带有魔咒一般鼓舞人心,在不少课堂、讲座与文献中,以绝对真理的形象出现,并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中国司法所有的问题都来源于司法不够独立,但问题真的是这样吗?在后来的学习中,我逐渐发现,即便是对这个名词的定义,似乎也是含混不清的(一位美国教授曾经以“司法独立?引用的多,理解得少Judicialindependence: often cited, rarely understood”为题撰文,表达了这种困惑),而如果打开这个概念,它到底指代了什么样的制度呢?是单一的制度还是多种制度的结合?是全球通行的标准还是在各国有不同的表现(制度组合)?
在法学中,其实这类披着天然正确性外衣的概念或理念比比皆是,但正如邓老师所言,总是“缺乏理论研究的基础,以至徒然成为纯粹的意识形态之争”。希望大家在阅读本文之后,在未来的学习中有所注意。(斯考特·杜罗描写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年级生活的经典之作《哈佛新鲜人》中描述了哈佛法学院一年级合同法课堂的一个场景,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这种问题,“一天课堂上,佩里尼问了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交易与立约权是所有成年公民都享有的,而不是只留给特定的对象?有位同学以耳熟能详的金科玉律回答:人人生而平等。“哦,是吗?”佩里尼问:“维亚先生,人是你创造的吗?还是,你做过问卷调查?”“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维亚回答。“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佩里尼继续问道:“你要怎么证明呢,维亚先生?”事事要求检验与佐证,并不容易。许多内心深处的本能信念,根本是分析不来的,有些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说,我相信财富应该要广泛分配给大众才合理,但是我也同时相信,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力;从个案的讨论当中,却常发现这两个原则纠葛不清,难以平衡。”)
第五篇文章是我们院汤文平老师的《民法教义学与法学方法的系统观》。
其实,通过阅读前几篇文章,诸位或多或少应该看到我国法学方法争议的冰山一角,也就是法解释学(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PK。
对于这个问题,诸位目前无须过多关注,但如果细心阅读前面几篇文章,不难发现,无论是哪一方的观点,都认为法学院学生的知识面不应当局限于法学的专业知识,毕竟法律解释本身并非一个纯粹的文字解读作业,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认知过程(从葛文的王先生洗车案,诸位应该可以略有感悟),事实上,无人否认法律人需要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甚至自然科学知识),关键在于如何将之有效地整合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导入自己的法律思维体系,避免思维漫无边际,尤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信息和知识并不难,但是养成专业的思维方式很难。
在这篇文章中,汤老师对这一问题做了解答。考虑到本文以学界为主要受众,诸位在阅读时觉得困难是很正常的,在具备一定专业知识之后再读,想必会有新的感悟。在此仅希望诸位新鲜人关注几点,在第一部分,汤老师把法律问题的判断先简化为“合法vs非法”(这二者之间其实有一定的模糊地带,但在此暂时不必过多关注),而提出了一个“规范上封闭,而认知上开放”的解题思路。
汤老师在此举了民法上请求权基础的例子,由于诸位还没学过民法知识,可能看不大懂,简单来说,假如有一天,刘表过来起诉刘备租赁了他的荆州楼,但租期届满之后赖着不走,请求法官判决刘备搬离荆州,并赔偿损失一万元,而刘备则辩称,虽然租期到了,但自己目前资金链断裂,没钱租住其他地方,而且时值寒冬,如被迫搬离,怕是全家会在街头饥寒交迫而亡,对这个问题应当怎样分析呢?刘表的主张能在法律上成立吗?如果成立,依据应当是哪一个条文呢?请求赔偿的一万元合理吗?刘备的理由在法律上能构成有效的抗辩吗?
如果刘备所言真实,那么法官在作出裁判的时候需要考虑这种可能会发生的严重后果吗?对此,“规范上封闭”就意味着,针对当事人的主张,法官要在有效的现行法之中找到相应的法律规范(这就是请求权基础),从这点来说,“规范上封闭”本身就是“依法裁判”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封闭”并不意味着法官只能死扣条文,僵化适用法律,没有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就不能在审判中考虑,如果说制定法是一种形式性的依据,那么对诸如行业习惯、社会主流价值判断这样的实质性判断依据仍然需要保持“认知上的开放性”(诸位可以对比黄卉老师的文章中这段话“成文法的基本特征和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它对千姿百态的人、事、物关系进行了高度概括,为了覆盖尽可能大的适用范围,此谓成文法的高度抽象性。但是,那些被生硬削剪掉的事件细节——它们是生活的褶皱,是空气——往往对法律裁判更为重要,狠下心弃之不顾,实在是成文法的先天不足。于是,法律适用需要一册详细的、活页形式的使用说明书,帮助读者还原被抽象法条隐去的具体,同时不断添加使用者的新发现以节省后来者的使用成本”),仍然应当在现行法之中找到像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这样的支撑点,否则不但依法裁判无从谈起,最严重的是司法会沦为法官的任性。
在本部分,汤老师还讨论了法教义学沟通立法、司法与法学的功能,初入法门的诸位不知对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看法呢?原则上,立法者制定法律,司法者适用法律,法学家发展法律,似乎是一派和谐的景象。但诸位将来在实习和工作中,很有可能会发现现实是一副三国杀的场景,司法者埋怨立法不可操作,法学家批评司法僵化裁判,司法者批评学者脱离实际,不一而足,这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大家目前不必关注,需要留意的是,为什么说法解释学是沟通这三者的最佳方案,试想,假如我们“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能够学会用这个方法贯通三者,那将来的就业岂不是更方便了吗?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