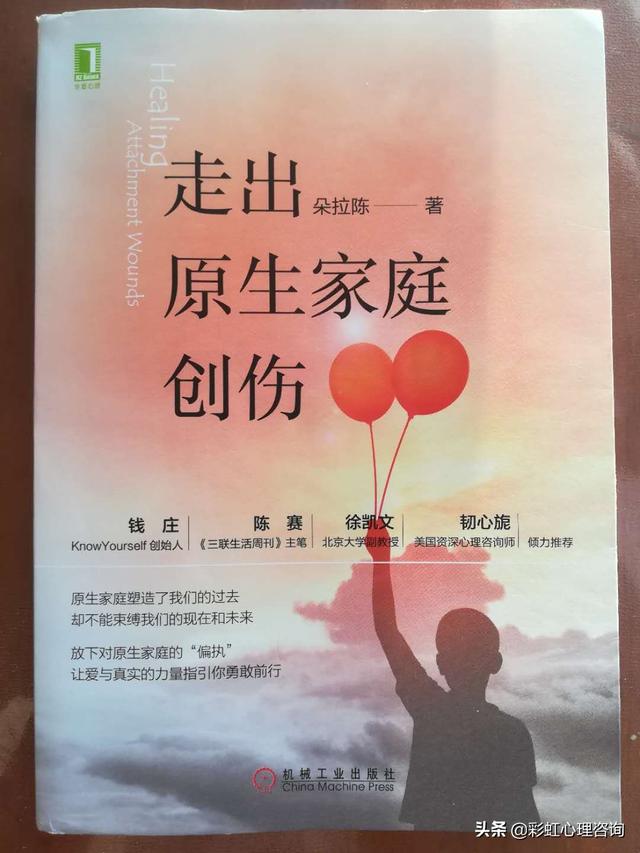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实习生 丁超逸
上海的四月里,杨程睡在窗边,每天被鸟叫声吵醒。
一个清晨,耳边不停有人在对他说,“你可知、你可知?”仿佛要让他接受一个真理。醒来后,杨程一顿纳闷,听到窗外有鸟叫,“咕咕咕”,也是三声,原来是鸟叫声钻进了他的梦里。
他32岁,是一名广告行业工作者,租住在延安西路附近的老公寓。封控在家后,他偶尔烦闷,对窗外的风景变敏感了。4月22日,一对雄雌斑鸠来他家窗台考察地形,一会儿窝进花盆里,一会儿飞出来,过了两天,花盆里出现了两颗蛋。5月初,小鸟孵化出来了,绒毛茂密。“那时候蛮激动的”,杨程说。

杨程窗外,珠颈斑鸠和它的两颗蛋。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年幼的珠颈斑鸠,浑身绒毛杂乱。
封控期间,路上几乎没有人影,听不到车流声。只有偶尔响起的大白志愿者的喇叭声,城市安静下来。
这时,杨程窗边珠颈斑鸠的叫声显得更欢快、密集了。
过去的两个月里,居民隔离在家,他们与外界的接口可能只是一扇窗,或是一个阳台,随着活动尺度的缩小,他们重新发现了同样在城市里讨生存空间的另一批居民:野生动物。
人类“消失”后的世界
鸟似乎变多了。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员王放有这样的感受,疫情期间,被“关”在家几十天,在小区的树下、小池塘边坐一坐都成了奢望。为了维持五岁半儿子的心理健康,能出楼栋后,他每天和孩子沿着小区的一条路线巡游,意外发现树上有一个不起眼的乌鸫窝,等待食物的小鸟在焦急地大叫;棕头鸦雀的数量好像也增加了。
一路下来,孩子的衣服和裤子总是沾满了草籽。王放很惊喜,正常情况下,小区里的植物都有物业请来的工人按时修剪,封控时,“人都管不过来”,草木疯长,这给了鸟在小区里更好养活自己的可能性。
一天,他和孩子走着走着,满地都是紫色的汁水,抬头一看,是一棵樱桃树,白头鹎和乌鸫源源不断飞来,啄食樱桃。

封控期间,王放的儿子每天望向窗外。
封控的春天恰好是鸟类求偶的高峰期。鸟类爱好者朱维佳察觉到,人变少后,小区里的鸟更加“肆无忌惮”了,为了求爱成功,到处有鸟在打架,“飞来飞去、撞来撞去,一个追、一个逃。”家住松江佘山镇的张雅娜是观鸟爱好者,她也感受到,鸟的胆子变大了,它们会飞入往常不会停留的低矮灌木中,例如樱花树。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看来,上海这座城市中鸟的种类和数量本身就多,是跟人类距离最接近的野生动物。它们受疫情影响明显——人不出去活动之后,原本只生活在园林绿地的稀有林鸟,很可能会扩大活动范围,飞进小区里。
过去,车辆噪音、人对鸟巢的破坏、对幼鸟的捡拾,都会影响鸟的繁殖。现在,何鑫有一个大胆的猜测:疫情期间由于受到了更少的人类干扰,鸟类能更自由自在地求偶、筑巢、孵蛋、养育,从而提升繁殖率。
除了常见的林鸟,天空中还更多地出现了猛禽的踪迹。自然教育讲师蒲川整日呆坐在飘窗前,平时他常带学生去湿地公园观鸟,封控时只能困于约16平米的出租屋里。那日,他正望着天,灰蒙蒙的,突然一群白琵鹭排成人字形列队,往北飞去,蒲川觉得惊奇,他意识到,自己难得地见证了它们的迁徙。

白琵鹭北迁。
张雅娜看到的是红隼和凤头鹰,无意中,它们从上空飞过,儿子拍到了,这些猛禽平时很少能在小区看见,它们过去只在辰山和天马山飞行和捕食。她猜想,“也许是人少了,世界安静了,它们扩大了巡游的范围。”
不过,上海封控期间城区的鸟是否增多,以及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还没有调查与研究结果。何鑫提到了另一个影响居民判断的因素——在正常活动期间,人们会去更远的野外观鸟,很少有人关注小区里的鸟。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疫情期间,何鑫和同事们在自然博物馆的公号上也策划了一场阳台观鸟活动,“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去发现现在周围野生动物是不是更活跃一点。”
每天在窗外,蒲川能见证数不清的珠颈斑鸠求偶“滑铁卢事件”。雄性斑鸠向雌性斑鸠求爱,发出一连串“咕咕”的叫声,并不停地打躬靠近。雌性斑鸠会摆出一点架子,迈着优雅的步子离开,雄性斑鸠则紧追不舍。
平日里,人和鸟的相遇通常只有一幕,封控意外地给了人们更多的时间,“长期跟踪它,就拍它整个生活史”,朱维佳说,“我很有乐趣。”隔离在家的一天,他看到一只鹊鸲正站在一棵竹子上,叼了满嘴的虫子,朱维佳想,它不把虫子吃下去,那准保要去喂小鸟了。
疫情时,他一度情绪低落,看到网上的视频,“各种各样困难的事情,老人就医、上门消杀。越来越害怕。”朱维佳一个同事的亲人,也因为救助不及时,在医院离世。后来,在小区里观鸟和拍鸟抵消了他的无助感。
那次,他花了两天时间,果然在鹊鸲活动范围附近找到了鸟巢,位置在一个油烟机的排风口。他发现,鹊鸲喂好小鸟后出来,还会把小鸟的粪便捡出来。他把这些画面都拍摄记录了下来。

鹊鸲飞进油烟机排风口。 朱维佳 图
“疫情似乎为‘人类世’按下了暂停键,让城市周围的动物‘夺回失地’。”何鑫说,“(但实际上)忙碌的城市生活,让大多数人忽略了身边那些共同分享着城市环境的生物。疫情让大家知道,其实很多鸟类,也是有可能出现在你自己家周围的,只是你之前不会注意。”
何鑫介绍,相比于哺乳动物,鸟类本就更擅长利用城市环境,例如珠颈斑鸠除了会进入居民区觅食,还经常在居民楼的空调外机平台筑巢。
在四五平米的阳台上,朱维佳种了月季花、薄荷、夏威夷竹和枇杷树,花死了,他没把泥土倒掉,地上专门留了五个花盆,盛着干土。每天从早到晚,有不少鸟来他家洗泥澡。好几次他正在阳台上浇花,鸟从背后飞过来了,见他转身便飞快溜走。
但“不幸”的是,前段时间因为缺菜,朱维佳把三个花盆种上了葱和丝瓜,现在鸟儿们只剩下两个洗泥浴场了。

朱维佳阳台上,原先的洗泥浴场已长出葱。
一起生活的城市
朱维佳没想到,能在小区里记录到貉的踪迹。
封控期间,可以下楼后,朱维佳把红外相机绑在了小区的棕榈树和竹子底部。视频画面里,一只貉出现在草地上,它的脸像浣熊,浑身披着乌棕色的毛发,肚子圆滚滚的,步子有些迟缓。
很显然,这是一只怀孕的母貉。母貉不断向一只刺猬走去,刺猬蜷成一个球,滚着想要离开。朱维佳以为貉想跟刺猬玩,直到貉用嘴巴叼住刺猬,被刺到后,不停地甩嘴巴,他才反应过来,原来貉想吃刺猬。
通过相机的记录,朱维佳逐渐掌握了貉的行踪:两次踪影,分别出现在凌晨2点和4点。
这是貉为了能在城市安家改变的作息,它们的藏身环境也从洞穴、墙根转移到了小区假山、墙体空隙和废弃下水道。

00:35
貉捕捉刺猬。(00:35)

朱维佳拍到的貉。
貉是乡土物种,是一种在上海生活了千万年的野生犬科动物。王放是关注城市生态的生物学者,2018年开始调研貉在上海的生活状况。他告诉记者,目前上海至少200个社区存在野生貉,最中心的分布点在城市西南方向,也就是松江、闵行一带。
“19世纪中叶,上海是河网密布的长江口冲积平原上一个不起眼的城镇,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界一带以及外滩,当时都是芦苇丛生、群鸟翱翔、走兽出没的湿地。现在上海变成了城市,只在崇明东滩、南汇东滩等少数区域还残存着相对自然的滩涂。”何鑫说,“城市诞生于荒野,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将荒野吞噬。但即便如此,城市无法将荒野的痕迹完全抹去,河流、野地、丘陵……这些残存在城市中的自然栖息地吸引着很多动物。”
王放说,提到上海,许多人不会想到,这个城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另外,上海江河很多,还有池塘、湿地,“所以两栖爬行动物和昆虫的数量也非常多。”
疫情期间,很多时候,朱维佳感觉小区成了动物的世界。刺猬的脚步声很响,“沙沙沙”,仿佛人走过落叶。两只刺猬相遇时喜欢斗气,它们将头顶在一起,发出“呼呼”的声音,可以僵持数分钟,直到有一方被恐吓得不行,掉头跑路。

两只刺猬脑袋顶在一起“互怼”。
相比之下,貉胆子很小。有一回,他见到小区步行道上有一只貉,貉发现他后,好奇地看了一眼,便溜进草丛里了。有时候,几只貉还会轮流蹭吃猫粮。
“它不挑食”,何鑫介绍,貉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也就是哺乳动物中,既能依靠自然食物生存,也能利用人类环境中诸如垃圾和被丢弃的饭菜这类资源的物种,这让它们能更好地“进城”生活。
2020年疫情时期,王放和研究团队监测到,“进城”的貉,数量激增。
他们在十五个公园和社区绿地放置了近百台红外触发相机,疫情后回收数据发现,四五月正值貉求偶、繁殖的高峰期,居民活动减少后,城市成为了貉的天地,它们沿着公路、小街道到处迁移。同时,因为很多区域生活垃圾管理粗放,“那个时候貉面对的是一个还能很轻易地得到猫粮,很轻易地吃到人的残羹剩饭的时期”,王放说,这也助推了貉数量的快速增加。

出生三个月大的小貉,从洞里探出脑袋打量王放手里的镜头。

松江一个小区的貉在吃市民投喂的猫粮。
一个更直观的观察是,原先小貉很害羞,比成年貉胆小很多,2020年以前,王放和团队成员多次想拍到小貉,但它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躲回洞里。但疫情期出生的小貉不怎么怕人,会直勾勾地冲到他们的脚底下,主动讨要食物或者打量人。
王放猜想,由于没有太多的人类活动干扰,小貉可以跟着父母探索一个人类和车辆都少得多的世界,因此更大胆了。
但到今年4月,关于貉的数据出现了一些变化。
王放透过红外相机收集到的数据看到,由于人完全封控在家,貉的数量反而可能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这两年疫情的区别,更进一步证明,其实它们是城市野生动物,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跟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并不是那种真正荒野意义上的、靠自己的本事完全依赖自然环境生活的动物。”王放说,“当人类投喂给流浪猫的猫粮和人类自己产生的湿垃圾都减少之后,貉也会陷入封城的困境中。”

黑夜中,松江一个小区里,两只貉在互相梳理毛发。
生存的尺度
四月中旬,在张雅娜的小区里,发生了人和貉的冲突。
最初,一个业主发现自家飘窗下有一个洞,便把洞堵上。可是,第二天又冒出新洞。于是,业主便在洞前架了一台相机,并在树上挂了个灯,整晚拍摄,最终锁定了打洞做窝的“真凶”。
视频中,貉从墙洞里探出头,朝着光亮的地方,张望一下,又转身跑向河的方向。
张雅娜了解到,业主很害怕貉,曾用铁丝网堵住洞,但因为貉的咬合力很强,最终把铁丝网咬破了。更令业主崩溃的是,貉似乎很满意这个住处,过了几天,监控画面里,又多了一个新伙伴。于是,这位业主直接使用上了封控“硬隔离”的铁网,后来的三四天里,再未出现貉的身影。

貉在观测周围环境,准备打洞。
“冲突主要源于不熟悉。”王放说,2020年疫情后,上海貉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快速扩散,当时居民的反应非常强烈,市长热线出现了大量投诉。
但是,过了一年,王放回访发现,原本激烈投诉的小区普遍安静了下来,当居民了解貉的习性之后,开始接纳它们的存在。
这让王放意识到,当貉的数量最初增多的时候,可能人们会反应激烈,但是随着野生动物数量稳定下来,人们逐渐熟悉它们,人与动物的关系可能又要发生新的变化。
在一次演讲中,王放提出,所有动物都需要一个适合生存的尺度。
螳螂需要的尺度跟一个舞台差不多大,坚持几个月不喷洒杀虫剂,不让剧毒的杀虫药附着在它的猎物身上,它就能够安全地度过夏天,继续帮助我们控制害虫;黄鼠狼需要的空间可能更大一点,跟一个会场差不多大,同时它们需要每隔一公里到两公里,就有一片会场这么大的绿地,这样它们可以一个一个城市岛屿之间跳跃,完成觅食和求偶。
“比如一个刺猬,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间就够了,因为它可以到处走,小区几个花园、几片绿地,其实就能够让两三个刺猬的家庭在那生活。”

王放带儿子在小区里夜观刺猬。
野生动物进入和适应城市生活,有不断收缩生存空间的迹象。貉是典型的例子,王放说,在自然界,貉有非常强的领域性,会驱赶闯入它领地的竞争者,活动范围达到一、二平方公里,但在城市,它们的生存空间需求缩小了二十分之一,一个十几公顷的小区环境就能够让三四个貉的家庭生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野生动物生存状况也会变化。曾经分布在上海的一些动物数量稀少,“比如小灵猫的数量大幅度下降,以前曾经多到可以到河沟里用脸盆去装的无斑雨蛙也消失了。”河岸硬化后,王放曾听说不少溺水的貉和刺猬的故事,“貉能游泳,但是直上直下的池子它们爬不上来,还是人帮忙把貉从水池里边打捞上来的。”
疫情期间,这样的现象更为明显,两个月频繁的消杀,让空气中弥漫着消毒剂的气味。王放观察到,小区里蝌蚪的数量少了很多,筑巢的翠鸟和萤火虫也消失了。
在担忧的同时,王放告诉记者,“保护”的意义有时被扩展了,“城市的国土功能主要就是满足经济发展、满足人的社会需求的地方,所以从法律法规上,没有在城市里建大的保护区。能够适应的动物留下来,不能够适应的消失一部分,这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对于那些有非常强适应能力的动物,人们反而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减少它们的食物,降低它们在城市的密度,“突出的是可持续,让它们能够更安全地、更长期地维持正常的数量和行为”,王放说。
而让城市里的动物与人共处,或许不需要有特别宏大的目标。让王放心心念念的,是一个叫作“生境花园”的项目——通过在小区里创造一些小池塘、小野地或者小湿地,让野生动物重新回到小区环境,“这其实是一个副产品。以前大家不会低着头去观察,这里到底有一种青蛙,还是两种青蛙,现在大家察觉到这些变化,能感受到小区环境变得更漂亮了,更愿意坐在旁边乘凉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就足够了。”
很多人会问王放,城市本来就是人生活的地方,为什么要恢复生物多样性?他想,这样的小小改变或许就是人和生物多样性最直接的连结,“让动物不经意地有一些活动的空间,也让人不经意地觉得更舒适一点。”
(文中人物杨程为化名,感谢姜龙、吕永林、李辰阳、周依、李明芝对本文的贡献)
责任编辑:黄霁洁 图片编辑:张同泽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