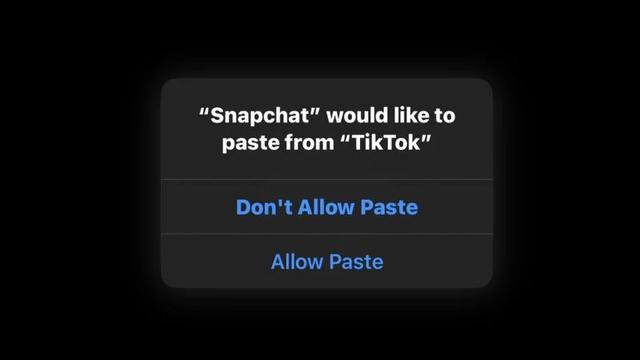春分刚过,一些地方却没有春意闹,也没有纸鸢翻飞,整个春天裂开了,在北国,冰天雪地,惟余莽莽;在南方,春江水暖,分外妖娆;而在人间,我看见一抹浓稠的“疫”郁。时光愈暖,静待花开时,唯念山河安,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香港、深圳、上海、吉林等一个个地方,像涟漪一样被波及.....人们被圈禁在春天之外,这本不该是春天的样子,但我们要相信,疫霾会褪去,而生活是向前的。一个人最了不起的能力,就是自愈力。
有一种马尾松,当伐木工人砍去它的枝条时就会发现,伤口处很快会流出一种含油的汁液。原来,受伤后的马尾松通过分泌油脂包裹伤口,来防止病菌的入侵,促进伤口快速修复,静默承受,慢慢痊愈。我们熟悉的胡杨,不也是一样吗?丢失了这半个春天,我们还有下半个春天;就算失去这整个春天,我们还有下一个春天。但你不能就此打住,正如高尔基曾在《童年》中所写:“生活就是一团美丽的蕾丝边,但旁边坐着的,却是一位老妇人。”打住了,你就停止生长了,你就老了。
短短三年,很多城市永失休闲。
你现在很难听到这样的对话了。
“大爷,一天搓两把不?”
“搓,一天两把,上午四五个小时,晚上四五个小时。”
“以后最好不要搓麻将了哈~”
“不能搓麻将那还有啥子耍头哦?”
可又能怎样呢?活在当下,也是意味着接纳,拥抱生活的不易和苦难。这个时候,需要的依然是那种豁达幽默和烟火气,只不过,一个人独处,在慢悠悠的茶香里,酝酿光阴。
像孩子们样,那种不知愁的天真神情和事事满足后淡淡的颓废杂糅合在一起,就像成都人骨子里那种闲适,这种闲适不是用钱堆起来的,而是乐观却不散漫。
这个残余的春天,许多城市的人们像遭了霜的茄子一样,那憋屈感,急需另外一种姿态跨越“倒春寒”回归常态生活。

林语堂先生说:“春天要做三件事,赏花、踏青、喝西湖龙井。”
春天最迷人的地方,在于给我们新生的希望。
在经历上半个春天后的我们需要治愈也需要自愈。
说起赏花,之前这个时节,很多人会去远方,到婺源去看油菜花,去武大看樱花,去桃花源看桃花,去韶山看映山红,春天的花数不尽数,茶花、杏花、那种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流连忘返。现在深圳开得最热烈的是黄花风铃和木棉花,前者的话语是“感谢”,后者的话语是“珍惜身边的人”。深圳的疫霾还未完全散去,由衷感谢抗疫的每一个人,也由衷希望每个人都能珍惜身边的人。

赏花,是一件老少皆宜,男女都爱的事情,有趣,且陶冶性情。宋代著名词人,湖南的赵葵有一首七言绝句《赏花》把宋时人们赏花的那种欢趣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
“人乐清明三月天,也随人赏万花园。
偷闲把酒簪花去,不似儿童笑语喧。”
赏花,其实是一种文化。在古时,有诸多赏花的讲究。归纳起来大体为四种:观“色”、闻“香”、品“姿”、赏“韵”。
观花“色”,绝美为艳。古人赏花首先是看花之色。玫瑰的红,菊花的黄,玉兰的白……无不令人赏心悦目,古人称之为“养眼”。什么样的花色最为绝美?古人以一个“艳”字作了概括。何谓艳?就是色彩鲜明。我们可以从留下来的诗句一窥究竟。在春天,花之艳是红色,“万紫千红总是春”。《诗经·周南》中的《桃夭》诗篇首即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古人为何喜欢桃红?或与女人有关。北宋诗人林逋《杏花》诗称:“蓓蕾枝梢血点干,粉红腮颊露春寒。”
闻花“香”,花分九品。花之美在乎“色”,亦在乎“香”,所谓的“国色天香”,缺一不可。春有梅香,花之香至极品,则称为“天香”,与生俱来,美如天然。明代张谦德《瓶花谱·品花》中,将花卉之香分成九品,其中第一品有9种,兰花为一品之首,后面依次为牡丹、梅、细叶菊、水仙、滇茶、瑞香、菖阳。宋陶谷《清异录·草木门》“香祖”条称:“兰虽吐一花,室中亦馥郁袭人,弥旬不歇,故江南人以兰为‘香祖’。”

赏花“姿”,形势第一。赏花除了色与香,还要看花之风韵,用清朝画家松年的观点来说,叫“花以形势为第一”。自称“梅妻鹤子”的北宋诗人林逋对梅花的色、香、姿都有独到观察,他在《山园小梅》诗中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在明清以来,人们喜欢斜姿曲势的梅花,近乎病态。清龚自珍《病梅馆记》文提到了当年江浙人的赏梅观是:“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

品花“韵”,寻花品质。古人认为,“不清花韵,难入高雅之境”。先秦时孔子即喻兰花为“君子”。北宋苏东坡《题杨次公春兰》称:“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时闻风露香,蓬艾深不见。”或喻为“妙姬”“丽人”,如南朝宋鲍照《芜城赋》称:“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质兰心,玉貌绛唇。”
总而言之,赏花是一件雅俗共赏的事情,不同人不同境界,不同见底,欢喜则好。待解封之时,到满园春色里尽情撒欢吧!

再说踏青。古代“白富美”踏青:铺席藉草,围坐一圈。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朝的京城长安,每逢春天,仕女们郊游踏青,路上遇到好花,就在花前铺席藉草,围坐一圈,并插杆结索,解下身上的红裙递相垂挂,权当作野宴的帷幄。在今天许多地方,这是个奢侈的事情,因为疫情,保持社交距离,不能聚在一起。古代“文艺青年”踏青:自带酒菜,厨师相随。《浮生六记》就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古时踏青赏花,大都是文人雅士的癖好。而文人雅士很重面子,提着锅碗瓢盆去踏青赏花,不仅麻烦还有失格调。于是苏州的文人们就想出了一个点子,请了一个卖馄饨的跟随他们一同踏青。带着酒菜、炊具去赏花,既解决了生活难题,又别有一番野炊之趣味,实在很像“文艺青年”们想出的妙招。古代“单身男女”踏青:借助郊游,成就良缘。自古封建礼教严苛,男女授受不亲,而唯有郊游期间暂时废除了那些礼数禁锢,男女可以自由交往,这些单身男女们哪能放过这一年一次的求偶良机,所以踏青春游往往就会成就一段段佳偶良缘。据说这种求偶式郊游最先是兴起于先秦时代。
今时今人,亦可以效仿古人,约三五个中意之人,既可探花撩草,又可成就一段良缘,岂不美哉!

喝西湖龙井,是春天里最动人的时光。
清朝的刘瑛一首《谢龙井僧寄茶》诗,将西湖龙井写到妙处。“春茗初收谷雨前,老僧分惠意殷虔。也知顾渚无双品,烦试吴山第一泉。竹里细烹清睡思,风前小啜悟谈禅。相酬拟作长歌赠,浅薄何能继玉川。”
西湖龙井号称“绿茶皇后”,是绿茶中的天花板。龙井分“狮”、“龙”、“云”、“虎”、“梅”五个品号,其中,以狮峰龙井为最。所谓“天下名茶说龙井,龙井上品在狮峰”那里可是有乾隆亲封的十八棵御茶树。茶好,除了产地以外,时间尤为重要,“明前茶,贵如金”就是最好的诠释。稀有,大自然限量,口感也是一级棒。有提神、生津、清热、利尿之效,但茶性寒,脾胃虚寒者,少饮。

不识茶,谈不上喝茶。西湖龙井茶,有着独特的气质。外形扁平挺秀,色泽翠绿,内质清香味醇,泡在杯中,芽叶色绿。素以“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四绝著称。

好茶要好水。自古以来,便讲究好茶配好水,方能知茶味。《茶疏》中说:“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这里的“无水”是指没有好的泡茶之水。明代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中写到“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茶性受水质的影响,若是用好水来泡茶,可以最大地释放茶的特质;反之,即便是再好的茶,用品质不好的水来冲泡,茶性也不会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提到:“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地慢流者上。”,煮茶的水,用山水最好,其次是江河的水,井水最差。山水中,乳泉、石池这种流动慢的水为最佳。

学会了识茶和识水,最后就是泡茶了!泡西湖龙井,今人一般用透明的玻璃杯。用玻璃杯冲泡可观察到茶在水中缓缓舒展、游动、变幻。冲泡后芽尖冲向水面,悬空直立,然后徐徐下沉,如春笋出土似金枪林立。可采用上投、中投、下投三法,水温在85摄氏度左右。等茶汤明绿,倒入公道杯使茶汤均匀即可。然后再分到品茗杯中观色、闻香、啜饮,其中滋味,如人生况味。
写在最后人生,时而喧闹,时而寂寥,起落变化,有傲霜,亦有寒彻骨;有迎风,亦有扑鼻香。当我们折腾得累了,想生活的时候,我们或许还可以逃离回乡村,在乡村的阡陌中走一走,踩着潮湿的泥土,闻着春天花草香,把那些该死的纷纷扰扰都抛掉,做一个渔耕樵夫。无论何种,出去走一下,在残余的春天里,赏花、踏青和喝一碗鲜爽甘甜的明前茶,才算不枉度此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