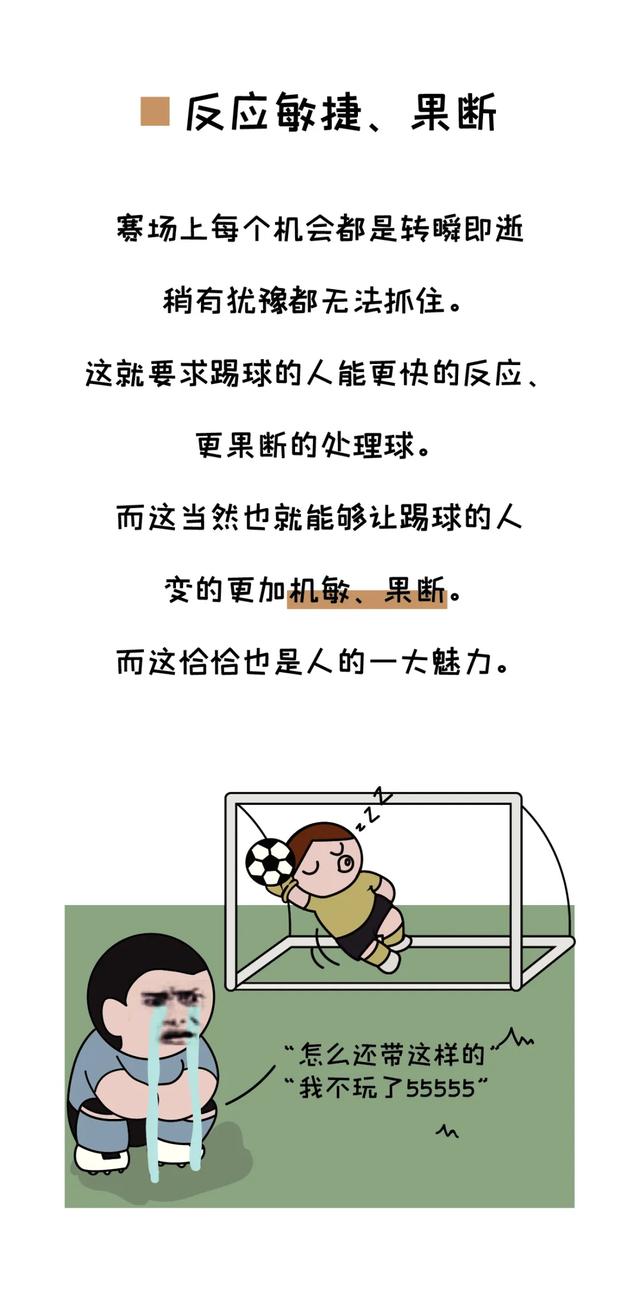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两国关系非常友好,在这一大背景下,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研制提供专家技术、留学生名额,以及实物、模型等。1958年4月,赫鲁晓夫向毛泽东同志建议在中国建长波电台,7月又提出要建联合潜艇舰队,都被毛泽东同志拒绝了。毛泽东同志说不允许外国的军事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友邦如此,敌对国就更不要说了。那么随着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越来越大,1959年6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终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苏联专家陆续撤回国内,技术图纸等也都一并带走了。截至“协定”终止,苏方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导弹的实物,但是原子弹的教学模型直到最后也没能落实。中苏关系闹僵以后,苏联方面称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我们中国当然不能示弱,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当然只有气概是不行的,还要有谋略。于是中央向有关方面下达指示,苏联人靠不上了,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最后实践证明我们没有用那么长的时间。
上图离我们最近的两个人,左边是彭桓武在爱丁堡大学的导师马克斯·玻恩,195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右边是埃尔温·薛定谔,他是1933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留学期间,彭桓武曾在马克斯·玻恩的推荐下两度在薛定谔的手下从事研究工作,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对彭桓武的科研能力高度赞赏。但是我们看的这张照片是马克斯·玻恩和他的同事及学生的合影,里面并没有彭桓武,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回国了。有趣的是其中包含着另一位“两弹一星”勋奖章获得者,在第二排左边,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程开甲院士。所以在马克斯·玻恩那儿,程开甲是彭桓武的师弟。照片第二排中间那个人,他也是一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北大教授、物理学家——杨立铭先生。既然说到杨立铭先生就顺便多说一句,他的夫人也是一位院士,是我们国家计算机科学的开创人之一夏培肃。据初步统计,我们中国科学院有13对院士。
接下来再介绍一个人。原子弹爆炸的过程涉及到许多力学问题,1960年,钱三强请钱学森推荐这方面的负责人选,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当时的钱学森是力学所的所长,而郭永怀是副所长,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早在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他们都是著名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学生。郭永怀比钱学森大两岁,但是按拜入到冯·卡门的门下,去加州理工念书的时间来算,郭永怀比钱学森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学森算得上是郭永怀的辅导师。因此,钱学森对于郭永怀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的科研工作非常了解,并发自内心地欣赏他的科研精神。钱学森在一篇怀念郭永怀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郭永怀之所以能做出这两项重要成果,是因为他有见识,遇事看得准,而一旦看准,就有胆量去攻关。当然这是我们从旁见到的,我们也许看不到的是他刻苦的工夫、呕心沥血的劳动。”
1960年5月,郭永怀在担任力学所副所长的同时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西北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不幸因飞机失事壮烈牺牲。我们之所以用壮烈来形容,是因为当时飞机已经到达北京上空,在距离地面几百米的地方突然失火,后来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两具遗体被分开以后,人们发现郭永怀的公文包就夹在两个人中间。生死关头,他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工作。

上图是1988年郭永怀牺牲20年之际,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在院落内安放郭永怀塑像时拍摄的照片。王淦昌、彭桓武都来参加了这次塑像揭幕仪式,以向他们昔日的战友致意。另外参加的人还有“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和陈能宽院士,最中间的是一位军人,名叫李觉。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都是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而所长就由这位李觉将军来担任,因为核武器研制本质上是由军方主导的一项工程。郭永怀在世的时候常对他的学生讲:我们这一代,你们以及以后的两三代,要成为中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通过刚才以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为例讲述的一些故事,大家不难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其实不只他们三个, 23位“两弹一星”元勋绝大部分都有留学经历。下面这张图展示了他们在国外大概待了多长时间,计算方式是回国时间减去出国时间,名字与时间相对应。

红色字的名字是念了博士学位后回国的,蓝色字体说明是硕士学位,而黑色字体是在国外做访问的。
上面一共列了21个名字,23位元勋当中只有于敏、钱骥两位是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当然,没有出国留学不等于贡献小。在国家卫星研制初期,钱骥协助赵九章在协调各大部委的需求、国家卫星研制的规划方面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于敏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我们国家氢弹理论的突破就是由于敏完成的。于敏在自传中说过这样的话:“时代的使命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于敏起初醉心于理论物理的基础研究,但钱三强跟他谈过之后,他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根据国家需要选择研究方向。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大批中国科学家特别是核物理学家从国际学术界消失了,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星消失在他们过去的灿烂天空里,他们被民族的声音召集在一起,隐姓埋名,把理想和智慧,一腔热血都奉献给了“两弹一星”这个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作者:何林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
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独家文稿《何林:请历史记住他们 ——“两弹一星”研制给我们的启示》
全文链接:http://www.71.cn/2019/1023/1063623_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