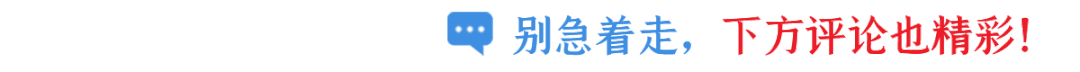本文源自于《书法研究》总第140期
作者 张国宏
[内容提要]
王羲之以其对中国书法无与伦比的贡献,取得了难以动摇的“书圣”地位。王献之审时度势,继续沿着古质今妍的道路发展,并开创实用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行草体,终于也取得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在此框架内,从历史机遇、传世作品、精神气质、书法风格、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六个方面对二王父子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 古质今妍 内擫法 外拓法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小字阿菟,山东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费县)。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父子俩生卒年代都有争论,现在一般采用唐代张怀瓘《书断》的说法。
琅邪王氏是西晋的豪门大族。王羲之的祖父王正,曾任尚书郎。叔祖王澄任荆州刺史。父王旷做过淮南、丹阳等地的太守,曾参与朝廷大计,是晋王朝南迁的策划者之一。王羲之的堂伯王敦、堂叔王导都做过丞相,堂叔王廙官至荆州刺史。当时社会上有“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的说法,就是因为王氏家族初过江时是一枝独秀,从将军、尚书到刺史、丞相,位居要职者,高达二十多人,基本上垄断了朝廷的政治和经济大权。王家还通过联姻,不断巩固家族的地位。如:王羲之娶了太尉郗鉴之女郗璿,他们的次子王凝之娶了丞相谢安的侄女谢道韫。王献之与表姐郗道茂离婚后,与简文帝之女新安公主结婚,成了驸马。他们的女儿神爱公主后来被晋安帝立为皇后。
二王父子仕途都很顺畅。王羲之二十二岁开始走上仕途,当上秘书郎。二十八岁任江州临川郡太守。三十二岁任征西将军庾亮的参军、长史,后又升迁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四十六岁时,经好友殷浩推荐,任护军将军。后又转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人称他为“王右军”。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献之“起家州主簿”。后又历任建威将军、谢安长史、吴兴太守。二十九岁与简文帝之女新安公主结婚。三十五岁时“征拜中书令,”故后人称他为“王大令”。四十三岁献之死于任上。
王氏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地位显赫,而且因书法人材济济而蜚声书坛。
王羲之的父辈王旷、王敦、王导、王廙皆有书名。《淳化阁帖》中有王敦、王导、王廙书迹。王羲之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据史料记载,他七岁开始习字,不久就师从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卫夫人。卫家也是名门望族,世代善书,卫夫人擅长楷书,并有书论《笔阵图》传世。同时王羲之还向叔父王廙学习书法,南朝宋书家羊欣《采古今能书人名》称王廙“能章楷,谨传钟法”,与卫夫人同以擅长钟繇楷法而名扬四海。王廙见侄儿“书画过目便能”,大为惊讶,发出由衷的赞叹:“余兄子羲之,幼而歧嶷,必将隆余堂构。”(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王献之学习书法的条件更为优越。他五岁就开始学习书法,卫夫人(卫铄)还特意书写一篇《大雅吟》送给他。此时王羲之已四十六岁,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王羲之亲授爱子,并亲书《乐毅论》作为范本。王献之天资过人,从小深得羲之赏识。相传献之七八岁时,其父出其不意,从其背后拔其笔杆,意在试其笔力如何,献之笔不脱手,羲之叹曰:“此儿后当有大名。”王献之十岁时,还随父亲及两位哥哥(凝之、徽之)参加了兰亭盛会。
王羲之有七子,依次为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称他们“皆得家范,而体格不同,是善学逸少书者。······逸少之书,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中当以献之得其源为高,因为献之得源之后,继续变化发展。除父兄外,对献之书法产生影响的人还有很多。外公郗鉴、母亲郗夫人、舅父郗愔、郗县、从父王恬、王洽、王劭、王荟、嫂嫂谢道韫、保母李如意皆有书名。
自二王父子步入书坛,千百年来中国书法便与之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二王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本文将从历史机遇、传世作品质量与数量、精神气质、书法风格、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六个方面对二王父子进行比较研究。
历史机遇比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各体书法交相发展,并日趋成熟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蜕变时期。它是在汉代书法发展的基础上,完成了汉字书体的演变,篆、隶、真、行、草,诸体俱备,日益完善。
魏晋时期的隶书,已经走上了程式化的道路,艺术魅力迅速下降。它的字形偏扁,横向取势;收笔又朝上作分势,对直行书写来说,很不方便,隶书被楷书取代是势在必然。
楷书演变的成功离不开钟繇、王羲之这两个承前启后、巍然卓立的大书法家的杰出贡献,钟繇“从“法”字上改变尚扁尚平的字体,从章法上改变行近字远的布白,从笔法上改变蚕头雁尾的书写方式,把隶书的整齐方正的美变为楷书的纵横可象的美,韵味更浓更淳。”①钟繇的楷书已经很成熟,十分古雅。所谓古雅也就是稍带隶意。王羲之楷书主要得力于钟繇,然后“增损古法,裁成新体。”(张怀瓘《书断》)也就是去掉了钟书中的隶意,创造出遒美流便的今体,使楷书完全成熟。
魏晋时期的行书也在隶楷的递变中,由发展走向成熟。行书大约起源于东汉后期,相传为东汉的刘德昇所创造。实际上行书在其形成过程中,有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向:其一,它是在由隶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这是一种在民间流行的非隶、非楷的简捷的手写体,可称作“前期行书”。其二,是在隶书演变成楷书之后,由楷书简捷流便写出来的书体,这是一种基本脱尽隶法的行书,可称作“后期行书”。当时的行草书,虽然都已初具规模,但不同程度上都带有隶书的烙印,能将前期行书与后期行书有机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一种完全成熟的书体的杰出代表就是王羲之。行书经过王羲之的创新,变古质为今妍,形成了一种俊逸、雄健、流美的书风,对书法艺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随着楷书取代隶书,今草取代章草也是必然的趋势。东汉开始流行的章草,到了西晋时逐渐起了变化,即向今草转化。到了东晋,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东晋书家提纯了今草的写法,主要也是去除了隶意,加强了使转,使其笔势连绵不断。在结体和线条的把握上,非常准确精到。王羲之的草书平和洒脱、典雅飘逸,艺术水平极高。
世上万物大都始于渐变,而终于突变,书法亦然。在各种书体演变过程中,是王羲之抓住了书法发展的脉搏,推动了字体的突变。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它既需要历史机遇,更需要超人的智慧、非凡的勇气、杰出的创造力。所以,当王羲之将自己的艺术活动与时代需要紧密结合时,就创造出了惊人的艺术成就。
王献之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他比王羲之小四十多岁,到他成年时,各种书体的演变,基本上已由其前辈书法家完成了。从东汉到东晋几百年间,书法创作很繁荣。唐朝张怀瓘《书断》列为神品书家的二十五人中,大都为魏晋南北朝书法家。唐窦臮《述书赋》所说的“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就是指当时东晋王朝王、谢、庾、桓四大名门中的二十一位书法家。这时期可以永载史册的书法家有:杜度、崔瑗、张芝、蔡邕、梁鹄、刘德昇、钟繇、卫觊、韦诞、卫瓘、索靖、皇象、卫夫人、王羲之、谢安、王献之、王珣等。为什么与王献之同时期的书家能上榜的寥寥无几呢?就是因为前辈书家历史机遇比他们要好,作出的贡献也比他们大。
王献之的前辈中还有一位叫王洽的堂叔,他是丞相王导之子,又是《伯远帖》书写者王珣之父。王家后代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在其《论书》中称:“亡曾祖领军(王洽)书,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变古制今,唯右军、领军,不尔,至尽犹法钟张。””实际上,已将王洽放在仅次于王羲之的地位。张怀瓘《书断》称:“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宛转,大行于世。”也充分肯定了王洽对书法变革的重大贡献。由此可见,虽然王献之与其父辈前后只相差几十年,但他们的历史机遇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传世作品比较
王羲之虽然没有真迹传世,但唐代摹本及各种刻本非常之多,而且质量非常之高。举世瞩目的《兰亭序》,它的各种摹本、刻本完全可以开设一个《兰亭序》博物馆了。唐代摹本,在大陆及台湾的有《寒切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平安三帖》(《修载》、《何如》、《奉橘》三帖)、《远宦帖》、《神龙本兰亭序》等;在日本的有《丧乱》、《二谢》、《得示三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著名的刻本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十七帖》、《定武兰亭》、《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兴福寺碑》等,北宋《淳化阁帖》中《旦极寒帖》、《近得书帖》、《昨书帖》、《建安灵柩帖》、《追寻伤悼帖》、《适重熙帖》,以及北宋《宝晋斋帖》中的《王略帖》、《裹鲊帖》等。
“二王”书法墨宝,经历了桓玄失败与萧梁亡国两次灾难,损失非常严重。唐初,唐太宗尽力收藏,内府藏品数以千计。但因唐太宗褒羲之,抑献之,致使王献之的书法有的被隐去名字,有的被改作他人作品,又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所以,现存的王献之书法珍品较少。王献之著名的书迹,有墨迹本《鸭头丸帖》,唐代摹本《廿九日帖》;刻本《洛神赋十三行》、《十二月帖》和《授衣帖》。王献之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地黄汤帖》、《送梨帖》、《东山帖》、《鹅群帖》、《兰草帖》、《舍内帖》、《保母砖志》等。
书法作品的流传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但它又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它也是决定书家社会地位的因素之一。从作品流传情况看,王献之传世书法的质量与数量实在是无法与其父亲相提并论。
精神气质比较
二王父子都具有超凡的精神气质。《晋书·王羲之传》称王羲之“幼讷于言,人未奇之。·····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大凡少时沉默寡言者,多深沉而善思想者,这一类性格发展成为“骨鲠”也是合乎情理的。《王羲之传》记载了两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王)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为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袒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此正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 以女妻之。”如此不拘礼法,充分显示了王羲之“骨鲠”的性格。
王述与王羲之皆为名士,但王羲之看不起他。“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王羲之从本性出发,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也如此不屑一顾,完全不考虑政治前途,一代名士的傲骨显露无遗。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中也记载着几个关于羲之的故事。“羲之罢会稽,往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值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书坏。'王云:“但言右军书字,索一百。”'人市,市人竞市去。妪复以十数扇来请书,王笑而不答。”又“羲之性好鹅,山阴县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往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亿甚盛,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棐床几,至滑净,乃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还家,其父已刮尽,生失书,惊懊累日”。从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王羲之的洒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极其自然的,这是一种只有真正名士才具有的风流。
《晋书·王羲之传》称王献之“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献之也深得名臣谢安赏识,据《世说新语·品藻》记载,王黄门(徽之)兄弟三人诣谢公(谢安)、子猷(徽之)、子重(操之)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问:“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晋书·王羲之传》记载:“谢安甚钦爱之,请为长史,安进号卫将军,复为长史。”
王献之遇事不惊,从容不迫,很有名士风度。《晋书·王羲之传》记述:“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净。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虞龢《论书表》记述:“王子猷(徽之)、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之敬神色怡然,徐唤左右扶憑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王献之才高气盛,不畏权贵,而且敢说敢为。据虞龢《论书表》记载:“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耳。”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张怀瓘《书断》称:当时人们向王献之求书法,很少有人如愿,“虽权贵所逼,(献之)靡不介怀。”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谢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魏仲将(诞)悬凳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王献之做过谢安长史,能如此直言,确属不易。
王献之又很有傲气,但有时不守礼法,近于佯狂。刘谦之《晋记》称:“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世说新浯·忿狷》:”王公(献之)诣谢公(谢安),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谢安之侄)曰:子敬实自清立,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谢安对他的批评也可以说不轻了。《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时辟疆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旁若无人。辟疆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屑意。”从以上两例子看,献之对人傲慢,有时确实有些出格了。
书法风格比较
二王书法的共同之处都在于表现了艺术内容的实在性、表现方式上的理智与客观。我国古代书法始终沿着一条从繁到简、从质到妍的道路发展。虞龢《论书表》说:“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王羲之书法把握住古质今妍的发展规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王献之书法的可贵之处则在于能沿着古质今妍道路继续发展,并能冲破父亲的藩篱,自创风格。他那疏旷不羁的性格,反映在书法上就是更加宏逸开张。可以说,王献之是当时古质今妍转变中走在最前列的人。羲之和献之相比,羲之为古,献之为今。前人称献之“变右军书为今体”,也就是这个道理。对二王书法风格,黄庭坚曾有妙喻:“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如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山谷题跋》)王羲之书法含蓄灵和、内涵风骨,如《左传》述事精妙优美,得“立言高标,著作良模”之称;王献之草书纵逸豪迈、风流俊美,似《庄子》为文恣肆,意到笔随,有“汪洋辟阖,仪态万方”之誉。黄庭坚以左氏、庄子比作二王,甚为确当。
要分清二王书法的差异,一定要分清内撅法与外拓法的区别。大凡笔致紧敛,是内撅所成;反之,必然是外拓。王羲之书法“刚健中正,流美而静”,使用的是内擫法;王献之书法“刚用柔显,华因实增”,使用的是外拓法。沈尹默强调“内撅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为筋(筋力)胜之书。······内擫近古,外拓趋今,古质今妍,不言而喻”。(《二王书法管窥》)我们如果把二王书法中的楷书《乐毅论》、《洛神赋十三行》与草书《十七帖》、《十二月帖》进行一番比较就能看出内撅与外拓的差别。王羲之的书法笔致紧敛,转折处以顿笔方折居多,故刚健中正,其特征是动中有静;王献之的书法笔致放纵,转折处提笔暗过,以圆转居多,动态特征更加明显。
历代名迹中,凡学大王者,用笔多内撅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学小王者,多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欧阳询行书《梦奠帖》取法大王《何如帖》之类作品,为典型的内撅法;《中秋帖》节临王献之《十二月帖》,为典型的外拓法。。唐太宗的《晋祠铭》取法大王较多,以内撅法为主;而其《温泉铭》取法小王较多,以外拓法为主。《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刻碑在武则天时期,怀仁忠实地摹刻王羲之书法,所以内擫特征明显;唐大雅集王羲之《兴福寺碑》刻碑在唐玄宗时期,大雅集字是采用临摹结合的方法,相对较随意,字体也稍放纵。所以,同样是集王羲之书法,两碑的风格差异就很明显了。
历史贡献比较
王羲之被尊为“书圣”已有一千多年了,这不仅是因为他达到了其他书家难以企及的绝对高度,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书法的巨大影响和卓越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王羲之通过艺术手段,使汉字的真、行、草三体形成了独立机制。从王羲之的师承看,他得益于带有隶意的前辈书法;而他的贡献却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开一代新风。他基本上清除了点画、结构和章法上的隶书痕迹,把楷书和行书推向成熟。
第二,是王羲之将真、行、草三体高度艺术化,达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他根据当时东晋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趣和思想感情,将汉魏以来凝重质朴的书风,变成了流丽而遒劲的新体,他的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这些书体都大大超出了同时代书家的水平。故张怀瓘《书断》赞曰:“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非自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王羲之书法中高度成熟的、极富变化的笔法、结构和章法,已成为后世百代师法的楷模。
王献之对书法的贡献,首先是对王羲之所创造的新体继续进行改造,也就是将王羲之笔致紧敛的内撅笔法,演变成为纵逸流畅的外拓笔法;将王氏书法演变成为笔迹流泽、婉转妍媚的新体裁。王献之对书法艺术有很强的感悟能力,又有创造性的见解,早在十五六岁时,他就建议其父亲改体:“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张怀瓘《书估》)实际上,王献之向父亲所建议的道路,正是中国书法顺应古质今妍发展的道路,是一条推陈出新的道路。沈尹默先生指出“内撅近古,外拓趋今,古质今妍,不言而喻”。(《二王书法管窥》)二王书法相对于前人,有古今之别;而父子相比较,又成新的古今。果然,在王羲之去世一百多年后,世人嫌王羲之的书风古质,将兴趣转向“用笔外拓而开廓,散朗而多姿”的王献之书法。对这种现象,也就是虞龢所说的,“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当然,王羲之能成为“书圣”,是靠其书法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但要说起弘扬王氏一门书法,是离不开王献之的杰出贡献。
其二,王献之在继承父风的基础上,创制了一种新的行草书,也就是神峻流畅的“大令体”。这种行草书体,打破了书体的界限,流便简易,可草可行。它随意而书,并能传情达意,给书写者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张怀瓘在《书议》中写到:“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王献之所创行草书体,虽然不能与真、行、草、隶、篆这些大书体相提并论,但它能使二王书法体系进一步得到充实完善,是一种非常实用的书体。王献之所创的书风,也正是东晋以来书家所追求的一种新的书体风格。张怀瓘称其笔法和体势,是当时“最为风流者也”。后来自晋末到六朝,书家都崇尚这种新书风,使献之名声更加显赫。
历史地位比较
王羲之书法成功之后,引起了朝野各阶层人士的心理共鸣与崇尚,包括那些书法世家的子弟,也都学习王字。据虞龢《论书表》记载,当时大书法家庾翼在荆州为官,见庾家子弟,不继承家传而学右军,愤愤不平地说:“小儿辈乃贱家鸡而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后来他在其兄庾亮处见了王羲之给其兄的书信,乃叹服,并写信给王羲之:“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是“四庾”之一,书名原在右军之上,右军书法能使其内心折服,确属不易。
王羲之书法取得了他人难以比拟的成功,但其确立书坛盟主地位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整个南朝学习王献之书法的人众多,王羲之的地位受到了儿子强有力的挑战。根据史料记载,晋末以来乃至整个六朝,都崇尚华美的书风,使王献之书名大显于世。南朝书家孔琳之、羊欣、谢灵运、薄绍之、王僧虔都以学习王献之为主。
梁代陶弘景《与梁武帝论文启》称:齐梁之间,“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梁代袁昂《古今书评》称:“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鼎能者并不超过冠世者。这种情况要到梁武帝赞扬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古今书人优劣评》)以后,才有所改观。
隋代智永主要取法王羲之,又在钟繇《宣示表》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清代何绍基指出:“右军书派,自大令已失真传,南朝宗法右军者,简牍狎书耳,至于楷法精详,笔笔正锋,亭亭孤秀,于山荫棐几,直造单微,惟有智师而已。”(《东洲草堂金石跋》)智永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大王法多于小王法,并直接对初唐书法产生影响。
唐初,唐太宗崇尚大王书法,对王羲之地位进一步的确立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还亲自写了《王羲之传论》,太宗把王羲之与钟繇、王献之、萧子云作比较时,极大地肯定了羲之的书法成就,他称赞羲之“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把王羲之凌驾于所有书家之上。帝王为书家撰写传论,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同时他还贬低了王献之,“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如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枒而无曲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唐太宗作为一代帝王如此褒扬王羲之,贬低王献之,其影响是非常大的,以至于出现把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作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的怪事。初唐孙过庭草书师法大王,成就很高。他在《书谱》中写到:“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惑疑也。”他认为王羲之书法之妙在于“思虑通审,志气平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而子敬以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孙过庭的观点非常鲜明。《书谱》作为初唐最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其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李嗣真在其《书后品》中盛赞美王羲之书法:“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廓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谷卷舒,烟空照灼······可谓飞白之仙也。”从此以后,王羲之头上有了“书圣”的光环。
盛唐、中唐时期,以张旭、颜真卿的成功为标志,书风向雄健豪放方向发展。书法的艺术标准和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变化。杜甫诗句“书贵瘦硬方通神”是张旭、颜真卿之前的旧标准;苏东坡诗句“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不公吾不凭。”则是张旭、颜真卿之后的新标准。当时书家已多用外拓法,王献之书法地位也随之日益提高。所以出现学习草书者,无不学大令的现象。唐代李嗣真高度评价王献之草书的同时,首先提出王献之的草书超越了王羲之。《书后品》称:“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唐代杰出的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对二王书法作了长期的,也是最为详尽的比较研究。天宝十三载(754)他在《书估》中称:“如小王书所贵合作者,若藁行之间有与合作者,则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子弟尔。···..·可谓子为神俊,父得灵和。父子真行,固为百代之法。”能提出“家尊才可为其子弟”,在当时是需要极大胆魄的。乾元元年(758)他的《书议》又将二王作了比较:真书逸少第一,子敬第四。行书逸少第一,子敬第二。章草逸少第四,子敬第七。草书子敬第三,逸少第八。他还评论:“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同时他大胆批评王羲之“草书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也”。也提出王献之的草书超越了王羲之。贞元三年(787)张怀瓘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书断》,他将二王的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皆列为神品。同时作了概括总结:“子敬真不逮父,章草亦劣。然观其行草之会,则神勇盖世。况之于父,犹拟抗行(衡),比之钟、张,虽勍敌仍有擒盖之势。·····其间备精诸体,唯独右军,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逸少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观点有了明显的转变。
南唐李煜称:“子敬俱得右军之体,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六)以李后主之性格,不喜欢王献之纵逸的书风,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宋代是一个“尚意”书风盛行的时代。所谓尚意,旨在摆脱束缚,主要是摆脱书法法度、技法对书家性灵的束缚。王献之的书风也因此得到了宋代书家的高度重视。宋四家中,米芾受王献之影响最大,《宋史本传》称其:“妙于翰墨,沉着飞翥,得王献之笔意。”黄庭坚的草书也从王献之书法吸取养分。所以他们二人对王献之的评价也最高。米芾《书史》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黄庭坚《山谷题跋》则称:“右军草书入能品,大令草书入神品也。”
元代书坛盟主赵孟頫高举师法晋唐的大旗,但他主要是研习王羲之的行书与初唐诸家的楷书。元代能见到的王献之书迹已非常之少,元以后所谓学王者实际上多为学赵者。所以自元以后,王献之的地位再也无法与其父相比了。
王羲之以其精湛的书艺,以及对中国书法无与伦比的贡献,取得了“书圣”的称号。千百年来,书家多以王羲之书法为最高的典范。但纵观历代书家成功经验,凡学习王羲之书法者,基本上都兼学王献之。除了南朝书家,隋唐以后的智永、欧阳询、虞世南、李世民、孙过庭、杨凝式、米芾、黄庭坚、赵孟頫、鲜于枢、董其昌、王铎、何绍基等也都在王献之书法上下了很大的工夫。这除了审美趋向有了改变之外,献之行草书比羲之行草书比较容易上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这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因为王献之对中国书法的贡献是确实是无法与王羲之相提并论的。
王献之对书坛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能审时度势,继续沿着古质今妍的道路发展,并开创实用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行草体,终于与其父并称二王,成为继王羲之后,我国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二王的成功,对千百年来的中国书坛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