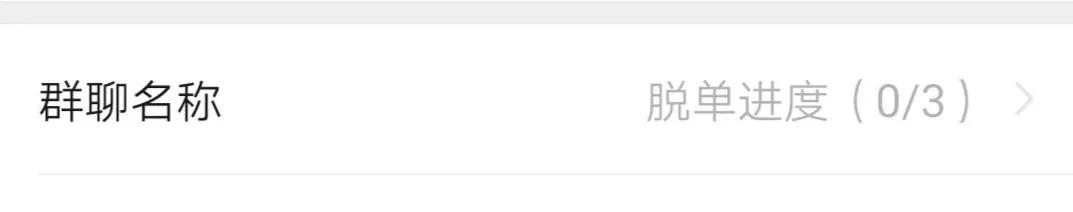族制是人类的亲族组织与相关制度,包括父系、母系的亲属人群、姓氏称谓、家族宗族及其相关制度。既是传统史学中的重要内容,属于“礼”的范畴,也是当代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所关注的课题。对“族制”较早开展研究的有章太炎,他在《訄书》中设“族制”一目。吕思勉于1932年出版《白话本国史》,也列“族制”一章,认为族制为血缘亲属之制,包括同姓和联姻的异姓,族与姓分化的两种组织。族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考察和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视域。

族制与秦汉社会的变迁。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受血缘亲属制度的影响比较大。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殷周之际是一个‘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时代;其兴废之变有三: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王氏所讲的殷周制度之变,主要是在族制内容上。
族制的变迁本是个长时段的缓慢过程,但在秦汉时代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因素。学界也注意到了“周制”与“秦制”的变化。吕思勉指出秦汉时有一个由“宗法”到“户法”的变革,指出:“秦、汉以前有宗法,秦废封建,宗法与之俱废,萧何定《九章》,乃变为户法。宗法以宗为单位,户法以户为单位。”邓子琴将自东汉开始的“门阀时代”,与以往解体的“宗法时代”相对应。晁福林以长时段理论审视,认为秦统一标志着“氏族时代”的终结和“编户齐民时代”的开始。诸家所言的社会变革也多发生在族制方面,与新旧制度的承变有关。毋庸置疑,秦汉是自商周以来新旧家族制度和亲属关系规范的又一重大变革时代,汉代族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秦汉族制研究的内容,应该从四个方面考虑。族类意识与亲属群体。秦汉时期三族、九族的族类意识并非专指父系之宗族,同时也包含着外亲的概念。贵族阶层的权利分享,外亲舅党是不能忽视的群体,刑罚的实践也常牵涉到妻族与母族。宗族的贵族特征及其演变。秦汉贵族的特点是由食封贵族向士人之族转化,由此也影响了宗族的变化,宗族组织带有“半官办”特色。宗法活动与宗族制度。宗法开始下移,墓祠祭祖、族内互助、官修牒籍是秦汉宗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族制与王朝政治、秦汉社会。族制与日常生活中的家族,宗法观念、族类意识对汉代制度的影响,爵位和财产继承制度、外戚帷幄政治、地方世家豪族的形成等问题。
除了族制自身外,还可以以族制的视角,去探讨秦汉时代的一些事件和人物,那么“老问题”则会有新发现。比如,由秦汉继承习惯看秦始皇的立嗣,从姓氏、称谓制度考察成蛟、子婴的母族和秦始皇的妻族,从属籍制度和刘贺海昏侯“太祖”身份推测“大刘记印”及其无字印的含义,由三族制看战国秦汉时代的太后干政、舅氏擅权现象,等等。
“亡秦者胡也”与胡亥母族的研究。先秦时期,妇人称姓而男人称氏。氏从姓而分,得氏的途径很多。姓为族,氏为宗;姓百世不迁,而氏则变化无常。秦汉时期姓、氏合一,其时去古未远,仍然保留姓氏称谓的部分古风。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秦王政“姓赵氏”,是随母赵太后姓而为赵氏(秦汉的文献一般称秦始皇为赵政或秦王政,极少有称“嬴政”的),即“古者因生以赐姓”的原则(《论衡·诘术篇》);而《高祖本纪》称汉高祖刘邦是“姓刘氏”,随刘太公的父姓。出身贵族的秦王政保持取氏的旧传统,而庶民出身的刘邦则采用姓氏合一的新原则。
随母姓,也是秦始皇“姓赵氏”的缘由。姓赵氏,只是秦始皇本人,上不继承,下不延续,不包括他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及其异母同父的兄弟,不会有赵子楚、赵成蛟或赵扶苏、赵胡亥的称谓,因为他们的母族不同。随母姓,也即随外家之氏或以舅氏之姓为氏,正如《越绝书》所言,秦始皇帝“号曰赵政,政,赵外孙”,是以舅氏姓为氏。
由于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和兔子山秦简《秦二世元年文书》的发现,秦始皇的立嗣和胡亥的继位又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秦始皇之前秦有舅党擅权和太后干政的传统,秦二世母族的背景怎样?这是胡亥和秦史研究中不可不注意的问题,但限于直接史料的缺失难有进展。然而从姓氏称谓到族制入手,会有新的研究视野。
“胡亥”是姓名还是名?人们往往并未深究。由当时秦室贵族随母姓的惯例来看,二世称“胡亥”,与始皇帝称“赵正”(文献上也作“赵政”)意义相同。在《赵正书》简文中称始皇帝为“秦王赵正”,称二世为“秦王胡亥”。“秦王赵正”,赵为氏,正为名。同理,“秦王胡亥”胡也是氏,亥为名。二世皇帝姓胡氏,也有时人认知为证。秦时著名的谶语“亡秦者胡也”,所谓“胡”,秦始皇以为是北方的胡人,所以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以“击北胡”;而秦亡后汉人认为是应在了胡亥身上。《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郑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郑玄说“胡亥”为“人名”,准确地说应该称“氏名”或“姓名”,“胡”是指姓氏。两汉间还有两条谶语见于《后汉书·光武纪》《公孙述传》:“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卯金”“八厶子系”都是指姓氏,即指“刘”姓当再兴,“公孙”氏当为王。
胡亥为何姓胡氏?当然是随母姓,与其父赵正姓赵氏一样,也就是他的母亲为秦始皇的胡姬。胡姓的源流,据司马迁《史记·陈杞世家》和《世本》所载,源自妫姓之胡和归姓的胡子诸侯。这两胡氏都是中原古老的姓氏,其与偏西的秦王室联姻的可能性不大。还是根据那个“亡秦者胡也”的谶语,秦人认为是胡族政权,汉人认为是姓胡的胡亥,实际上可能二者皆为有之,也即胡亥的母亲胡姬,既姓胡氏,又是胡族之女。春秋时晋献公曾娶戎族狐姬、小戎子、骊姬,都是以种族为氏。晋文公之舅氏狐毛、狐偃即以“狐”为氏。春秋之“狐”与战国之“胡”,应该都是秦晋诸国对戎狄族氏的泛称。秦立国西陲,杂戎狄之俗,战国以来秦宗室不但联姻楚国,也与戎君保有通婚习俗。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曾与义渠王同居而生子,这是胡人男与秦人妇的通婚。秦国庶民与胡人通婚也是常见的,秦律曾就秦、胡通婚所生子的身份做出界定。《法律答问》:“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按秦律,母秦人、父臣服于秦的胡人,他们所生子则有“夏子”的身份。秦伐夷狄灭六国,秦王政收各国女子置于后宫,自然也少不了胡女,她们会生有子女的。
胡姬为胡族之女的推测,还可从胡亥的母族教育背景上看出。《新序·杂事》记载胡亥幼儿时的故事:“秦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皆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子闻见之者,莫不太息。”胡亥的举止颇值得玩味。胡亥入学后受宫中教育,“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应该是懂得法家的“君臣上下之分”的规矩,不会乱来。秦人及中原各国儿童的教育,一般是七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二十岁左右行成人礼。有时或迟或早,秦王赵政举行冠礼是在二十二岁。所以胡亥践败陈履的举动,应该是他进入宫廷教育前为小儿之时的表现。
胡亥践败陈履之举非常怪异,非秦人及六国之风。秦及中原各国的人们席地而坐,入户要脱鞋袜,跽坐或跪坐,自然要陈放鞋履于户外阶下,这是生活习惯,虽小儿也视以为常。胡人住穹庐,旃裘靴,“脱帽徒跣”是匈奴人祈降之礼。如果是出生于胡风生活环境的小儿,头一次出席秦的宫廷宴会,发现这么多的鞋履排列在一起,会感到新奇有趣,做出踩踏鞋履的嬉闹举止非常自然。战国秦汉时期,诸侯贵族出嫁女子仍保持媵臣制和外戚侍帷幄传统,出嫁到夫家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保留着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年幼的子女在入官学前基本随母亲生活而受母族原有风俗的影响。还有大家熟知的“指鹿为马”和“束蒲为脯”典故,也能说明这种情况。潘岳《西征赋》有“野蒲变而成脯,苑鹿化以为马”句,讥讽秦二世的愚昧。中原多鹿,北胡多马。蒲生长于池沼之中,《说文》:“蒲,水草也,可以做席。”席地而坐是华夏族的生活习惯。束蒲、鹿是中原常见之物,而骑马与肉脯则为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日常,二者形似而实非,南北悬隔。秦廷众臣不会马鹿不分、蒲脯不辨,赵高只是以此验证他们是否顺从自己,然而二世胡亥却真的疑惑了。“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其直目,而从邪臣之言。鹿与马之异形,乃众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分别是非,况于闇昧之事乎?”胡亥并非愚不可及,为何不能自信其亲眼所见,对蒲、鹿发生认知上的疑惑?赵高对胡亥非常了解,知道其自幼生活在胡人母亲家中,对中原的蒲、鹿认知有限,赵高指鹿为马、束蒲为脯,对胡亥是有针对性的。
如果说胡亥的母亲胡姬为胡族之胡女,那么秦人理解的胡人亡秦之说亦能成立,即胡族之胡姬所生之子灭亡了秦朝。
回到族制的层面,很多看似不相干的史实,都有相关的因素。举一反三,古代中国何以家国同构,亲属宗法制度如何影响王朝政治,贵族宗族组织又为何庶民化并影响到民众生活?这些都可以从族制研究中找到串联出真相的线索。由此可说,族制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族制研究”负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闫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