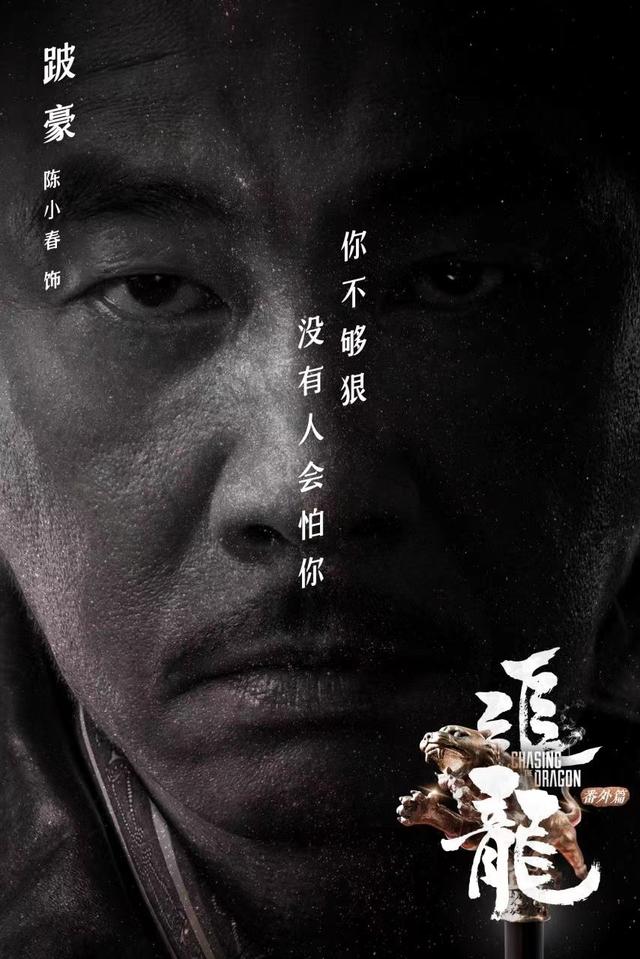文/朱万章

金农自画像(配图来自网络)
相关阅读:种满墙阴一架新|金农的葫芦画(上)
三
金农的葫芦画,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亲承教泽、获益最多者莫过于嫡传弟子罗聘。
罗聘(1733-1799)也是“扬州八怪”之一,字遯夫,号两峰,又号衣云、花之寺僧、金牛山人、师莲老人等,祖籍安徽歙县,其先辈迁居扬州。他一生布衣,游于金农门下,诗书画兼擅,善绘人物佛像、山水、花鸟等,“颇有逸趣”(清·钱泳《履园画学》),著有《广印人传》。罗聘的花鸟画和人物画于其师浸淫尤深,梅花受其熏染最为明显。除此之外,便可属葫芦画了。
罗聘传世作品中,葫芦画有两件,分别为《葫芦图轴》(江苏镇江博物馆藏)和《葫芦图册》(上海博物馆藏)。无一例外地,两画均烙上了浓厚的金农印记。罗聘在《葫芦图轴》中引用金农的“葫芦口大贮古春”句题于画上,并题识曰:“秋平三兄斋中所挂葫芦甚多且精,一望而知其为有道之士也。醉后以指蘸墨,依样画之,以发一噱,两峰道人并记”,钤白文方印“罗聘私印”和朱文方印“两峰”、“花之寺僧”。虽然罗聘自谓是依斋中葫芦之“样”而写,但从画风看,实际上是依金农之“样”而绘。图中所绘四只葫芦从右至左分别为小亚腰葫芦、瓠和两只纺锤葫芦。小亚腰葫芦为淡墨白描勾线,悬于藤蔓之上,葫芦叶墨色层次分明,瓠和其中一只纺锤葫芦亦用淡墨晕染,颇有晚明泼墨大写意画家徐渭(1521—1593)逸意。唐代张彦远(815—907)在《历代名画记》中所言“运墨而五色具”,其“五色”(“浓、淡、干、湿、黑),在此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只纺锤葫芦则在白描绘出轮廓之后,再略点淡墨。此图无论是构图还是技法方面,都可看出是对金农的一脉相承。由于此图为罗聘“以指蘸墨”所画,而且是“醉后”的即兴之作,其画风自然系非典型风格,因而有论者认为此画存疑(王凤珠、周积寅编《扬州八怪现存画目》),这是很正常的。如果结合罗聘其他被认定为真迹的作品,并联系其一贯的笔性特征,就会发现,此图与其一贯风格并无二致,所以在《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中,该图又是被作为罗聘的代表作而选入的。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在上海、北京等地的书画拍卖中,出现多件罗聘的《葫芦图》赝品,其构图及题识均与此图相近。非常明显,这些伪作都是以此图为母本衍生出来的。这是需要鉴藏者和研究者特别注意的。
清·罗聘《葫芦图》,纸本墨笔,29x50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葫芦图册》实为罗聘《山水花卉册》(十开)中的一页,分别由枇杷、兰花、桃花、荷花、竹鹤、草亭、溪山、墨枝、疏柳、葫芦等十幅画组成。和金农《蔬果花卉图册》一样,此图也是所绘纺锤和小亚腰两只葫芦相互依偎,题诗也原文照搬。稍异者,乃此图专门画上了葫芦的龙头及数片大叶,题诗在画的右侧(金农原画的题诗在左侧),且将“衰年”改为“近年”,署款则为“喜道人”,钤白文方印“人日生人”。这是典型的对金农原画的传移模写。这种现象,在清代画坛极为流行,有的甚至到达以假乱真的地步。现存作品中,就有潘恭寿摹写明代丁云鹏的《玩蒲图》(分别藏安徽省博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蒋涟摹写清朝华岩的《金屋春深图》(分别藏广州艺术博物院和广东省博物馆)、屈兆麟摹写清朝郎世宁的《画仙萼长春》(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任熊摹写明代陈洪绶的《麻姑献寿图》(分别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广东省博物馆)、王翚摹写五代时期卢鸿的《嵩山草堂图》(分别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罗聘的《葫芦图》便是这一现象的折射,显示其艺术渊源有自。
此外,在南京博物院还收藏一套罗聘的《花卉蔬果册》(十二页),其中也有一件《葫芦图》。该图所绘两只葫芦,一为瓠,一为纺锤葫芦。其构图颇类上述金农《蔬果花卉图册》中的葫芦,并抄录金农的“采铅客,拾珠人,种满墙阴一架新,葫芦口大贮古春”句,款署“喜道人画”,钤朱文方印“两峰”。该册页曾刊载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文物出版社梓行的《南京博物院藏画集》,八十年代台湾艺术图书公司出版的《扬州画派》一书还选刊了此图。从笔性与气韵来看,这件作品非罗聘所作。在八十年代后期,以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等为代表的书画鉴定家所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全国巡回鉴定时,也一致认定此画为伪作。由于罗聘的诗书画在清代中后期一直受到以江浙地区为中心的鉴藏家群体的追捧,在此情况下,赝品应运而生也就很正常了。因该《花卉蔬果册》涉及“葫芦”,虽非真迹,但构图及画风也与金农有诸多相近之处,可以让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罗聘葫芦画的传承,姑妄存此备考。
在金农弟子中,得其法乳最深者非罗聘莫属。无论在诗文,还是在书画方面,罗聘均能得其真传,并阐释光大,自出机杼,成为与金农并驾齐驱的书画名家。正如晚清藏书家叶德辉(1864—1927)在《消夏百一诗·金农》中所说:“心出盦家心抱冬,画梅满幅似虬龙。华光长老传衣钵,弟子冰寒罗两峰”,可谓道出师徒之翰墨因缘;而清人秦祖永(1825—1884)在《桐阴论画》中论及罗聘时也称其“笔情古逸,思致渊雅,深得冬心翁神髓”。从两人葫芦画嬗变过程及其传承便可见其一斑。
金农虽曾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受裘思芹推荐而举博学鸿词科,但一直未走上仕途,一生不得志。他去世后,罗聘广为搜罗其遗稿,并出资付之梨枣,使其著作得以流传至今,留下一段艺苑佳话。
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金农和罗聘时代,作为配饰功能的葫芦仍然存在于画中。最为明显的例证便是与金农、罗聘同为“扬州八怪”的黄慎(1687—1772)所绘的佛道人物,就与葫芦不离不弃,沿袭了元明以来的绘画传统,如《费长房遇仙图》(扬州博物馆藏)、《醉铁拐李图》(天津博物馆藏)等便是例证。这种传统虽然在金农以后便渐行渐远,但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仍然能偶尔见到零星的作品出现,如李育的《李仙幻像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钱慧安的《求浆仙窟》、《鹿门采药图》(均藏天津博物馆)、沈铭的《钟馗图》(广东省博物馆藏)、蒋璋的《八仙图》(天津博物馆藏)、郑芳的《仿黄慎戏蟾图》(广东省潮州市博物馆藏)、傅雯的《指画梓潼帝君像》(天津博物馆藏)、王元勋的《和合二仙图》(浙江省博物馆藏)、居廉的《寿星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李灿《拐仙图》(福建博物院藏)和朱伯姬《秋山行旅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等均是如此。这种作为配饰的葫芦画已经慢慢衰落,代之而起的便是以金农、罗聘等人的以主角形象出现的葫芦画。
在金农和罗聘之后,晚清时期的居巢、吴大澂、“海上画派”的周闲、虚谷、赵之谦、吴昌硕及近现代的王一亭、陈半丁、陈师曾、王云、齐白石、王个簃、高剑父、陈树人、赵浩公、佃介眉、唐云、钱瘦铁、丁衍庸、赵少昂、杨善深、朱屺瞻、娄师白、谢之光、杨和明、陈大羽等都兼擅葫芦画,且所绘葫芦均是作为蔬果类科目而以主角呈现。他们或对金农的葫芦画传移模写(如吴大澂、唐云),或私淑其艺、远绍其画风,均直接或间接传承衣钵,受其影响。尤其在吴昌硕、齐白石时代,以葫芦为主角的葫芦画发展到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名家和名作层出不穷,单就吴昌硕、齐白石而言,传世的葫芦画就有近百件之多,远远超出宋元明清以来葫芦画的总和。这就说明,在葫芦画的发展历程中,以金农为分水岭,作为配角的葫芦画日渐式微,而作为主角的葫芦画则日益兴盛。所以,当我们在考察葫芦绘画发展与嬗变的历程时,金农的开创之功显然是不可忽略的。(本文作者朱万章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本文原载《文史知识》2016年第9期总第423期)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图文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