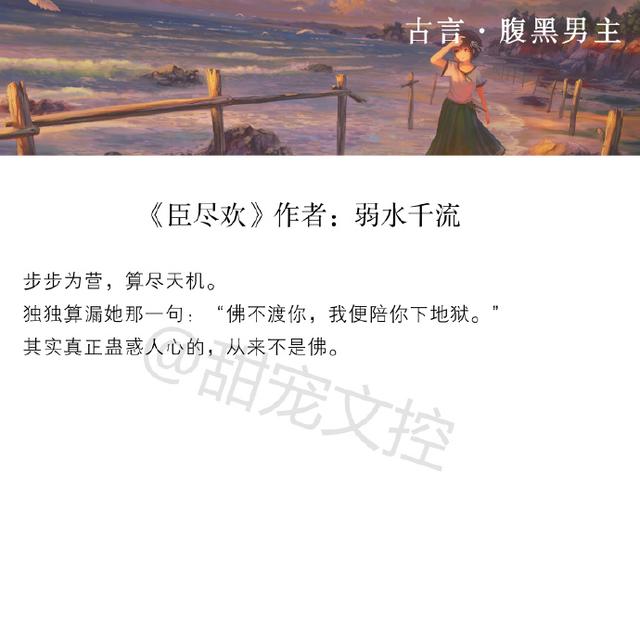1.
近日阿夭又将墙头加高了些,避免像去年一样,东边院子那三个淘气的小子爬树偷桃。
其实,阿夭并不是十分吝啬那几个果子,只是那树已有一小半伸长他们家院子里,那边的吃了也就罢了,却还要爬到树上偷吃这一面的,吃便吃了还要乱折枝,阿夭便不高兴了。
“好些日子不见那院子里有人走动,听说是去走亲戚了。”月亮倒了一杯花茶递给她。
她接过侧头往那院子瞅了瞅,好像是这样。
东院住着一个泼辣妇人带着三个孩子,前些天的夜里月亮吓得她那几个儿从墙头上跌下去摔坏了屁股,被她掐腰在门口好顿撒泼,最后赔给她一兜零嘴儿果子不说,临了还扯走阿夭手里的一方帕子。
平时那三个孩子上蹿下跳,猫嫌狗烦,难得这几日耳目清静。
偏这一方日日鸡飞狗跳的小院,也是阿夭避开那人的所有耳目才找到的,已属不易。
阿夭刚喝了口茶便听到那院有了动静,接着便是一道尖利的哭声响在自家门前。
“哎哟,不要活了啊,大家都来评评理我这才出门几日便被人砌高了墙头,再见不着一点光亮了呀......”
正是那东院的妇人,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来跑门口哭闹,院外已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你个撒泼皮痒的刁妇,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月亮撸起袖子抄着一把扫帚往前冲,那妇人一边同月亮撕扯,一边嘴里不停,“大家都看看,这是我男人不在家欺负我们母子没人撑腰啊......”
阿夭不理门外的门外的闹腾,只端着茶欣赏树上的小小青果,再耐心等些时候便要熟了呢,她想那味道应该不错。
2.
突然院外停止了哭闹,只余车马而至的声音。
众人看去,只见这一行来人大概有二三十个左右,个个劲装冷面。
随从放了马凳,从车上下来一人,周围的邻居和泼辣妇人都看直了眼,他们从没见这等风姿尊贵的人,身体不由自主的往旁边让去。
只有月亮心忽的一惊,转身便要往院内跑,身后的随从快速的伸手一劈,人便立刻昏倒在地,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吓得伏地而跪不敢再出声音。
阿夭将要入口的茶已洒了大半,直直的看向信步而来的人,金冠束发,云纹黑锦,通身贵气,面上端的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他正是阿夭一直躲避的人,秦王邰曜。
邰曜撩袍坐在她对面的位置上,淡淡的笑着看她。
“怎么,见到本王不高兴?”
“不敢。”
不知是惊吓多一些还是沮丧多一些,阿夭为他倒茶的手有些发抖。
眼前的杯中浮着几粒白绿茉莉,汤色黄绿明亮,执杯入口,清鲜甜美。
“窨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错实不错。”邰曜上翘的薄唇带着水泽,抬手转动着手中杯子。
“阿夭一直思念王爷来着,突然见到您有点不敢相信。”
她一直努力保持微笑来着,可是奈何面上绷得太紧,怎样也做不出那种自然的效果,给人的感觉很是牵强。
邰曜轻笑出声,“你说你一直思念我来着?”
阿夭垂眼道:“正是,终日思君,衣带渐宽,为君憔悴。”
就这?他看了看她比一年前较丰夷的脸又指了指自己。
“王爷,当初您与我约定,若是一年之内找不见我,便随我自由,现在已经超出三月有余。”
阿夭握着拳定定的怒视着他,似想从他眼中看出哪怕只有一分真假,就像那时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重新审视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
那时刚嫁入王府中不久的阿夭,偷偷潜入暗牢中看到令人骇怖的一幕,邰曜坐在一盏昏暗的油灯旁,手中擦拭着一柄带血短刃。
而他面前的刑架上绑着一个满身血污,奄奄一息的人。
此人正是归鸿书苑云山先生的父亲,当朝的太子太傅谭蒿泊。
之后的阿夭总是梦魇中惊出一身冷汗,而身侧之人则总是轻轻的搓着她的背,低声细语。
可即便如此她总觉得这偌大的王府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在第一次决定出走后刚到城外渡口,那等待已久的人便转身关切道,“你是要去找被人拐走的鹰儿了吗?”
阿夭从那一刻开始感觉到,这个自以为的举案齐眉原是真正的深渊厉鬼。
阿夭慢慢的松了拳,他此刻出现在她面前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如今在有期盼便是自欺欺人。
邰曜弯唇:“这个倒记得真切,从前我说过的话你可是信过一回?”
不是她不信他,而是次次他出尔反尔,他曾说过她那唯一的侄儿鹰儿还活着,可却从未让她看过一眼,多希望他能信守承诺一次。
两人默默不言地较着劲,正在此时站在不远处的一个满脸精明的随从开口。
“王爷,刚才那个俾子如何处置?”
阿夭认出了此人,是邰曜的贴身常伺,福瑞。
邰曜未从阿夭面上移开,冷声问道:“冒然冲撞皇亲国戚是何罪?”
福瑞:“杖毙。”
福瑞刚要转身去执令,却突然感觉后背有东西砸了过来,一偏身躲了过去,一只杯子啪的碎在地上。
“你个欠嘴多舌的狗腿子,把吃过的桃花酥都给我吐出来,要是今天敢伤她性命,我日后必定扒了你的皮。”
福瑞被阿夭骂得狗血淋头,转身委屈的看着自家主子,奴才为了帮您接回媳妇生命都受到了威胁,您不能不护着我。
3.
秦王府的花园很大,彼时的菊花开得正盛,不时穿梭着赏花的女人们。
“前面那位像是前些时日被王爷接回来的侧妃,叫什么夭的?”
说话的是一个身着绛紫色锦衣华服的美丽女人,手中正拈着一朵刚摘的金色菊花。
“正是呢王妃姐姐,她是原震远将军俞振家的小女儿,叫俞惠子,小名阿夭。”
另一个穿着艳丽的女人笑着回道。
王妃是兵部尚书刘大人的嫡长女刘雅辞,另一个则是大长公主的女儿陶玉儿。
见王妃正打量着远处菊丛中的清丽佳人,眼珠一转,“听闻这位侧妃妹妹王爷稀罕得很,十日有八日都在她那处歇着,当眼珠子似的宠。”
其实这话一个外人说来非常不妥,更何况是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但碍于她的身份又是秦王默许她经常出入府中,王妃也不好当着众人发作。
她面上情绪不显,缓然开口:“宠着点是应该的,毕竟两人从小青梅竹马,之前又消失了一年多,这才刚找着。”
几人说着便走到了出来透气的阿夭近前。
阿夭总喜碧色衣裳,这也趁得她白皙的皮肤更加娇嫩盈人。
“这便是惠子妹妹吧,一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如今一见当真是明艳佳人。”王妃笑道。
阿夭将手中刚刚采摘的一束秋菊递给了月亮,朝王妃施礼,“见过王妃。”
之后便立在一旁不再言语,随王妃一同过来的陶玉儿开口道,“妹妹也知道姐姐是王妃,怎的回来这么许多天也不到王妃那里去请安。”
“你是哪个?”阿夭抬眼。
“我是大长公主之女陶玉儿。”
“哦,原来是郡主殿下,还以为是伺候秦王的无知小妾,刚才你称我为妹妹,还以我那个已过世多年的爹生前在外欠下的风流债呢,下次莫要乱认亲戚,免得污了人家清白。”
“你!竟敢......”陶玉儿用手指着阿夭气的说不出话来。
王妃见到这不愉快的情形,拍了拍那陶玉儿的手安慰道:“罢了罢了,都是趁着好时节来赏花悦心的,没必要平白生气,彼此都退让些罢。”
说完再不给阿夭一个眼神,带着一行人冷着脸离开了。
没有人知道,被王妃拢在袖中的那朵菊花被捏得满手汁液,随即被不着痕迹的丢在了脚下。
4.
邰曜来到馨月苑的时候已过了晚饭时。
“看样子,你在别处用过饭了罢?”
阿夭见他后面的福瑞提了一篮新鲜的桃子,便笑盈盈的上前挽着他在桌前坐下。
邰曜知道她从小就爱吃桃,那时磨了她父亲好久,才将园中所有的桂树砍了换成了桃树,气得当时那个名叫桂花的妾室显些晕了过去。
当时拿着斧子的邰曜看着满院倒下的桂树摇头叹息,直道她是牛嚼牡丹,暴殄天物。
还有书院中如若不是有棵硕大的桃树,她是不会乖乖去读书的,就连在外漂泊这一年多的时间也找了个带桃树的院子。
“下次到了饭时你就先吃,莫要等我了。”
邰曜看着桌上已经凉了的饭菜道,略带疲态。
“没关系,我又不是很饿,每天等着你来至少有个盼头。”
“真这么想的?”
只见阿夭望向案上的新桃,深情款款的柔声说道,
“那是自然,王爷待我好我总不至于一直不知好歹。”
身后候着的月亮看着阿夭的后脑勺有些失落,王爷待小姐好吗,这才离开一年多王府中便有了正王妃,并多了几个貌美侍妾,听说还都是有来头的。
可要说不好,王爷每次从不空手而来,就连进贡给小皇帝的稀罕夜明珠他都拿来给她家小姐当弹珠玩儿。
见邰曜嘴角衔笑一脸的不信,阿夭举起三根手指郑重模样道,“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邰曜赶紧扶额挥手,“罢了罢了,你这是要给我送走。”
虽然知道他已经吃过了,可她还是往他面前的碗里夹了许多菜。
邰曜想起两人少时也是这样,但凡同在一处吃饭,阿夭总是把她认为的好吃的夹满他面前的碗,看着他吃完她才肯动筷,邰曜无奈只得陪着先吃了两口。
“好吃吧?”
“还好。”
阿夭转头看向月亮,“我就说嘛,这王妃的品味差不了,她送来的东西王爷定是喜欢的。”
邰曜喜欢不喜欢王妃阿夭并不清楚,但喜不喜欢自己,阿夭想应该是有一点的吧,若不然,在她父亲战死沙场的几年后,邰曜依然信守承诺娶她过门。
“咳咳咳......”邰曜吐不出又咽不下,卡在喉咙实在难受。
福瑞赶忙给自己主子倒了杯茶水,默默地为阿夭竖起大拇指,奴才佩服您五体投地。
“下个月十五宫中举办游园会,你也一同去看看吧,出去透透气也好。”
阿夭听完停下手中的筷子,接过月亮递过来的酒壶,那双少了两指的纤细柔荑,每每看到总是刺痛着阿夭的心,虽然当时月亮对流着泪的她说,小姐,一点也不疼。
她知道他留着月亮也不过时刻提醒着她,之前所为只削两指,再走,只会要了她的命,又或是她的命。
“按照您的吩咐,我今日去拜见了您的那位正头王妃。”
阿夭抬手给他倒了杯酒,“为了你兄长的大业苦心经营,精于算计,总有累的时候,来,尝尝,这是我去年埋在树下的桂花酿,没毒,死不了。”
是啊,他的兄长,在这世上唯一的至亲,那个野心勃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摄政王。
他为了兄长可以替他求娶兵部尚书之女,可以收下为之拉拢那些人送来的美人侍妾,还可以为他明里暗中肃清朝中异党。
邰曜沉脸,“以后莫要再妄议我兄长,不然......”
“不然怎样?就要将我置于死地,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王爷您说是吧。”
阿夭笑的轻快,仿佛说的话中与自己无半点关系。
“没良心的东西,不如半道将你掐死喂了野狗。”
邰曜瞪了她一眼,恨恨的饮完杯中酒。
阿夭自顾自的掰着手指数了五息,抬头冲着月亮磨牙,“你个心慈手软的怂蛋玩应儿,当真没放毒哪。”
福瑞暗自倒抽凉气,祖宗您能耐,您可真是什么都敢说。
月亮被她斥得低头看着自己脚尖,那是五步断肠散,府中的明兵暗卫可不是摆设,当真放进去她俩此时怕是已经成了肉馅。
邰曜冷脸对着阿葆,“你们两个滚出去,走的慢了自己把腿砍了。”
两个有眼力见儿的退的轻车熟路,带上房门前齐刷刷的冲对着阿葆投来同情且无能为力的目光。
主子,您息怒。
小姐,您保重。
5.
雨打屋檐,声声入耳催人眠,阿夭立在窗前看着对面檐下的泥筑,那里早已没了叽叽喳喳的燕子,再不用归巢。
“小姐,当心受了凉。”
月亮觉得小姐同之前不大一样了,就连那笑中似乎都掺杂了些别的东西。
从前即便是躲躲藏藏的日子里她也会和她满脸期待的描绘未来的日子,可自从这次回府后小姐便不再与她说起这些了。
月亮为她披了件外衫,静静地退了出去。
阿夭一声长叹,吐出的气因这天凉生成了一呼白雾,心思神游。
那天游园看到的小皇帝,纵然再金黄灿烂的菊花也无法掩盖他眼中的灰败与颓丧,他才刚刚十二岁啊,应该正是意气风发的好年纪。
他的母后又岂会不知其中原由,所以极力让游园的位高权臣家的女儿上前来说话,可这些权臣家的女儿哪个不是人精,如今皇帝不过一傀儡,真正大权在握的是摄政王邰应,所以均是顾左右而言他。
当日惊鸿一舞的陶玉儿走过她身边时对她说了一句话,“听闻那城外十里的乱葬岗,有具臂上长着只蝴蝶形状胎记的幼童尸体,被秦王府的人安葬在野桃林中......”
阿夭听后天旋地转,眼前一片黑暗。
在回府的马车上,邰曜一直抱着她轻唤她的闺名,可那时她竟有股拔下簪子扎进他心脏的冲动,只奈何没有一点力气。
晚间转醒时,邰曜亲自盛了一碗参汤喂阿夭,勺子刚到嘴边阿夭苦笑抬头,“干嘛那么吝啬,放我一条生路可好?”
邰曜皱眉有些不耐,将勺子扔回碗中,迸起的汤汁溅了他一身。
阿夭吐了一口浊气,拿过他手中的碗一气喝了下去,罢了,这个时候还盼着他些什么呢,自己当真可笑。
“以后她送过来的汤我都会喝,但你不必再过来了,见到你实在心烦,我想走的时候清静些。”
阿夭说翻身朝里侧躺去,不在理他。
邰曜憋着一口气,起身想踢翻桌旁的椅子,又怕惹了床上的人,最后只得甩着袖子使劲踹了几脚门口的福瑞,方才解气罢休。
窗边的人身形单薄孤寂,自从这次回来后她便迅速的消瘦下去。
“妹妹这样的雨天也不怕着凉,莫要再开窗户了吧。”
王妃关切的说道,身后跟着的丫头将带来的汤盅放在桌上。
“看你这几日气色不大好,让人熬了参汤给你补补。”
“多谢姐姐记挂。”
阿夭请王妃坐下,接过汤喝了几口,“味道比之前的要浓郁很多。”
王妃笑道:“这可是北夷之地的上好老山参,稀罕得很,前儿个才新得的。”
“那可确实是稀罕,想必姐姐在北夷之地地有亲朋至友?”
王妃脸色突的一顿,片刻后又恢复笑容,“妹妹说笑了,我家世代居住在京城,哪里会认识蛮夷之地的人,不过是从商人手中得来而已。”
刘雅辞在未嫁入王府之前一直有个极倾慕她的人,那人在她成亲之后便负气远走北夷。
而阿夭与那人在书院中极为相熟,皆因两人都善丹青。
看到她刚刚的反应想来是确定了她的猜测。
王妃同她又寒暄了几句,便要带着丫鬟回去。阿夭执意要送送她,说自己权当出去透透气。
回来的时候恰巧遇到执伞而来的陶玉儿,这姑娘想嫁入秦王府的愿望真是做到人尽皆知。
“切,才几日的功夫就开始扮做病西施来哄人。”
阿夭莞尔一笑,“还不是多亏了王妃姐姐每日的参汤,滋补又养颜,而且啊......”
她故意上前一步贴近道,“那老参来自北夷蛮荒之地......”
陶玉儿嫌恶的往后一退,“那又怎样,别以为你会一直得秦王的宠,他早晚有一天会厌了你。”
“秦王的宠爱我倒不甚在意,倒已是双十年华的郡主殿下,若有朝一日入这府中想要的是什么位置呢,难道只为挤兑我这个侧妃打打牙祭,啧啧啧......”
阿夭讥笑着摇头离开,只留陶玉儿撑伞回味她刚刚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当夜,王府中便进了刺客贼人,所幸王妃那日被邰曜留宿在清风轩,只在王妃房中乱翻一通,像在找什么东西。
可之后王妃便心中惶惶,找了一日便对邰曜说要到北山寺去祈福。
6.
馨月苑中的那棵桃树随北风慢慢凋零,每日望着它的人也渐渐萎靡。
邰曜不知为何心中升起一种不踏实的感觉,“那院每日送来的东西确认无毒?”
福瑞忙回道:“确实无毒,每回东西都找人验过。”
是啊,参是好参,里面掺着的红花也是金贵,不仅无毒还都实实在在是些上好的滋补佳品。
“小的也遵了您的吩咐让人去请宫中的太医为侧王妃诊治,可侧王妃说是嫌晦气都将人骂了回去。”
“明日去我兄长府中将夫子请来和她说说话吧。”
“是。”
福瑞领了吩咐,心道那位曾经在归鸿书院教过几月书的名唤阶而的女夫子可不是一般人,不知摄政王府会不会放人前来。
秦王府和摄政王府一样气派奢华,给阶而的感觉也一样的压抑。
“夫子这样的忙人,难得今日有空不再多坐坐。”
说话的正是慢慢踱步而来的邰曜。
阶而对那张与邰应七分目相似的脸实在没有好感,目中无他径直与人擦身而过,可走出几步后顿住又折返回来。
“邰曜。”
福瑞见她直呼主子姓名,想要张嘴却忌惮其身份,瘪了嘴便默在一旁。
邰曜挑眉,“王嫂有话吩咐?”
“曾经伴先生左右时你问我,善恶可会在同一人身上所现,那时我不解一个清风霁月的王公贵胄为何这般问,如今想来你所做种种也并非是你真心所愿。其实这世间善恶本就一体,只是看人如何选择,也许你的一念之仁,就是他人生机所在,无论做何应对,事后莫要后悔当初便好。”
阶而见他一副假惺惺的毕恭毕敬,洗耳恭听状,心中叹息他又能听进去多少,实在让人气恼。
“哦对了,别叫我王嫂,不爱听。”
说完转身便走,来去皆如疾风。
邰曜对着她的背影高声笑答:“谨遵夫子教诲。”
大概今日见过夫子阿夭的心情很好,午饭后便邀邰曜一同到走走。
“夫子今日又同你讲了多少稀奇故事?”
邰曜搂着阿夭坐在亭栏上看着天上盘旋孤鸟。
回想起在书院时的那段快乐时光,实在让人怀念,那时书院中的云山先生带了位女夫子给她们。
本以为这年龄相仿的女子没有多少墨水,但谁承想这女夫子讲得一手好故事,又能引据经典将其中道理阐述的明白透彻,只可惜......
阿夭摇了摇头,“今日没讲故事,倒是听夫子问我这许多年可曾为谁心动过。“
邰曜低头看着怀中人似乎也想知道,阿夭环住他的腰轻轻笑道,“我动心可有好些回呢,”搂着她的人身体有些僵硬。
“比如看到他替我被先生责时的倔强模样,又或者爬到宫中那棵最高的树上为我摘果子时,还有帮我砍掉院中那些碍眼桂树的得意神情......”阿夭咯咯咯的笑起来,
“夫子说能让自己心动之人必有特别之处,也只因这特别在这世间仅此一个,人活今生不能期望于来世,须得珍惜现在。”
怀中的人目光灼灼的望向他,不知道这话夫子是说予她听的,还是阿夭说给他的。
邰曜摩擦她手背,“你总是不信我的话,可你对我讲的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如今我竟也辨不出了。”
“我从未想过要伤你的性命,等这些事情处理完,你便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的秦王妃。”
“想去哪里便去哪里?”
“这里是你的家,你还要去哪里。”
邰曜吻了她的额头,将怀中的人拥的更紧了些:“就快好了。”
阿夭眼中的光芒转瞬即逝,靠在他怀中的额头冒出一层层冷汗,身体也开始颤抖。
邰曜发觉怀中的人有些不对,却被阿夭牵过他的一只手放在她的小腹上,“如果,他能有活着一定是个淘气鬼。”
邰曜闻言蹙眉,握得阿夭手臂生痛,“什么时候的事,为何不告诉我?”
阿夭颤声,“这要多亏了你的那些山参,假死或者成为和你一样的人,我做不到,不如赔你条实在的性命来得让人信服。”
邰曜原以为娶了他的女儿便拉拢了他在朝中的势力,可没想到那兵部尚书竟是如此顽固之人,宁可联合外贼也要将他兄弟二人的势力从朝中铲除。
秦王侧妃一人性命不足撼动那兵部尚书的位置,可若是带着秦王的骨肉那便另当别论,更何况此时城外的王妃正在带着夷人写予她父亲的往来信件赶赴秘密之地,这兵部尚书谋反的罪名怕是要坐实了。
7.
城外十里长林繁盛,一辆后面跟着十几个护卫的马车横在另一辆马车前。
“王妃姐姐,这是要出城去往何处?”
陶玉儿撩帘问道。
“哦,原来是玉郡主,出去办点事情,今日便不与妹妹多聊了。”说完示意车夫向前。
可对面的陶玉儿不仅不让路,还命随从扶着从马车上下来。
“是去为你那反贼父亲送信罢。”
王妃面上大惊,“郡主莫要胡说。”
陶玉儿一挥手,身后的人便与王妃带来的人打作一团,可到底寡不敌众,王妃一行人被快速制服。
信件确实属夷人之手,王妃百口莫辩,当日夜里尚书府被抄,哭声一片。
王妃一直哀求见秦王一面,可在尚书府一干人等被斩于菜市口之时,她也仍旧没能见到邰曜,次日听狱卒来报,原秦王妃自杀死于狱中。
京城中这几日人心惶惶,空中到处弥漫着血腥味,凡是与尚书府关系密切的均被提审查抄,之前讨好奉迎的个个胆战心惊。
“你这身子骨可真是弱不禁风,”陶玉儿差人端了碗补药递给月亮,“好好养着,养好了也好跪迎我与秦王的大婚。”
一旁的月亮听到秦王又要再娶心中酸涩不已,看着自家小姐即替她难过又替她委屈,尤记得当初那女夫子说过的一句话很对,令我一片赤诚之心千疮百孔,乃是心中无我之人,当弃。
阿夭靠在床侧有些气弱,“真是好福气,能够娶得同类,也不枉我担心他以后会孤单一人。”
啪,陶玉儿甩了甩手,盛气凌人道:“今日这巴掌我早就想扇在你脸上,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月亮刚要上前便被阿夭止住。
“你今日不该来此。”阿夭笑看着她,像看一个死人,似乎刚才的巴掌落到了她的脸上。
陶玉儿看阿夭云淡风轻的模样恼怒不已,“我可不是刘雅辞那个废物,你且好好活着吧,折磨人的手段本郡主多着呢。”
陶玉儿走后,阿夭盯了好久桌上的那碗补药。
“月亮,快去将秦王请过来,不管他在哪。”
月亮喊了一声小姐,眼泪落在握着她的手上,“为什么非要这样,您不是喜欢他的吗,若不然我们还可以逃出去的,去他找不到的地方。”
阿夭摇了摇头,能走到哪里去呢,他是一只鬼,一只鬼孤单的渴望陪伴的鬼,早在他们相识的那刻起一条无形的锁链便被他缚在她的身上。
她喜欢他是真,即便他做了恶事,恨他也不假,因为他藏起了鹰儿将兄长玩弄于鼓掌,利用她仿得一手好丹青,曾经那样一个目光清澈的人如今变得这般深诡,她再不愿与他同行更是真。
邰曜急匆匆的赶来时,阿夭嘴角渗血奄奄一息,而床边碎了一只瓷碗。
“是谁?”他目眦欲裂,怒火燃烧。
月亮急道,“是郡主,她逼着小姐喝下不知是什么东西,还打了小姐。”
阿夭的脸上浮着通红掌印,此时的她气息微弱。
“我那心实的兄长......一直感激你在为他寻那唯一血脉,”其不知是将狼子作恩人,“算我最后求你......将鹰儿还与他,放他一条性命,为你所用也好,削官为民也罢,可成?......”
邰曜看着眼前的人,目光慢慢的失去光彩,心痛的回道,“可。”
8.
几日后的京城百姓口中议论纷纷,不知夷人哪来胆子敢混入庙会的人群中截了玉郡主的车架,连同人一并掳了去,至今下落不明。
秦王府中的地牢里,一盏昏暗的油灯,一身黑色锦衣之人玩弄着手中带血的短刀。
而在他前面的刑架上绑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嘴里发出痛苦的呜呜声。
“你再嚣张跋扈也须得知道,有些事你做不得,有些人你不能动。”
这里的守卫对这见惯不惊,总隔几日他们的主子便来此在这没了舌头的女人身上割下几片肉来,之后又命人医好。周而复始,不厌其烦。
阿夭走后不久,她的兄长俞翎荆千里飞骑赶回京城,在阿夭坟前痛哭不止,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也离他而去,回想当初那个满脸幸福的小丫头在送别的城门口朝他挥手,如今却孤伶伶的葬于城外黄土之下,便令他心口刺痛,悲恸欲绝。
可当他颓然跪坐于坟旁深陷往昔之时,一个稚嫩的声音将从悲伤的回忆中唤回。
“爹,爹......”
“阿鹰......”
俞翎荆见鹰儿飞奔过来紧紧将他搂住,而邰曜唇无血色的正站在不远处。
“爹,是姑父救了我,他为了救我受了好重的伤,可是,姑姑,姑姑......”
鹰儿泣不成声,俞翎荆握紧剑的手也松了下来。
将在外无召不得回京,邰曜着了一队人偷偷护送俞翎荆父子回北疆。
此后坊间皆流传着秦王对已故王妃俞惠子的深沉爱意,妃位空置不续,每年的初秋之时秦王妃墓前都会摆满新桃。
9.
很久以后,阶而来到那个曾经、现在挂满青桃的树下,静立许久。
犹记得当时那张憔悴的脸上挂着淡淡的期盼笑容,“先生交予夫子的异时山图就埋在那处,如果季节正当,您便帮我尝尝树上的果子甜不甜......”
“阿姐,俞小姐这么做值吗?”
阶尔摘了片桃叶放入手中:“对于执迷不悟的恶人,追悔莫急的痛不欲生对他也是种惩罚。”
东院的妇人那听到这处有动静便寻了过来。
“您是之前这院子里那位姑娘的什么人?”
妇人眼角扫了下阶尔后面站着的左一言,当看到那年轻男子的脸上有条可怖的刀疤,让她有些局促不安。
“我啊……是她的姐姐。”
妇人狐疑的看了她一会儿,从怀中掏出一方绣着对红桃的帕子,“这是之前那姑娘落在我这处的,劳烦您替我还给她。”
夫子接过帕子,眼中盛满的泪水滴落在上面。
原来真是她的姐姐,瞧着那天带走那姑娘的那些人,必定是些惹不起的大人物,那妇人想,又颤颤的对上她的目光:“让她,让她......让她莫要与我一般见识。”
翌日清晨,东院的几个淘气小子攀上墙头想一窥昨日那仙子般的容颜,久未见人,却见桃树下被人翻了很深的土,而树下的石桌上只余一枚被人吃了半颗的青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