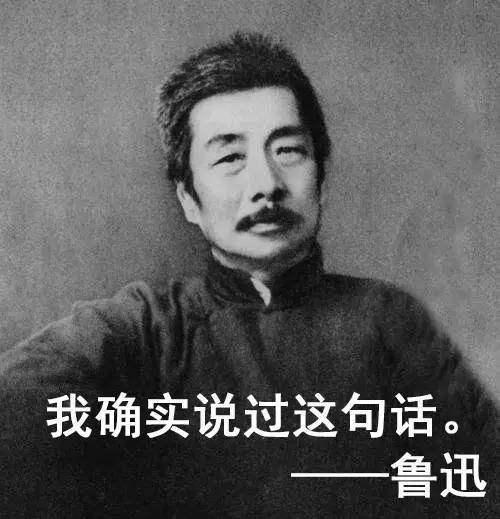
鲁迅自己的笔名多,在文章、书信中给别人起的外号也多,多到简直信手拈来,多到成了文学形象的代名词。比如提到“孔乙己”,就立刻想到那种穷酸迂腐掉书袋的人,提到“阿Q”,自然就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假洋鬼子”说的就是那些喝过一点洋墨水就附庸风雅、目中无人的人,而“圆规”,当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瘦骨嶙峋又嘴碎刻薄的杨二嫂。鲁迅的起外号能力,不光是在虚构文学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用在现实人物身上,更是寥寥几字就勾画出一副副肖像画来。

周作人就在回忆录中写过,鲁迅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同行的有一人叫邵明之,留学札幌,学习修铁路。这邵明之的脸又圆又黑,还有一脸大胡子, 因为他所就学的北海道当时开发程度不高,有很多野熊出没,鲁迅就开玩笑地叫他“熊爷”。在鲁迅住宿的宿舍里,还有个老头,每天下午就一个人出去,到半夜才回来,一进门老太太就问他:“今天哪儿着火了?”一开始鲁迅不解,便叫他“放火的老头”,后来才知道,他是消防队值夜班的。
文字学家钱玄同,曾与鲁迅同读,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结果听的时候,钱玄同很不安分,坐不住,总在榻榻米上挪地方,鲁迅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爬翁”。又,守旧派的文人林纾,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荆生》,其中一个人物取名“金心异”,说自己讲《说文解字》是骗钱,来影射钱玄同。于是鲁迅又在信中称呼他“心翁”。同一封信中,因为1919年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失败,中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鲁迅又称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为“仇偶”、子女为“半仇子女”,当然鲁迅对信子夫人并无实际的敌意,这些称呼只是与钱玄同之间的幽默言语罢了。
北洋教育总长傅增湘,鲁迅叫他“女官公”或“女官首领”,这得要转几个弯子才能明白。太平天国时,有女状元傅善祥,担任东王府的女官首领,而“傅增湘”与“傅善祥”恰好音近。把堂堂政府大员比作天国时的女官,可以说是很轻蔑了。据说是因为傅增湘喜欢收集古书,鲁迅在把一批旧书转手给他的时候,他死命压价,令鲁迅十分不满,所以用这样的外号揶揄他。除了玩谐音之外,有时候也会玩玩形近字,比如鲁迅曾将“章士钊”写成“章士钉”,这是因为某期《京报》上刻板刻错了字,他便拿来戏耍。
中国早期的摄影家、陶瓷学家陈万里,鲁迅称之为“田千顷”。陈与田古音相同,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是妫姓田氏,也作陈氏。“万里”与“千顷”相对应。这也是需要猜一下字谜才能知道的。
北大校长蒋梦麟,鲁迅称其为“梦翁”,这是比较尊敬的称呼,私底下还有个戏称叫“茭白”。“蒋”字在现在的语言里仅仅作为姓,其实在古代,“菰蔣”是蔬菜“茭白”的别称。

徐志摩在鲁迅的笔下被称为“诗哲”,这可不是夸赞,因为孔子是文圣人,姜子牙是武圣人,圣人庙里陪祀的几组人物被称为“十哲”或“十二哲”。1925年泰戈尔来华访问,徐志摩一直跟在他身边当翻译,因为当时泰戈尔人称“诗圣”,徐志摩作为跟班,也就得了“诗哲”的雅号。
鲁迅不喜京剧,对当时的艺术界也颇有微词,所以在1934年3月24日给姚克的信中,称刘海粟“大师”、称梅兰芳“梅郎”,都是指他们的格调低,暗指刘海粟有能力游历外国,向中国青年介绍国外艺术,却只顾自我标榜;梅兰芳的戏是“男人扮女人”,他也看不惯。
鲁迅给人取外号,有个特点,凡是他想要批评和讽刺的,往往给一个“高大上”的外号,“诗哲”、“大师”如是,管胡适叫“新月博士”,管赵半农叫“国家博士”,文中都带贬义。越是亲密的人,起的外号越是诙谐,甚至借用别人的恶意来表达亲切感。比如钱玄同的“心翁”,还有曾称许广平为“害马”,取的是杨荫榆在女师大风潮中称她为“害群之马”的意思,这些外号反而体现了鲁迅对友人的支持。

为此,鲁迅自己有话说。在1934年4月22日写给姚克的信中,鲁迅说:“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