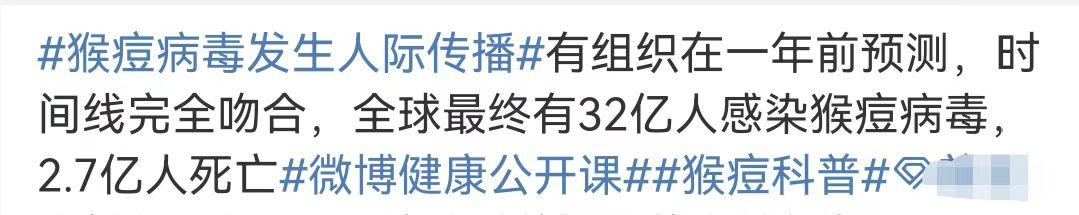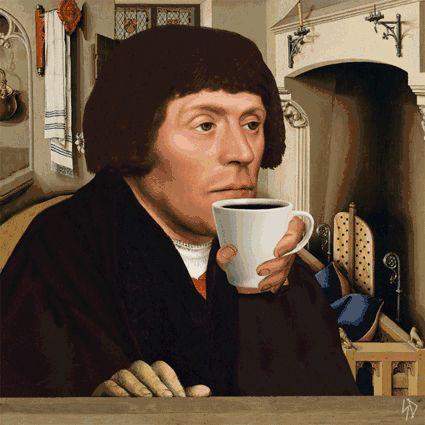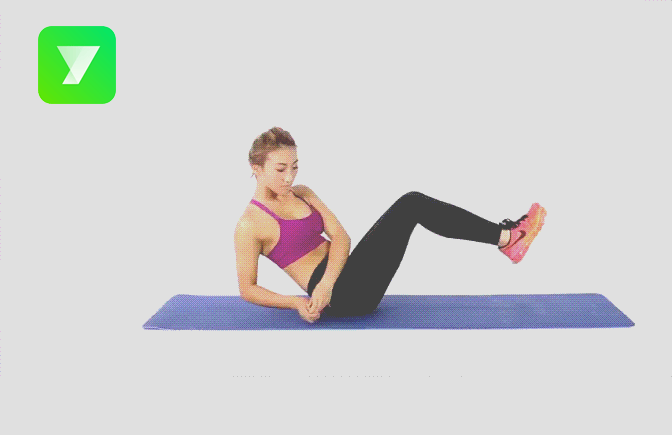1946年9月的柏林,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过度的操劳,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在这之前,他被查出患上了白血病。他对照护的人说想要杯香槟,他们用汤勺喂他喝了几口。10日,他开始昏迷,当天傍晚悄然离开了人世。这一年,他68岁。他是饶家驹,一位曾帮助过30万中国难民的法国人。

饶家驹肖像,图片由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提供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藏饶家驹铜像,图片由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提供
1913年,饶家驹来华,他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还能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和上海话。过人的语言能力,为他后来在上海进行的难民救助,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大家眼里,饶家驹个子高高的,相貌英俊,体格健壮,性格爽朗自信,乐于助人,喜欢戴一顶法式贝雷帽,胸前别一枚红十字徽章,穿一袭黑色长袍。在一次科学实验事故中,他不幸失去一条手臂。但提起这个事,大家更愿意相信饶家驹的这条右手臂是由于抗战而失去的。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宣传教育部 讲解员 王忠夏
1927年北伐战争后期,饶家驹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积累的人脉成功救下修道院的修女、儿童和躲避巷战的难民。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经他努力,又救出不少平民。而这些,仅仅是他在建立举世瞩目的上海南市难民区之前众多善举中的两例。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这一天,满目疮痍的城市,浸满死亡与恐怖。日军在焦土中继续烧杀掠抢,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上海的租界原本是对难民开放的,但是由于几十万难民的大量涌入,已然超出了租界的承受能力。8月13日当天,租界与华界之间数十处铁栅门开始由巡捕军警驻守,严控进入的数量和频率。到9月,进出租界已经需要通行证,收容难民的大门被关上。这使得大量难民不得不聚集在租界的周围,尤其是南市地区。他们挤在民国路,也就是就今天的人民路上,眼巴巴地望着法租界的大门。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宣传教育部 讲解员 王忠夏
上海的各社会团体纷纷开展慈善活动。但难民太多,收效甚微,每天街上都有冻死和饿死的难民。担任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副组长的饶家驹见状十分忧心。于是,他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俞鸿钧提出一个建议,在南市划出一块区域建立难民安全区。位置在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挡在该区域和日占区中间,提供了很大的回旋空间和可能性。
俞鸿钧市长认为只要保证中国的主权,一定赞成和支持此事。在得到中国方面的同意后,饶家驹继而与日方进行交涉。他用流利的日语直接表达希望日方能承诺建立这样一个中立区,并直言他们都负有责任对上海的难民予以保护。

对于划出的这一区域的性质和权属,中日双方是有分歧的。饶家驹很清楚让中日双方坐下来协商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他睿智地提出以个人名义分别与双方达成非正式协议,淡化敏感问题,并提出成立“南市监督委员会”作为管理和执行机构。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成员包括3个法国人,2个英国人,1个美国人,1个挪威人以及两租界的代表,以确保在和列强交涉时得到有力支持。他知道当时在上海,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社交中都很看重是否有“洋气”。

法租界地图上的饶家驹安全区(阴影部分),图片由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提供
经过三个昼夜紧张激烈的谈判斡旋,中日交战双方就建立难民区一事竟达成了一致:在南市划出一块区域,作为难民避难所,日军不得对此区发动任何进攻。1937年11月9日,饶家驹以他博爱、坚韧和独创的精神在上海创立了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难民安全区。从地图上看,整个南市难民区如同一轮半月。在抗战的烽火连天中,那轮半月像天使张开温柔的翅膀,庇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使他们有了暂时的栖身之所,避免了被日寇屠戮的命运,安抚了无数颗惊魂不定的心。
饶家驹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安全区设立了难民委员会,把安全区分为九个区,每个区设一名区长,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调查、医务等职,工作人员均由难民选出来的中国人担任。此外还设立了警卫、医院、学校等机构。
难民们都喜欢饶家驹,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饶家驹也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家驹每天坐一辆黄包车,从吕班路到老北门或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到南市难民区办公,黄昏才回到租界寓所,或到洋泾浜天主堂休息。他每天工作,每天到“区内”巡视考察,事必躬亲,确保一切正常。

饶家驹带领客人参观安全区,图片由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提供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宣传教育部 讲解员 王忠夏
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和舆论支持,他常常亲自出马,领着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人参观安全区,或外出开展募捐。他在俞鸿钧市长等人这里为安全区争取到大量的资助,他还跑去静安寺路的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大家踊跃捐输、共襄善举。他飞赴美国和加拿大,为难民募捐。在那里,他发起“一碗饭运动”,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饶家驹此行募集到大约100万美元,这在大萧条时期实属巨款。所有的奔波都是为安全区的难民,所有的募捐所得全部被用于难民救助。
1940年,上海时局渐稳,难民大多数回了家乡,南市难民区关闭。在难民区存在的963天里,饶家驹始终是第三方的代表、仁慈的代表、道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中日交战双方的监督力量,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和赞誉。
在成功创办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这个战时平民保护的“上海模式”,后来在南京、汉口、广州等地相继被复制和推广。被誉为“中国辛德勒”的拉贝在南京创设的难民安全区,也是对饶家驹安全区的效仿。1949年制定的《日内瓦公约》中,对“上海模式”做了具体的说明和解释,从而使其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
饶家驹曾发下誓言,要为不幸的人尽自己最后的力量。事实上,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之后的法国和德国。他用毕生的努力,为满目疮痍的孤岛之城点亮了一座生命绿洲,更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财富。
资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记者:贺晓晨 马斯曼
编辑:盛杰
校审:余婧瑶
监制:颜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