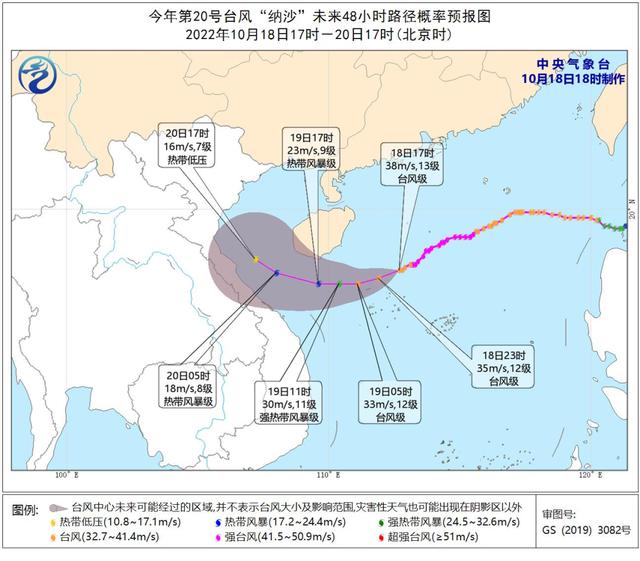余华是先锋文学代表作家,80年代曾经创作过《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带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先锋作品,其中充满着暴力和冷漠叙事。
先锋文学退潮后,余华从创作《细雨中呼喊》开始转型,写作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熔铸了现代主义的手法的现实主义作品。作品与世界和周围的矛盾对立性减弱,创作中更多地体现着人性的温情。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转型后的代表作品。它以50年代到文革历史为背景,讲述了许三观靠一次次靠卖血度过人生难关的故事。王安忆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1月12日上所说,“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许三观就是余华塑造的一个当代的英雄。他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身上却又带着英雄的精神
一、血汗争平等
许三观有着英雄不服输的精神和对尊严的执着。他卖血实际上是在以这种行为追求着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的平等。许三观生活穷困,卖血成为他唯一为自己争取平等的途径。
卖血让他证明了自己有着同样强壮且充满力量的身体;让他在一乐闯祸后,可以维系家庭,不用变卖家产;让他可以在曾经心仪的女人林芬芳献身后,提供同等的关怀;也让他在一乐生病时,尽到自己的能力去救回家人。

卖血不仅仅是在换钱救急,更是许三观对自我的确认,卖血给了他尊严,让他找到平等。许三观和20年代鲁迅笔下的农民阿Q以及80年代高晓声笔下的农民“陈奂生”都不相同。阿Q对自尊没有要求,哪怕被打,也只是通过“精神胜利法”找寻平衡。或是说一句“儿子打老子”,或是抽自己两个耳光,很快就忘记痛苦。
陈奂生虽然有了对平等的要求,他感到自己在村子中没有地位,也想要证明自己。但是,他对自己尊严的争取却是通过一种偶然的方式。许三观与上述二者都不相同,他有自尊,也有为了自尊的积极行动力。他以“卖血”的方式换取平等,甚至在无法卖血时,会大哭一场,平等和尊严对于许三观来说有着更重的意义。
二、为感情违背常理
许三观有英雄的“利他”和牺牲精神。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自序中评价许三观时说他“头脑简单,虽然他睡着的时候也会做梦,但是他没有梦想”。也就是说,许三观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说,自幼接受的传统“纲常伦理”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花钱养别人的孩子,简直不能想象。倘若这个孩子还是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人所生就更是伤风败俗,让自己颜面尽毁。

但是,许三观虽然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他恰恰做了这一件按照常理来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许三观的英雄性也恰恰体现于此。大儿子一乐就是妻子和何小勇的儿子,许三观知道实情之后,经过内心的挣扎,最终跟随情感,选择接纳了一乐,把他当做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
一乐离家出走被许三观找到后,许三观当即用卖血换来的钱给一乐买了面条吃;为了给一乐治病,他卖血一路卖到上海,险些丧了性命。同样,在对待妻子的老情人何小勇时,许三观也做出了自己在“纲常”上的退让。
他允许了儿子去帮快要死去的亲爹何小勇“叫魂”,也没有怪罪妻子出现在现场。许三观做的并不是扭转乾坤的大事。但实际上,对于他来说,这些事情的艰难性并不亚于那些看起来崇高伟大的事业。
三、韧性的力量
许三观身上有着英雄韧性抵抗危难的精神。许三观一路走来,经历过许多危难的时刻。譬如,饥荒岁月中,许三观一家面对着饥饿的痛苦,唯一能吃的就是玉米粥。在这种情况下,许三观开始用嘴巴“炒菜”,给孩子们画饼充饥。
这是一种面对困境的乐观态度,体现着鲁迅所认同的“韧性精神”。这是一种不求立即见效,却专长于保存实力来长久抵抗,最终获取胜利的精神。许三观就是这样,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轻言放弃,而是想办法与生活周旋。

在这里,许三观的周旋自然已经不是鲁迅笔下与腐败势力的对垒,而是对于生活中的危难进行抵抗。
同时,许三观的韧性还体现于他生命力的强盛。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他仍旧选择卖血换钱给孩子们买面条吃;在一乐生病后,自己一路卖血卖到上海。
他带有萧红笔下农民的气质,他和在“生死场”上接受着生存磨难,粗糙地生存着的农民类似;和那些在“呼兰河”旁,恣意生长的生命相仿。许三观生命力的强盛体现在他的这种永不言败的人生态度中。这是一种生命的顽强力量,一种无法被打倒的韧性精神。
许三观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但是身上却会显露出英雄的光芒。时代发生变化,我们不必为50到70年代作品中的英雄——《红岩》中的江姐,《雷锋之歌》中的雷锋等,已经不复存在而觉得怅惘。
英雄未曾消失,只是换了面貌。许三观就是一个余华笔下的当代的英雄。他用自己的血汗换来平等;愿意无私地用自己的爱浇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背离自己安身立命的“常理”;身上还带有着韧性的抗争精神,始终坚强、乐观。
铁凝曾经说过,中国的根在农村。挖掘许三观们身上的那些带有民间气息的力量和智慧,为长期生活于饱足时代中的我们注入生命的力量。这似乎仍旧具有独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