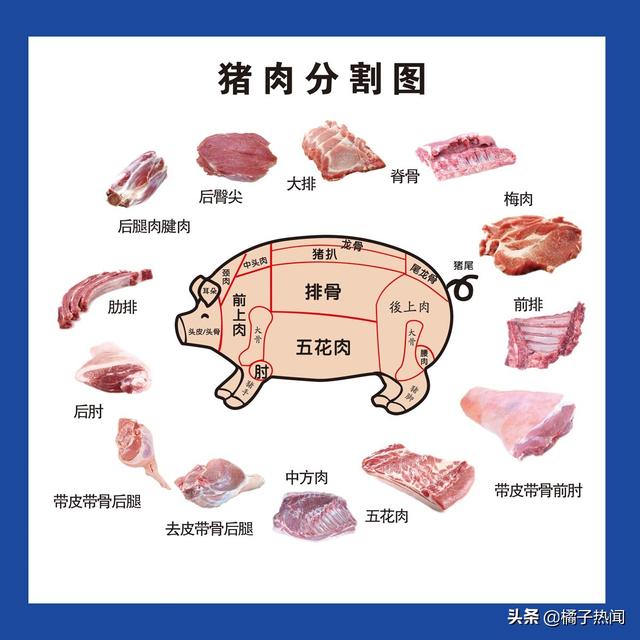【著书者说】
作者:江弱水(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在我的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头几年,陆续出版了好几本中国古典诗词的鉴赏书籍,如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集》,1984年中华书局的《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当然,更有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这本辞典,应该是当代中国出版界的现象级出品,收入了一千一百首唐诗及其赏析,撰稿人有程千帆、萧涤非、马茂元、周汝昌等众多名家。我还记得其中俞平伯先生分析杜甫的《咏怀五百字》,真是抽丝剥茧,令我心悦诚服。这些都是我古典诗词的入门兼进阶的读物,受益很深。

丹葩翠叶娜交加,品赛临安龙井茶。
漫议不堪供茗椀,朵擎仙露是流霞。
清代画家钱维城国画花卉艺术作品。资料图片
细究文心、深具文采的唐诗选本
这本《唐诗鉴赏辞典》,对我来说意义还有另外一层。我买到初版的时候,是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出了校园门,却又像回到课堂上,因为书中有一百五十多篇都出诸我的老师余恕诚与刘学锴两位先生之手,读起来就像是继续在课堂上听讲。刘、余二先生在李商隐研究上所做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他们的课也上得特别好,在普及方面同样是硕果累累。该辞典撰文最多的作者,现在的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正是刘学锴老师的研究生,前些年曾回顾说:“如果说当代唐诗研究有一个鉴赏学派的话,中心就在安徽师大,领头的就是刘、余两位老师。我在校念书时,他们就曾经教导我说,不要鄙薄此道,远不是所有的专家学者都长于此道。”

《指花扯蕊:诗词品鉴录》江弱水著商务印书馆
刘、余两位老师的功业一直持续到今天。余恕诚老师已经去世,他历年所写的赏析文字,已结集为《唐音宋韵》一书行世。刘学锴老师已是88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他从75岁开始,花了4年时间,撰成三百万字的《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的初版,是两块巨砖一样的上下两册,去年分拆为十册,重印了修订本,方便阅读多矣。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作,被誉为近30年最好的唐诗选本,精选了六百五十首唐诗,广泛吸收了学界近几十年整理、考订与研究的成果,而最精彩的部分,正是刘学锴老师那六百五十篇细究文心、深具文采的赏析。
中国古典诗词鉴赏的一本小书
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与渊源,写一本中国古典诗词鉴赏的小书,在我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吧。这本《指花扯蕊》,副题是“诗词品鉴录”。古典诗词导读的书,一般都叫“鉴赏”,也有称“赏析”,而少有叫“品鉴”的。我是爱其五个字正好依次是五声:“诗”(阴平)“词”(阳平)“品”(上声)“鉴”(去声)“录”(入声)。“品鉴”“鉴赏”“赏析”,几个词看上去没什么区别,都是把诗词文本的好处讲出来,教你怎么去阅读,但其实它们各有所侧重。后出的应该是“赏析”,来源却挺古,应该出自陶渊明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把“赏”和“析”联了起来。早出的“品鉴”和“赏鉴”,本来不是针对诗文,而是汉末魏晋人用于对人物优劣的品评与鉴别,故“品鉴”之后是“铨判”,要给予高下的定位。所以,“品”是精确地评判,“鉴”是审慎地观察。《文心雕龙》所谓“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可为定义。总之,客观的成分比较多。而“赏”是对作品仔细体会,反复掂量,含有对其审美价值的看重,并根据个人经验对作品加以脑补和引申。这就较多涉入主观的成分了。
所以,“鉴赏”是兼摄了客观与主观的审美活动。朱光潜的《谈美》有一节谈考证、批评与欣赏的关系,说:“了解和欣赏是互相补充的。未了解绝不足以言欣赏,所以考据学是基本的功夫。但是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只是做到史学的功夫,却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换句话说,“鉴”与“赏”也是互相补充的:“鉴”是“赏”的基础,着手在求真;“赏”是“鉴”的发展,着眼在审美。
鉴赏需要基本的考据功夫。许多文学史上的常识,这些年来陆续被学者们颠覆了。就唐诗而言,陈子昂并没有写过他最著名的《登幽州台歌》,杜牧也没有写过他最著名的《清明》,这些都成了共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真正的作者其实是朱斌,原来的诗题应该是《登楼》。崔颢那首有名的《黄鹤楼》诗,开头一句是“昔人已乘白云去”,而不是“昔人已乘黄鹤去”,那是明朝人擅改的。在这些已然置换了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开始进一步的工作。所以,文学鉴赏首先要甄别文本的真伪,校勘文字的舛误,然后才谈得上对文字的准确解释。
比起给古典诗词作注释,鉴赏者在字句的解释上更不能含糊。坊间有许多诗词选注,避难就易,当注不注,不必注的却注得很勤快。比如说,李白《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里有一句“中间小谢又清发”,我看过好几个选本,都注“小谢”,不注“清发”,大概因为“清”字好讲,“发”字不好讲。类似的情况有苏东坡《水调歌头》的“雄姿英发”,好多选本都解释成“姿容雄伟,英气勃发”,我认为有欠准确。“英”和“发”应该是并列关系,跟“清发”一样,是两个形容词的并列。“英”是卓越、俊美的意思,“发”是舒张、焕发的样子,所以“雄姿英发”是指周郎的姿态俊逸而舒放。再说,“遥想公瑾当年”的“当年”,注释一般都免了,但鉴赏就绕不过去,得说说清楚,不是指想当年,而是指正当年。周瑜正当好年华,且新婚宴尔,所以才写他“雄姿英发”。这都是平常的字眼容易招来误解的例子。
但有些时候我们又不能求之过深。比如最近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对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传统理解是错误的,“龙城飞将”不是指飞将军李广,而是指降于匈奴的李陵,因为李广没有到过龙城。作者根据汉武帝因听信李陵“教匈奴为兵以备汉军”的传言而诛杀其全家的记载,认为“不教胡马度阴山”应该解释成李陵不曾教习匈奴练兵,故使之不南犯。还说“教”字依律读平声,正是“传授”的意思,而“使”“让”的“教”才读仄声。这一穿凿求新的结论,真令人大跌眼镜。程千帆先生早就说过,唐诗中的地名不能呆看。王昌龄这首七绝,“龙城”只是泛指塞上,“飞将”只是泛指英雄。这是超越于具体的史实之上的文学叙述。再说,依平水韵,“教”字作使令用,应读平声;作教学用,才读仄声。作者恰好弄反了却不自知。其实稍微联想一下,“曲罢曾教善才服”“玉人何处教吹箫”,哪个读平声,哪个读仄声,不就很清楚了吗?
在不同语境之间做文本的搭桥手术
文字的意思厘清了,才可以谈结构与节奏、句法与章法、技巧与意境,等等。这些也都需要一番精鉴,要对艺术特色做内行的分析,还要说明此一文本与同时或异代的其他文本的关联,在比较中说明其价值何在,因为只有在一个广阔的比较视野里,才能给予作品以准确的定性,定位,以及定价。
先须有“鉴”,始可言“赏”,才能够“享受美好的事物,领略其中的情趣”,这是《现代汉语词典》对“欣赏”一词的释义,倒是很符合如今很多人讲古典诗词的路数。对于这类鉴赏者而言,作品本身只提供一个跳板,帮助自己好向那些高蹈的思想、优美的情感起跳。我曾写过三篇《撕扇记》,指出某位忽悠型的鉴赏家在知识上的诸多硬伤。他经常罔顾文本的事实而奢谈感悟,“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充斥着故弄的玄虚、故作的深沉。而这不是孤例,一大批读后感式的赏析者,也都不会聚焦于文本进行细读,只把品赏的诗词当诱因,作载体,来寄存自己对人生的种种感叹和领悟。所谓鉴赏,基本是虚晃一枪,就径奔那碗热腾腾的鸡汤去了。这属于典型的印象式批评,是法朗士所谓“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算不上严肃的文学鉴赏。
但“鉴”后之“赏”是必要的,也应该是不拘一格的。不同于注释的大同小异,由于鉴赏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得的经验各异,对作品具有的认知,由作品引发的感触,都会千差万别。于是,对同样的一首诗,不同的鉴赏者各自有微妙的会心,能讲出不同的道道儿来。否则,每一首诗岂不只需要有一篇最好的赏析文章就足够了?何况任何作品都有许多空白点和未定项,需要读者用想象去还原和补足。尽管作者本有意图,作品原有主旨,大致规定了我们解读的方向,但也不可能完全限定它能开启的相对自由的感发与思考。
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把密实的技术分析与发散性的联想结合起来,在对古典诗词的细读中,引用中外古今的诗和小说的片段,穿插点缀一些花絮,与鉴赏文本彼此映照,相互对冲,以激活新的意义,丰富感受的层次,也增添阅读的趣味。有时虽不免枝蔓,但绝非离题万里的不靠谱的发挥。我喜欢在不同的语境之间做文本的搭桥手术。
所谓经典,就是经得起不同时代的人的不同方式的读,本身就有很多曲面,能反射出不同的光影,在不断推移的读者与不断换位的观照之下,呈现出变幻的形象。正因为如此,古典诗词最好有常出常新的鉴赏,这样才可以不断刷新我们对古典诗人的认识。不然的话,古人的自然与社会形态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相对比,简直是换了人间,那么,高铁与微信时代的我们,隔着遥远的时空,为什么还要对那些描述山水之美、田园之乐、羁旅之思、离乱之苦的古典诗词投注兴趣,产生共鸣呢?所以,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过度阐释也是有必要的。这就是鉴赏的妙用。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12日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