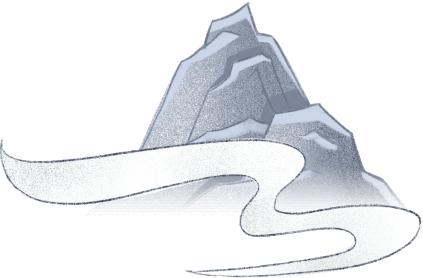
春分
摘要:从民族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大量的民族语地名(用民族语命名的地名)材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任何一种民族语地名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理基础和文化背景,都客观上内隐或外显与民族的生态环境分布、地缘分布、跨境分布相关的大量的文化的信息,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某一特定区域内民族的聚居、杂居与散居程度,历史地折射出区域内的民族构成和空间分布的动态变化。
关键词:地名;民族;生态分布;空间分布;跨境分布
民族的地理分布作为一种区域内特定的地理现象,在地理环境方面表现为生态分布和地缘分布,在空间组合方式上呈现出聚居、杂居与散居的特点。而地名作为一种特定的象征符号,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作为表达方式,显示出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人类群体同相关地理区域之间的一种特定的联系。从民族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民族与民族语地名之间富有历时性的对应关系进行一定的梳理,就会发现地名是探讨民族历史地理分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为此,本文将从地名对民族地理环境的客观反映,地名与民族的聚居、杂居、散居分布,地名与跨境民族分布等几个方面,全面揭示地名与民族地理分布之间的内在复杂联系。
一、地名对民族地理环境的客观再现及其生态意义
地名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原始人类在从事采集和狩猎等社会生产劳动时,必须了解周围的自然环境,知晓什么地方可以采到野果、哪个山坳有野兽出没、何处可以取到生活用水等。在外出采集狩猎时,则必须区别地理方位、辨认方向,以确保能够返回驻地。正是出于生产与生活之需要,地名就产生了。
地理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处于不同生态环境之下的各民族,在通过生产劳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中,慢慢地学会用自己民族的语言,给周围的山川湖海、草原平地、坡崖沟坎、溪水河流等各种不同的地理实体起上一个名字,以便于他们加深对周围环境的识记与了解。然而,由于各民族生活在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中,环境提供的可资命名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故而,处于不同生态位上的民族,各自形成一套对自然环境命名的地名系统。这个以反映自然地理特征的民族语言为基础的地名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这一客观条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民族形成和发展演变之区域地理环境的特点。
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地名系统中,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客观再现该民族所处自然环境的地名语言。这些属于自然要素类的地名,如果再细分的话,一般有以下四个大的类别:地缘形貌类的山岳体系地名、江河湖海类的水域体系地名、方位里程系列的地名和反映动植物区系特征的地名。
地缘形貌类的山岳体系地名,是自然要素地名中最为丰富的地名,它显示的是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要素的关注和依赖。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在对周围自然地理环境的感觉与感知中,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以自然地理实体中的地缘形貌所呈现出来的外表特征,加以恰当的联想、想象而赋予一定的地名。如在青海省境内德令哈地区的“柴旦”,因地处盐碱地而得名;“戈壁”则因该地北部有茫茫戈壁而得名;“织合玛”(藏语意为“红色山岩”),因山岩呈红色而得名;“达尔那”(藏语意为“马耳朵”),因附近两座山呈马耳状而得名。在蒙古语命名的地名中,直接源于地缘形貌的地名是甚为典型的。如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其地形以海拔800~1800米之间的高原为主体,在蒙古语中,“锡林”就是高原平原之意,而“郭勒”,指河川,“锡林郭勒”,意为高原河川;阿拉坦额莫勒,蒙语意为“金马鞍”,以其附近有一座状如马鞍的小山而得名;呼伦贝尔得名于呼伦湖和贝尔湖。从国外的地名中,我们也同样发现有很多源于地缘形貌。譬如,有着积雪山峰的欧洲中部山脉称作阿尔卑斯(Alps),意即“白色的”;北美的落基山脉(RockyMountains),原意为“岩石重叠的山”;美国州名中,爱达荷(Idaho)在印第安人语意为“高山上的亮光”;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意为“大山岗”。

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选择自然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水网地区居住,向来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居住模式。与这种近水而居的习惯相适应,几乎所有的民族在自己的地名文化系统中都包含着大量的与居住地周围的江、河、湖、海等水体,甚至是水体的颜色、流向、大小、深浅等相关的地名。譬如,在我国水网密布的珠江三角洲,粤语一般称小河为涌、津、濠,故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多带这些词,如车陂涌、东壕涌、龙津路、寺贝通津、西濠等。水边地多称浦(埔或圃),如黄埔、东圃、江浦等;堤围称为基或围,如新基路、水松基、同德围、永安围等;河滩地或海滩地称沙,如鸡抱沙、大沙头等。生活在茫茫大草原上的蒙古族,由于水源对于畜群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蒙古族人每当遇到清澈的湖泊,都要称它为“查干诺尔”。于是乎,查干诺尔这个地名,在蒙古族广阔的游牧区内比比皆是。青海的藏族多以游牧为生,他们的畜群同样离不开水源,其地名中有很多与水体相关。如青海藏语地名中的“直曲”,意为母牦牛河,形容长江源头像母牦牛鼻孔中流出的两股泉水;“约古宗列曲”意为流经炒青稞浅锅形状盆地的河;鄂陵湖的“鄂陵”二字,藏语意为“青蓝色长湖”;查灵海(即扎陵湖)的“查灵”,藏语意为“灰白色长湖”;青海地名中的“曲麻莱”是藏语“曲麻莱云”的简称,意为“红色的河,宽广的滩”,县名由境内的曲麻河(又名楚玛尔河)及其东支流莱云河而得名;“格尔木”原写作“噶尔穆”,又称“郭里峁”、“高鲁木斯”等,蒙古语意为“河流众多”,以市区周围小河众多、沼泽密集而得名。
方位里程系列的地名,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要素中的地形、山川河流、地理方位作为参考坐标而命名的地名。如山的左右前后、河的东西南北、距离之间的远近,常常成为参照点。这种地名是人类对周围环境认识逐渐加深的产物,它的产生同样很早。在我国古代,始传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谷梁传》曾明确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论点,并且为后世普遍接受,成为古代地名命名的一个基本原则。譬如,“洛阳”、“汾阳”之得名,因其分别位于洛水、汾水之阳(北面),“汤阴”,则源于该地处于汤河之阴(南面),“沂源”,指的是其在沂河源头一带,“衡阳”在衡山南麓等,就是这一命名原则下的产物。我国省名中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亦是如此。在少数民族语地名中,云南“德宏”因处于怒江下游而得名,傣语称下游为“德”、怒江为“宏”;潞西县因地处“潞江”(怒江另一称谓)之西而得名。内蒙古的“乌兰哈达”(Ulanhad)系蒙古语红头山的意思,以颜色命名;“伊胡塔拉”(Ihtal)蒙古语意为大草甸子,以其地理特征命名。蒙古语的上下用“德尔”(Der)、“道尔”(Door),远近用“浩勒”(Hal)“敖伊尔”(Oir)来表示。提到标志性的地名,我们这里顺便要提的是,在古代蒙古族的游牧区,常常能够看到带有“敖包”的地名。敖包在蒙语中是“堆子”的意思,最初是用石块堆积而成作为道路和境界的一种标志物,后来衍生为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动的地方。

在任何一个地理区域内,动植物的生长各自显出不同的区域特点。生活在相异区域环境中的各民族,在对周围动植物资源的识别和利用过程中,他们要么以某种植物生长的地理环境特点,要么根据植物群体的外貌特征,要么以植物的用途、审美意趣命名地名;有的则是根据某一地理区域内有特征性的动物作为地名命名的依据,这样就形成了很多源于动植物的地名。典型事例如壮族的不少村屯是以动植物命名的。靖西县的“果隆”,意为大榕树,因村前有棵大榕树而得名;“古求”即枫树,因村附近多长枫树,村以树名;“枯柑”是因为该屯种植柑果树多而得名;“巴练”因从前村前路口有棵大苦楝树而得名。在南壮地区,马多的叫马屯,猴多的叫怜屯,老虎成群的村叫“泗邦”(“泗”意为老虎,“邦”是多的意思),鱼多的村叫“板坝”(“板”意为村,“坝”意为鱼)。又,青海格尔木地区的“托拉海”,因该地生长着成片胡杨而得名;青海地名中的“尖扎”为藏语音译,本义为“猛兽出没的地方”,因古代当地人烟稀少、山林茂密、猛兽较多,故名。
如上四种不同类别的自然要素命名的地名,大体上反映了各民族以自然地理要素冠名的一些特点,代表了自然地理地名命名的一些基本方向。由于自然地理要素复杂多样,反映在地名构成上也是比较多样的。在许多民族的自然要素地名中,尚有许多双重或多重地理要素叠加在一起的蕴含着更多地理信息的地名,所以我们的分类是不可能周全的。尽管如此,由于自然地理地名是对民族居住环境客观而又直接的描述,分类梳理之,其最基本的学术价值是:透过这些自然地理地名,我们可以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群体的自然地理环境状况有一个历史的动态的了解。从更高的层面——自然地理地名的生态意义上而言,以自然生态命名的地名,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有些地名已经是名不副实了。著名的草原钢城包头,北依阴山,南临黄河,曾经是水草丰美的草原,晨昏之际,常有鹿群出没,所以名为“包克图”,蒙语即有鹿的地方。鄂尔多斯市的虎石梁,原意为“桦树多的地方”,现在已见不到桦树的影子了;朝垴梁,意为“有狼的地力”,狼也已经不见踪迹。又如云南南涧彝族自治县拉妈苴,彝语意为有大老虎的地方,使人联想到当地历史上森林茂密,有老虎出没,生态环境很好;富民县罗免彝语呼为罗梅白,罗梅为老虎,白为山,意为老虎山,历史上也是林海茫茫、虎豹出没之地;开远市小龙潭乡蚂蚁白村,彝语蚂蚁为马樱花,白为山,意为马樱花多的山,历史上生态环境也很好。上述地名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活动使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地名反映出民族的聚居、杂居和散居分布状况
在当今民族的地理分布中,聚居、杂居与散居是三种最为常见的状态。而这三种民族分布状态,是长时期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就各种民族共同体的聚居而言,无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居,还是血缘与地缘并重的聚居,只要他们较长时期地聚居在某一地,自然会在该地的历史地名中留下反映该民族聚居状况的一系列地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该族体于该地居住的时间越长,对该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越久,留下的民族语言地名就会越多。即是说,族体的居住时间以及对居住环境塑造、刻画的程度,与所留下的民族语地名是成正比的。如在今天的广东、广西,有一些地名出现“那”、“都”、“古”、“六”等字,据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考证》,均为壮语的古代地名用字。如广东新会的那化、阳江的那岳、番禺的都那、南海的古糟、三水的六塘、台山的六合,广西武鸣的那白、容县的都结、贵县的都六、柳江的古练、上思的古都、博白的六务、百色的六那等。由此可以推断,古代壮族人很可能长期住在广东、广西地区。至今,广西仍是壮族的集中聚居区。又譬如内蒙古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作为达斡尔族的一个传统聚居区,在该区域的86个地名中,以达斡尔语命名的单语固有地名80个,约占该地区地名总数的93%,达斡尔语、汉语双语地名6个,约占7%,没有外来语单语地名。

在一个民族历史地理区域内,多民族之间的相互杂居、散居,往往造成两个方面的民族语地名表现。其一是,凡是历史上在这个区域内生活过的民族,或多或少都为这个区域内的民族语言地名宝库中添加了自己民族语的地名。透过这些地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该地区历史上民族地理分布的一些变迁。如青海地区是藏、蒙、回、汉等民族杂居相处的一个重要地理区域,无论州县地名,还是山川、河流、盆地、湖泊、草地等地名,都大量地包含着藏语、蒙语及其他民族语言,尤以藏语和蒙古语的地名偏多。“据1979年青海省测绘局编印的《青海地名录》统计,青海高原的山山水水和行政地名共8200余条,其中以藏语称谓的达60%以上,以蒙古语称谓的约占20%左右,汉语称谓的约占17%左右,土族语、撒拉语、哈萨克语和维吾尔、羌、鲜卑等语称谓的则不足3%。仅以县名来说,全省37个县中,属民族语的就有22个,约占全省37个县的60%,其中除`祁连县'一名属古鲜卑语以外,藏语有17个、蒙古语有4个。至于县以下的乡镇名称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比例则更大。”譬如我国东北的长春地区,由于历史上居住着大量的满族和蒙古族,所以在当地保留有不少的满语和蒙古语的地名,“其分布范围大体上以清代柳条边为分限,柳条边外之西地域如长春、农安、德惠(部分)等市县境内,多有蒙古语地名。柳条之东即边内如九台、双阳、榆树等县境内,多有满语地名。德惠县境处于蒙古族和满族衔接地带,满语蒙古语地名兼而有之。民族语地名分布形势,与历史上的民族源流、民族活动范围大体是相一致的。”又如北京,由于自元明清以来有大量的满族和蒙古族的迁入,所以在北京也能够找到受这些民族语影响的地名,如昂邦章京胡同、沙剌胡同和如今北京西郊的蓝旗营、西三旗、镶红旗等地名,均系满族地名。而什刹海、中南海、西海、后海、海子桥等带“海”的地名,其“海”字来源于蒙古语。说明蒙汉长期杂居相处,因而产生了蒙汉语结合的这些带“海”字的地名。又内蒙古扎兰屯市境内达斡尔族居住区,作为达斡尔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一个典型代表,反映在地名上是在该区的50个地名中,以达斡尔语命名的单语地名为15个,约占30%;汉语、蒙古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等语言地名的数量及比例分别是2个(4%)、6个(12%)、16个(32%)、1个(2%);达斡尔语、汉语双语地名为9个,约占18%;蒙语、汉语双语地名为2个(约占4%)。
表现之二是,在多民族杂散居地区的地名系统中,由于民族的地域性和地域的多民族性,常常出现同地异名或异地同名的地理现象,或者出现大量的混合语地名和双语地名。所谓同地异名,即同是一个地方存在着多种民族语言命名的名称,或者说多种民族语言为某地命名的名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同时被继承下来。如青海湖,藏语称“措温布”,蒙古语称“库库诺尔”,汉语古称“仙海”、“西海”、“鲜水”、“鲜水海”、“羌海”、“卑禾羌海”等,这反映了历史上青海湖地区多民族居住的格局。异地同名指的是,同一个名称在不同的区域内重复出现,所指的并不是同一个地方。这一般是一个部落或部族从原居地移到甲地、乙地或丙地居住时,要么直接把原居地的地名部分地移到甲地、乙地或丙地去使用,要么仍按照本民族固有的命名方式给新的居住点命名。如在蒙古语地名中,据1976年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录》统计,以“查干”(意为白色)开头的地名,达204处。又据197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在吉林、甘肃、宁夏也能够看到不少以“查干”打头的地名。“原来,蒙古族生活在白云之下,养的是白绵羊,喝的是白奶,献的是白色哈达,白色是吉利的标志,所以意为白色的`查干'成了地名中常用词。把带`查干'的地名连成一片就不难看出蒙古族同胞历来活动的地域了。”混合语地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语言混合而成的地名。像昆仑山中支的伊拉博罗山(即阿尼玛卿山),清代称“阿木尼玛勒占木松山”,亦称“阿木尼麻禅母松阿林”。此山名系由藏、汉、阿尔泰语混合构成,其中“阿木尼”、“玛勒占”(麻禅)、“阿林”为羌藏语,其意分别为“祖先”或“圣祖”、“大孔雀”或“河源大山及洲”;山为汉语通名;“木松”(母松)为阿尔泰系语,意为冰,其山峰神奇而多冰雪覆盖,故有此谓。黑龙江地区的绥芬河市,河市为汉语,绥芬为满语,意为“锥子”。金阿林,“金”为汉语,“阿林”为满语,意为“山”。木兰县的大木兰达河,其中“大”、“河”为汉语,“木兰”为蒙古语,意为“江”,“达”为满语,意为“源”,译成汉语为“大江源河”。双语地名,是指一个地方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言的名称并行使用,其中,主要是当地少数民族有一个叫法,汉族又有另一个叫法,两种叫法之间,既不是意译,也不是音译,也即这类地名中的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音义不同,各有各的名称,混合使用。像青海地名中,(汉语)同仁(县),藏语叫“热贡”;(汉语)东沟(乡),土语叫“西吉郭勒”;(汉语)瓦匠庄,撒拉语称“霍孜阿格西”。

民族的地理分布是个异常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今天某一地区或者某一民族的聚居、杂居与散居状态,它既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也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以我国民族的聚居、杂居与散居最为典型的云南省为例,从遥远的上古时期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历史上分属于氐羌、百越、百濮和九黎三苗系统的各民族,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过他们的印迹。现今云南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散居的民族分布态势,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反映在云南地名的整体发展趋势上,在明以前,云南地名中主要是以民族语地名、地貌地形地名以及体现地方性、民族性的地名为主;少量的汉语地名主要集中分布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交通要道和军事开辟居民点等地区。明以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汉族聚居区逐渐由交通沿线、城镇、坝区向山区、半山区扩散开去,反映在地名上,几乎在任何一个地区都能够看到汉语命定的地名,而且汉语语义地名与汉族姓氏地名逐渐成为云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然而,云南毕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无论汉语地名如何增加,民族语地名始终具有广阔的分布面。“全省127个县及县级市中,绝大多数都有民族语地名,全为汉语地名的仅东北边缘的绥江、水富两县。西北隅的民族语地名比例最高,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占97.23%,德钦县占96.28%,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占76.3%,中甸县占76%。西部、南部边缘的各县民族语地名比例也高。泸水县占51.7%,瑞丽市占80%,畹町市占65%,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占49%,沧源佤族自治县占83%,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占92%,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县市占80%,绿春县占90%,红河县占80.9%,富宁县占64%。再靠内,还有一些民族语地名在30%以上的县,如师宗、广南、丘北、双江、墨江、元谋、兰坪、新平、峨山等县。”而在云南众多的民族语地名中,彝语地名最多,有17074条,其次为傣语地名12774条,壮语地名4365条,白语地名4330条,哈尼语地名3813条,藏语地名2852条,傈僳语地名2694条,纳西语地名1829条,拉祜语地名862条,景颇语地名和佤语地名各600多条。其中,彝语地名分布最为广泛,几乎云南全省都有分布。“西北的宁蒗、永胜、中甸各县;西部的大理州除剑川、洱源以外各县,临沧地区北部凤庆、云县、永德、镇康各县,最远达怒江边的泸水和龙陵;南部思茅地区的澜沧江以东各县(景谷除外);以及楚雄、昆明、东川、昭通、玉溪、红河、文山、曲靖等地州县,皆有彝语地名。但是,有的县只有几条彝语地名,有的县彝语地名仅集中在其边缘的某一小范围内,都只能算彝语地名的边缘区。综合分析彝语地名的数量、密度和重要地名比例,则彝语地名集中的范围,西北至金沙江以东,西部包有洱海以东、以南各县,以澜沧江为界,南部以红河为界,并包有红河以南的景东县,东南部包有文山州的文山、砚山、丘北、马关、西畴诸县。”这与云南彝族的地理分布大致是吻合的。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中,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不同的民族分布在不同的生态位上,即民族分布呈现出立体分布的特点。这种独特的民族分布,随之带来了民族语地名的立体分布。一般傣语地名往往在低海拔的坝子或河谷,哈尼语地名在有水源的山上,傈僳语、苗语地名在高山上。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有哈尼语地名274条、彝语地名223条、傣语地名100条,其中傣语地名多集中在低热的元江河谷和甘庄坝子,哈尼语地名在南山区,彝语地名则在其北山区。
三、民族迁徙与跨境民族分布在地名上的反映
历史上的各种民族共同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到他方寻求新的家园。这种民族空间位置的频繁移动,一个最为直接的结果是,不仅在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民族走廊沿线,我们会看到许多民族留下的历史印迹,就是在某一个民族变动急剧的地理区域,也能够寻觅到曾经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民族留下的许多不可磨灭的历史遗迹——民族语地名。所以,在民族史学的研究中,通过全面梳理民族语地名,揭示历史上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迁徙情况,向来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点,且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如历史上的“昆明”一词,秦汉时为族名位于滇西大理,三国时滇东北也出现昆明,隋唐五代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都有称昆明的地名,唐代昆明变为政区名,在今四川盐源设昆明县,元代昆明作为政区名才转移到今址。朱惠荣先生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多个“昆明”,系因民族语地名随着该民族的迁徙而多次移动位置的结果。而吴光范先生则通过对西南历史上出现在各地的多个“昆明”之称的考说,认为古时有昆明部落或昆明族,他们是彝族的先民,是“大种强夷”,又是游牧民族,迁徙于滇川一带,所到之处,族名就演化为地名了。昆明之称的变迁演变情况,反映了古昆明族的迁徙情况。属于氐羌系统的拉祜族,历史上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汉文资料中关于拉祜族的记载也甚为缺略,所以要从有限的文献资料获取拉祜族在西南历史地理区域内的空间变动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有的学者尝试着从民间口头传说资料——拉祜族古歌谣中的地名资料寻求切入点,在认真梳理古歌谣中地名后,认为拉祜族的始祖“必低必修”起源于甘南一带,活动在汉水河畔,江洛与武都之间,成为史籍中“武都羌”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他们逐渐向甘青交界的河湟地带游动,来往于青海湖畔并在青海湖北岸、祁连山南麓的“托拉山”狩猎过。这时的拉祜先民是“河湟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在先秦王朝征伐羌人的战争中,拉祜族的先民又随同其它古羌人一直向南迁徙,大致通过三条道路进入四川,之后又经过三条道路迁居云南。

地名反映民族迁徙的例子还很多。如“以景颇族、阿昌族历史上的迁徙为例来说,在沿金沙江至怒江一带,至今还保留着许多阿昌、浪莪(景颇族自称)的村寨名称。据史书记载,古代浪速(或浪莪)地在今云龙县澜沧江西岸的表村、早阳一带。而清代以后浪速地则在片马以北,两地东西相距数百里,中间隔着怒山山脉、怒江和高黎贡山山脉。连接今日带有阿昌、浪莪村寨的地名,就可以划出阿昌族与景颇族操浪速方言的一部分人,沿金沙江至怒江一带迁徙的路线。再以怒族的迁徙为例,云南丽江县九河乡的龙邑、大格拉、小格拉,剑川县的傥郎村,兰坪县的弥洛衣、恩照村等地名均为怒语,都是怒族先民居住过的村寨的名称。这些地名说明了古代怒族是居住在丽江、剑川一带的,后来逐渐迁移到兰坪的澜沧江两岸,最后又进入怒江地区居住的。”又在广东、福建等省区,有不少的“畲”字地名分布。1984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处对广东省31.5万条地名调查时,共整理出带“畲”字的地名793处。司徒尚纪也说:“以畲或为首尾地名多分布在山地、丘陵和台地地段,尤以内陆客家人地区至为普遍。例如平远有欧畲、下畲、季花畲、良畲……河源有横畲等等。”在福建,据陈龙统计,全省带畲字地名有231处。这些“畲”字地名,显然与畲族的早期分布有关。“畲既是族名,也是他们`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奇怪的是,现今的畲族居住地(闽东、浙南)倒是未见带畲字的地名。因为他们迁居到闽东、浙南时,当地已经早有其他地名了吧!从以上分布可以看出,畲族在福建早期聚居地主要在武夷山区自北向南延伸。这就为史学界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证据,看来,居住在武夷山区的闽越国人与畲族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民族。”畲族早期居住在闽粤交界处,后来自闽西迁经过闽北逐渐往闽东和浙南。
上面,我们是从地名看单个民族地域空间的变动情况。从一个具有相似文化的民族集团在一个相对宽泛的地域内所留下的民族语地名,也可以看出这个民族集团的变迁情况。如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通过对秦汉时期吴越与古岭南地名的对比研究发现,这两个地区有很多地名不仅冠首字类同,而且都属于齐头字,由此表现出来的相似性。他们推断,在周秦以前,江、浙、闽、粤一带为百越族群所居,后来这些民族大规模迁居两广、贵州、云南一带,自然会把一些地名的命名习惯带到新的居地,所以我们在秦汉时代的吴越地名中发现一些与古岭南地名相似的地名。
在当今世界民族居住格局中,由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移民和国家领土的赢缩等因素的影响,使某些在历史上同属于统一民族的群体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呈现出跨国境分布的状态。这种跨境而居的民族,由于历史的或居住地彼此相连等因素的影响,他们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国度,但在历史传统、文化特点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性。反映在民族语地名上,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民族语地名在不同国度的重复出现,或者说民族语地名亦呈现出跨境分布的特点。如我国南方及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以“那”字冠首地名的区域性分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据相关研究资料显示,“那”字冠首地名的分布范围,其东界中国广州湾东珠海市的“那洲”(沙洲的田),西界缅甸掸邦的“那龙”(大块的田);北界为中国云南宣威市的“那乐冲”(“冲”为汉语方言,意为山冲谷地的田),南界至泰国宋卡府的“那他威”(意为成双的田)。这块弧形地带,包括中国的广东、海南岛、广西及云南南部及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掸邦地区。“那”类地名在上述地理区域内的集中分布,说明此区域内的土壤、雨水、气温、日照等都宜于水稻栽培,而操壮泰语的诸民族群体,他们以稻作为生,称水田为“那”,在水田的周围聚族而居。而且,随着稻作民族的流动迁徙,含“那”字的表示水田名称的地名,随之也扩大成为一村、一乡、一镇、一县以至府城的名称。就是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首字冠那的地名,不仅成为壮泰等民族稻作文化的一种鲜明标记,还逐渐的成为融地域性、历史性和民族性的独特的地名文化景观。

不同国度同一地名的重复出现,实际上与民族的跨境而居也是不无关系的。如在东亚大陆的北部草原地带,同一民族虽然分居多处,但他们由于按照相同的方式给聚居地命名,故而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出现了许多相同的地名。如“蒙古国扎布汗省的吉布哈朗图、南戈壁省的敖包图、中央省的克尔伦、肯特省的达尔罕、科布多省的阿勒泰、东方省的查干敖包、巴彦乌拉盖省的查干诺尔等地,分别在中国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新疆阿勒泰地区、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阿巴嘎旗等地,多次重复出现。尤其蒙古国东方省的巴彦乌拉这一地名,在中国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巴林左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出现。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的巴彦查干这一地名,在中国内蒙古克什克腾、西乌珠穆沁、扎鲁特、新巴尔虎左旗以及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等5地重复出现。在同一国内,各地区之间也有这种现象。如巴彦塔拉一名,竟然在扎鲁特、科尔沁左翼中、乃曼、巴林右、西乌珠穆沁等5个旗县出现。白音和硕一名,也在东乌珠穆沁、西乌珠穆沁、巴林右、科左右、鄂托克等5旗重合。达斡尔族地名,也有同样的规律。雅克萨城,在俄罗斯境内,位于提威河湾,阿尔巴金城东。在中国则称雅尔斯屯,位于齐齐哈尔市城北,嫩江右岸。同是由达斡尔族先民所建。多金城,也在俄罗斯境内,位于黑龙江支流盘古河口东南,达斡尔敖拉氏所建。在中国有多金屯,位于嫩江上游左岸,同是敖拉氏所建。博尔多村,也在俄罗斯境内,原江东六十四屯之一。在中国的博尔多,位于嫩江左畔,今黑龙江省讷河县城,古称博尔多。鄂伦春族地名,也有同类情形。俄罗斯境内的布利亚河,原是鄂伦春人居住之地。中国黑龙江省逊克县鄂伦春族居地,也有一个毕拉河之名,与布利亚河同音异译。这说明跨国居住的民族地名,既有国际之间的地名重合,又有一个国度内各地区之间的地名重合,这是历史地名文化的一种普遍现象。
综合以上三个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种民族语地名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理基础和文化背景,都客观上内隐或外显与民族的生态环境分布、地缘分布、跨境分布相关的大量的文化的信息,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某一特定区域内民族的聚居、杂居与散居程度,历史地折射出区域内的民族构成和空间分布的动态变化。

来源:《贵州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报)》
2007年第3期
作者:管彦波
选稿:常宏宇
编辑:刘聪
终校:黄舒馨
审订:郭娟
先秦货币地名与历史地理研究
我国河流名称变迁的规律及成因
云南省掌鸠河流域近300年来聚落空间演变
唐波斯都督府治所地名问题考辨
荆门若干三国历史地名述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