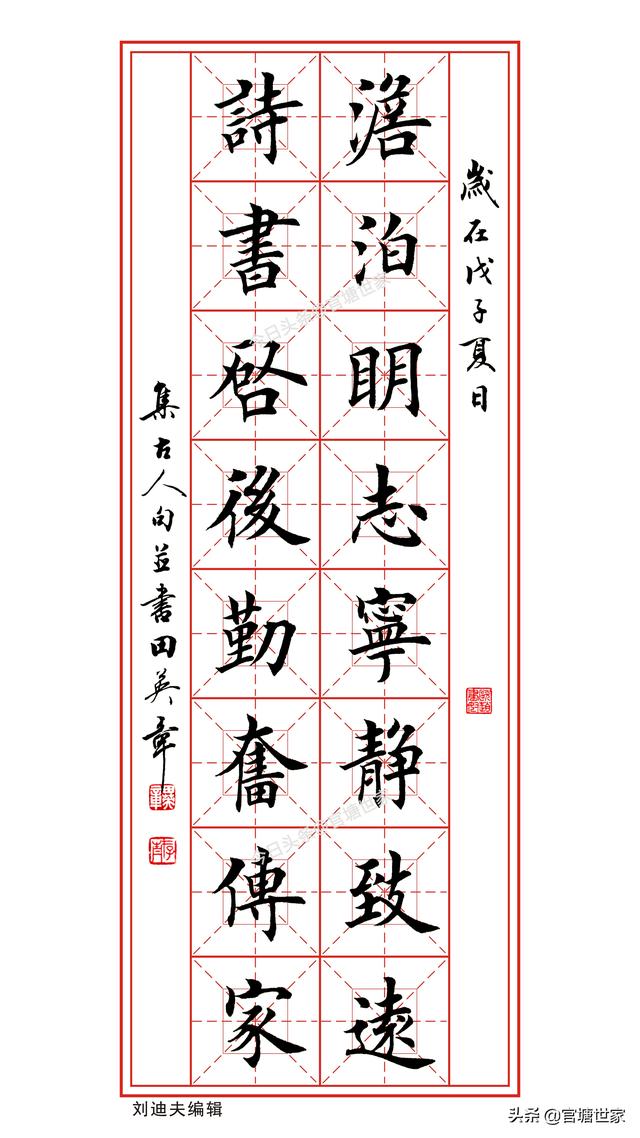1992年,冰心在北京家中与猫在一起。 (视觉中国/图)
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只愿我的作品/在人间不露光芒/没个人听闻/没个人念诵/只我自己忧愁,快乐/或是独对无限的自然/能以自由抒写/当我积压的思想发落到纸上/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冰心
“我所说的,你们都会如实报道吗?”接受采访前,冰心的小女儿吴青首先抛出这个问题,“我母亲一辈子讲真话,你们新闻媒体更是要讲真话。”
整个疫情中,吴青最怀念的人是母亲。母亲去世前一年,还在关心当年洪灾的状况。她的笔触曾描绘人类共同的痛苦和欢乐,期望与救赎,这点到今天更显珍贵。
从19岁登上文坛到2019年,冰心成名已经一百年。百年间,在历史书写中留下姓名的女性寥寥。但在新文学初创期的中国文学版图上,冰心却是无法跨越的。中国文学史中,隐匿着太多无声的女性,能够为自己书写的女性是稀缺的,也是宝贵的。
作家冰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带着文化界对新女性的期待登上文坛的。她少年成名,32岁时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全集”。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了极高的赞誉,这在那个女性声音几乎被遮蔽的时代是极其罕见的。
女性文学的重要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将冰心叫做“文坛祖母”是恰如其分的,在冰心最负盛名的时代,她写的每一部小说都会立刻被学生改编搬上话剧舞台,她影响了一代代青年作家的成长。冰心以今天的眼光看就是一位“新媒体”作家,她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晨报》成名,以崭新的新女性姿态来介入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在文坛一出场就让人耳目一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青年巴金是冰心的忠实读者,他说,“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
“文革”期间冰心被组织派去在作协四楼打扫厕所,扫了三年半,除了偶尔有好事之徒上去看看,她总是孤独一人。一位从海南岛来的读者特意走上四楼,告诉她:“冰心你是好人,对我影响很大。”来自陌生人勇敢的善意,从侧面证明了冰心文学的巨大作用:她让人不畏惧极端年代的恐怖,敢于坚守爱和真的价值。
这位和20世纪同岁的作家,她对自己的苦难总是选择缄默。吴青回忆,1950年代,家里一下出了三个“右派”,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文革”中大家离散在各地,但再重逢,谁都不提自己的遭遇。
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里,冰心以看似简单的观念“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声音是轻柔的,姿态是温和的,态度甚至有些讨好。但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却对抗了那个动荡年代的主流话语,成为温和的叛逆者。在后疫情的今天,全球化遭遇到阻隔和危机,在纷繁撕裂的价值观面前,她的这句话依然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量。

1980年代末,北京家中的一次聚会,听吴青讲做人大代表的心得。(从左到右分别是冰心、赵朴初、叶至善、吴青) (吴青供图/图)
“冰心女士”的另一面
张莉指出,冰心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经典化”了,她的小说中那种对优雅、纯洁女性形象的刻意塑造和克制讲述,使她收到了雪片一样的读者来信,也受到了密集的赞扬,但也让她的所思所想被遮蔽在读者对“冰心女士”的期待中。
在一般的观点来看,冰心的作品温和有余,批判不足,她的个人主体性是被规训的,似乎被“好母亲”“好姐姐”等形象掩盖。后来的女性主义者甚至批评冰心,认为她的写作过于干净,没有情欲。“不过是披着女性外衣的男性想象物”。
但若是仔细考察冰心的创作,似乎又不能这么理解。
1900年10月5日,冰心出生在古城福州隆普营,取名谢婉莹。19年后,“五四运动”涤荡了一代青年的思想,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化预科一年级学习的谢婉莹也参加了运动,她被选为学生会的文书,参加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担任文字宣传工作。
当年8月,当局逮捕学生,谢婉莹作为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成员参加旁听,以“女学生谢婉莹”为名在《晨报》发表了自己第一篇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文章一出,引发了广泛讨论,那时候以女性的身份发表文章的人少之又少,何况还是这种针砭时弊的内容。
不久,谢婉莹又以“冰心女士”为名在《晨报》发表了小说《两个家庭》,开始了此后八十年的文学生涯。“冰心”之外加上“女士”,是《晨报》编辑有意为之,他嫌“冰心”过于中性,因此突出了女性的特质。《两个家庭》连续五天在这个当时北京影响最大的报纸连载,“冰心女士”走进了千家万户。
1919年,冰心写作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等一系列作品,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星期都有出品”“多半是问题小说”。她最初的作品就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青年人在夹缝中的状态。早慧的冰心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真诚地将自己的问题意识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
文学搭载了冰心关心社会的热忱,也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1920年完成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的学习后,她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因为在文坛的成就,她直接跳过一年级,升入二年级。
1921年,冰心参加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有了“为人生”这样的艺术宗旨,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等。她于同年在《小说月报》发表了早期代表作《超人》。
《超人》的故事很值得玩味,讲述了冷漠的青年何彬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世上没有让他提得起兴趣的东西,也不愿意和人交往。因为深夜被凄惨的呻吟声所困扰,他于是给了跑街的孩子禄儿一点看病钱。禄儿写了一封长信感谢他。何彬坚硬的心被软化了,他意识到:“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在这部作品中,冰心渐渐把对母亲和自然的爱上升到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她女性特有的共情能力,从对母亲的赞颂移情到对弱者的同情,这在当时具有绝对的进步性。
1935-1936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对冰心的介绍除了诗人、小说家之外,还强调了“文学研究会干部”,所谓干部,在当时的语境来看就是主要参加者,主力的意思。《中国新文学大系》从文学史意义上赋予了冰心较高的位置。
但是,随着冰心成为当时市场上最被热捧的作家,茅盾等“左翼作家”对她发起了批评。认为她的作品题材贫乏、离现实太远以及“爱的哲学”解决社会问题的虚幻性。但郁达夫等知识分子则认为:“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苏雪林将冰心小诗的成就排在首位,认为其在新诗坛获得了特殊地位,同时认为,冰心的散文(苏雪林称其为小品散文)和短篇小说也值得享有盛誉。
更有甚者,文学史家赵景深将冰心笔下的“爱海”以精神分析学为依据,解读为“性欲的象征”。这个说法虽相当牵强,却也揭露出在早期文坛上,冰心的文学面貌就是被不同的观点和话语建构出来的。
“温和”一朝成“叛逆”
吴青的描述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自1951年从日本回国后,冰心的写作渐渐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吴青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人道主义被阶级立场所替代的时代里,她不敢再阅读母亲的书。
1957年,冰心写作了著名的《小橘灯》,这篇文章的故事简单:“我”去朋友家,朋友不在,在电话亭打电话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小姑娘。小姑娘的母亲生重病,“我”帮小姑娘给医院打了电话。小姑娘回家后,“我”一直惦记着她,便到她家去看,得知医生来过,母亲病也好了一些。最后,小姑娘用橘子做了一盏灯送“我”下山……
文章的最后,冰心才点出小姑娘的父亲是因为同情革命者才被抓走的背景。文章的核心依旧是她一贯的“爱与同情”的思想,是一种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照。这种写法在当时已然不在主流写作之中。而其结尾,“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对应当时冰心一家的状况,不像是革命的召唤,而是一种自我安慰。小橘灯作为爱与温暖的象征物,对冰心个人也许也产生了鼓舞的作用。
那一年,吴文藻被划成了“右派”,他的日记记录下当时的精神状况:失眠。高烧后胸部头部都感不适,精神急剧下降,连躺三天仍觉甚弱……神经失常。皮肤出疹。午后理报阅报,阅过即忘,记忆不了,心甚焦灼。向反右14人小组试作检查,检讨中情感失常,哭不成声……很难想象这位中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遭到了什么样的煎熬,有人劝冰心和吴文藻离婚划清界限,冰心断然拒绝:“我怎么和他离婚?我们想的一样!”
冰心曾在1932年出版《冰心全集》在双清别墅写作长序的时候,回应过对自己的种种误读和对“爱的哲学”的批评。“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
1977年,冰心夫妇和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见面,谈到了当年的这段往事,她说,“那时和后来,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的‘信仰’二字。”在席间,冰心借此回答了韩素音对自己“文革”中处境的关切,她说:“《圣经》中说,当你在舒适中走出,可能就是一次新生。没有这种走出,我们的人生将会如何的萎缩,那是不可想象的吧。”
回到冰心作品本身,它们是温和的,也是属于大众的,所影响到的是最广大的一群人。冰心带着现代启蒙意识姿态介入儿童文学的书写,塑造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她的女性主义立场和“新贤妻良母主义”展现出这位处在新旧交替时代女性身上现代性与古典性的矛盾张力与交叉融合。冰心是典型的20世纪早期的女性知识分子,但她的“温和”在意识形态泾渭分明的时代里也成为了一种“叛逆”。
曾任冰心文学馆馆长的王炳根认为:“解决由于社会变革带来的人的心灵与追求的问题,并非只有绝情、出走、斗争与革命。母亲的爱、童年的回忆与大自然的召唤,同样可以救赎心灵,达到平衡,实现人生理想,现出美好的前途与光明。也就是说,爱的实现,便是人性与社会异态的消失与常态的回归。这种理念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与文化观念中,冰心是唯一的。”
“还给儿童一个纯净的儿童世界”
1923年,冰心远赴美国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专事文学研究,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把自己在旅途和外国的见闻写成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冰心以姐姐的姿态,富有情感地写道:“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
回顾冰心的文学生涯会发现,她的《寄小读者》至今占据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以至于掩盖了作家冰心的其他面相。这其中固然有人们的“误读”,也彰显出冰心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她相信孩子,热爱孩子,在她这里儿童不是成人的书写的对象,她把他们当做和自己一样的,大写的“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重视儿童,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更是晚近的事情。五四运动之后,周氏兄弟倡导的“儿童本位”慢慢被人接受,儿童文学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
1923年,叶圣陶发表了童话《稻草人》,冰心的《寄小读者》在《晨报》的连载,中国儿童文学有了一些面貌。到了1930年代,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渐渐让儿童文学蔚为大观。此后郑振铎、陈伯吹、贺宜、严文井、金近等作家陆续有了非常丰富的创作。
学者吴翔宇在《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中指出:当时的儿童文学和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息息相关。在五四中国的复杂语境中,儿童文学自觉承载着“立国”与“立人”的特殊使命。“因此,在‘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真正肯定儿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主体价值,试图将其从成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给儿童一个纯净的儿童世界的文学作品是少数的。”儿童文学承载着成人对儿童的借代幻想。成人依然掌控着儿童文学的话语及运作。
以陈伯吹1934年创作的童话《阿丽思小姐》为例,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天真的小女孩阿丽思在梦境中进入了一个动物王国,但读者不难发现,这个动物世界就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射。
茅盾指出,“五四”时代开始注意的“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五四”儿童作家站在思想启蒙的高度来审视儿童,书写了一系列儿童形象。
针对冰心超然物外的儿童书写,茅盾却给予了激烈的批驳:“她这‘天真’,这‘好心肠’,何尝不美,何尝不值得赞颂,然而用以解释社会人生却一无是处!”冰心的意识却不同,她曾在《寄小读者》中呼吁儿童作家的出场:“‘儿童世界’栏,是为儿童辟的,原当是儿童写给儿童看的。我们正不妨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竭力占领这方土地。有什么可喜乐的事情,不妨说出来,让天下小孩子一同笑笑;有什么可悲哀的事情,也不妨说出来,让天下小孩子陪着哭哭。只管坦然公然的,大人前无须畏缩。”
但是,冰心和儿童的约定很难在“五四”时期实现,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在这一时期并未产生。或者说,真正理解冰心这种期待和希望的儿童也是非常少的。从冰心收不到儿童回信的失望情形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天两次,带着钥匙,忧喜参半的下楼到信橱前去,隔着玻璃,看不见一张白纸。又近看了看,实在没有。无精打采的挪上楼来,不止一次了!”
事实上,在儿童文学的书写上,冰心是一位真正的先驱,她要突破成人与儿童天然的边界,需要找到两者共同的心理基础和心灵记忆,那就是通过对“童年”的共同经验。但以今天看来,冰心这种完全尊重儿童天性,将成人和儿童放在平等位置对话的儿童文学观念,既天然是进步的女性主义的,也是更具有当代性的。
在张莉看来,冰心在儿童文学领域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后来的“知心姐姐”类型,也是从《寄小读者》开始的。她将富有美感的文字与温和温柔的表达相结合,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一条脉络。
“那些日本孩子侵略过中国吗?”
冰心一生追求博爱,在女儿吴青看来这背后是宏大的全球化视野。冰心的父亲谢葆璋遭遇过甲午中日海战,所在的“来远”舰腹背受敌,险些葬身大海。谢葆璋是凭着一身好水性,拼命游上刘公岛,才得以死里逃生的。
直到晚年,谢葆璋心心念念的不是当年战争的惊险和仇恨,而是在接收“来远”舰的仪式上,中国竟然以临时选的民歌曲调来代替国歌演奏。这件事深深刺痛谢葆璋的心,许多年以后,他还常常讲述这件事警示子女,但却并不教他们民族主义式的仇恨。
冰心是谢葆璋最大的孩子,她之后才陆续有了三个弟弟,他们不称呼冰心为姐姐,而是以“萤哥”代替。谢葆璋不以旧式女性的标准来培养女儿,力排众议不让她缠足,悉心教导她读书写字,甚至还有骑马。他常对朋友说,“这是我女儿,也是我的儿子”。在海军学校的环境中,冰心的天性得到十足的解放。
谢葆璋虽是旧式军人,但和严复、林纾等人都有交往。对他们翻译的《论自由》《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以及《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书都有涉猎。他这一代背负着中国人屈辱的历史,“救亡图存”的信念很强。但他没有教冰心仇恨,而是教会了她如何去爱这个国家,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师,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中国人。
他不是基督徒,却将自己的孩子都送进了教会学校,相信西医,用西方的方式教育子女。吴青继承了家族的传统,少年时在日本度过,“文革”结束后,在中央电视台上教全国观众英语,1980年代远赴美国学习。
1946年,冰心随丈夫吴文藻一同去日本工作,并在东京大学任教。在日本生活的时候,吴青当时年纪小,对日本人有种发自内心的恨,她却还记得母亲经常招待在美国做同学的日本阿姨,每周请她们来聊聊普通人对战争的看法,都会嘱咐家里的厨师做够饭菜,让她们和家人一周至少吃一顿饱饭。
有一次,吴青看到了一本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就组织了自己的小伙伴,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追日本孩子。几次三番下来,冰心知道后对她说:“小妹,那些日本孩子侵略过中国吗?在你追的这些孩子中,有的人可能是孤儿,有的人的父母可能就是因为反对军国主义而被关进监狱的。人家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可能被你吓得再也不敢出来了。”
冰心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抗争中,她拉扯着几个孩子躲避战乱,没少躲进防空洞。因为颠沛流离,她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即使如此,在《从重庆到箱根》她写道:“战争结束我们懂得了怨。而且我们虽然体验了激烈的战争,也懂得了同情和爱。因此,我在歌乐山最后的两年中,听到东京遭受轰炸的时候,感到有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之情。我想象得出无数东京的年轻女性担心着丈夫和亲人,背着柔弱的孩子在警报声中挤进防空壕那悲惨的样子。”
回溯母亲的历史,吴青发现了一部世纪华人开眼看世界的历史。从福建出发,经过烟台到北平,再去美国,早年冰心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是人道主义的信徒,为了探寻真理,走出安稳的书斋,以身体丈量世界,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逗我的动作比兄姐都多,在家的时间比陈恕还少。”——晚年冰心保持着一贯的幽默感,1988年题词送给女儿。(陈恕为吴青丈夫) (余雅琴/图)
“妈妈的思想塑造了我”
吴青回忆起小时候和母亲的相处,冰心从不会把自己当成孩子来管教,她尊重孩子的天性和选择,与孩子建立一种绝对平等的关系。自己和母亲最像,从小就是野孩子,凡事富有反抗精神。姐姐学习好,而自己更喜欢漫山遍野地玩,母亲就给缝制了大红色的衣服,好远远地可以看见自己在山林里穿梭。吴青小时候想要狗,母亲教会她“人吃饭,狗吃饭;人喝水,狗喝水……”若是可以照顾小狗,承担养狗的责任。这种承担,吴青记了一辈子。
至今,对吴青来说,童年的下雨天,母亲抱着她在长廊边讲故事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冰心给女儿讲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也讲童话《三只小熊》。《三只小熊》里一只熊好吃懒做,一只特别自私,只有最小的熊又勤劳又大方。冰心问吴青:“愿意做哪只熊啊?”吴青回答:“最小的熊。”每到这种时候,母亲总会抱着她亲吻。在吴青的印象里,母亲的亲吻和拥抱是很多的,给了吴青无限美好的童年回忆。
吴青今年已经八十三岁,父母和老伴相继去世后,她依然住在冰心生前居住的三居室。尽管书籍大多已经捐赠,不算大的屋子里仍全是书。她胯不太好,出门要拄拐杖,但每天坚持下楼锻炼,因为“有太多重要的事要做”。吴青独居,但她坚持不请家政阿姨,每一天都会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些习惯和母亲在世的时候一样。
疫情暴发之前,吴青还要去远在昌平的农家女学校上课,疫情中则坚持上网课。如此这般,吴青已经为农家女学校讲了二十二年课,听众两万多人。上课的时候,吴青总是将母亲送给自己的宪法随身携带,告诉农家女姐妹们法律可以赋予人的尊严与权利。她总说,“女性要永远记住你先是人,才是女人。”
吴青和农家女学校的缘分要追溯到三十年前,1990年夏天,吴青作为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聘请的社会性别专家,前往甘肃会宁考察。中国基层农村的贫困令她震惊:孩子没有夏天的衣服,还穿着补丁加补丁的棉衣棉裤。这件事给吴青的触动很大,她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中国农村,而其中的核心就是农村女性,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决定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可能性。
1993年,原《中国妇女报》编辑谢丽华创办了《农家女百事通》杂志,邀请吴青做顾问。三年后,她们一起创立了“打工妹之家”,维护女性农村进城务工者的权益。1995年,吴青和谢丽华作为代表共同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期间,谢丽华有了办一所让农家女学会自立的学校的想法,吴青也十分赞同。回家后,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冰心当即把才出版的全集第一笔稿费九万多元捐献了出来。这笔钱成了农家女学校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如今,她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依然树立在农家女学校显著的地方。
晚年的冰心身体并不算好,1980年得了脑血栓,吴青陪母亲住院,她感受到冰心内心的坚强。刚进医院的时候,冰心情绪很坏,她右半身偏瘫,偏瘫以后就不能写作。后来,冰心就开始练字,手握笔从半个字,一个字到五个字,十个字,后来写手都不抖了。到了1990年代,冰心的字已经和从前写得一样好。这中间付出了怎么样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冰心在写给小读者的信里写下“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也是这么做的。王炳根回忆:八十岁后的冰心,几乎足不出户,在家里也要靠助步器行走,但是她的信息很畅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断有人来看她,和她谈社会的种种现象。因为身体较弱,来看她的人又多,医生告诉她要谢客,门口写着“医嘱谢客”四个字。但是找上门来的,她都会打开让对方进去,和他们聊天。
1984年,吴青遇到北京市海淀区人大进行换届选举,她欣然接受了提名,并在当年3月5日,首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得知这一消息的冰心送给女儿一本198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履职人大代表的27年中,吴青因为经常运用宪法和法律维护公民权益为社会熟知,也引发不少流言蜚语和误解。冰心因此提笔赠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做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爱女吴青。”

吴青做人大代表投反对票引发争议,1989年冰心以林则徐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鼓励爱女。 (余雅琴/图)
1987年,冰心得知一些地方连小学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小学老师工资拖欠严重。久不写小说的她立刻写出了《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独白》,小说以一位大学副教授的口气,自述其与经商同学、身边出租车司机等人的收入差距,感叹教师境况窘迫、教育不受重视。这篇文章在冰心晚年写作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吴青说:“妈妈在80岁之后创作又是一个新高潮,那时候巴金‘舅舅’(编者注:巴金和冰心以姐弟相称)也在写《忏悔录》,他要讲真话。为什么巴金跟我妈妈成为好朋友,因为他们求真,对读者有真爱。”张莉也认为,晚年冰心越来越犀利,越来越敢写,因为此时的她开始懂得了什么是解放自我、什么是自由表达,她开始懂得了“自由表达”对于一位写作者的宝贵。
冰心一直写作到94岁,生命最后的几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但即使最后已经需要依靠鼻饲生活,她依然关心1997年的香港回归,1998年的洪涝灾害等大事。1990年,她就立下了遗嘱:
我如果已经昏迷,千万不要抢救,请医生打一针安定,让我安安静静死去:遗体交北京医院解剖;不要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骨灰放在文藻的骨灰盒内,一同洒在通海的河内;存款,除了分给吴平、吴冰、吴青的,其余都捐给现代文学馆。墙上的字画和书柜。书架上的书,有上下款的,都捐给现代文学馆;我身后如有稿费寄来,都捐给现代文学馆;书籍里面,没有上下款的,可以捐给民进图书馆(工具书你们可以自己留下)。
遗嘱立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冰心又做了修改,将存款其余都捐给“现代文学馆”,改为“希望工程”,冰心希望将最后的微薄之力献给贫困的孩子。
吴青看到不平的事,就想站出来说话,走在路上看见有人乱丢垃圾要上前阻止。过马路看见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她也要指出。疫情期间,她更是忧心忡忡,“你说我觉得过得平安吗,我一点不平安,我看到周边的人,就觉得人怎么活?”
2019年,吴青到苏黎世开会,主题发言是《我是一个动词》。她讲:“我是一个动词,我想到的事情就去实践,我就是要做事。另外,我是世界的公民,人必须有一个世界的意识……”
吴青说:“我觉得妈妈的思想塑造了我,妈妈也觉得我是最像她的人,其实爱就是责任。你爱这个人你就对他(她)负责,你爱这个国家,你也要负责,有问题就要批评,要发声。”
王炳根说,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冰心过时了,但她的思想在疫情当下还不够有当代性吗?“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仔细品味这句话,能解决多少世界上的事情。
冰心已经离世21年,她留下的精神财富,依然是研究20世纪文学和历史重要的文本。读者通过冰心在不同时代对“爱的哲学”的书写与演变,从五四时代的“母爱”,到人道主义之爱,最后落脚在“博爱救世”,我们可以从冰心的创作中,看到时代价值取向的转变。
(参考资料:《冰心全集》,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卓如《冰心全传》,张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吴翔宇《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等。)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余雅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