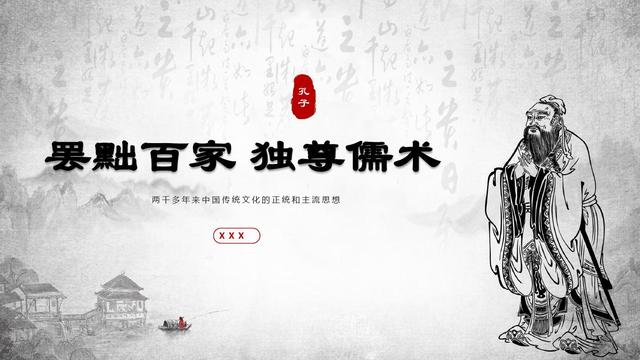们听过一句话:秦皇汉武,而实际上,在汉武帝实现中华帝国真正成了具有当时全球影响力的真正的大帝国,甚至他的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皇权至上真正实现了秦始皇所想要达到,而未能达到的辉煌的战绩。
汉武帝16岁登基,享年70岁,在位54年。这两项记录在中国的帝国史上都较为少见,在汉武帝时期,确实成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比如在汉武帝时期,汉朝的政治、经济、政府、军事、文化都达到了鼎盛,一个国家的疆域,东邻韩国,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当时称超级大帝国同样的辉煌灿烂,董仲舒、司马相如,音乐家李延年,探险家张骞、农学家赵过都出生在这个年代,在历史上,还有汉武帝非常不喜欢但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秦并天下之后,进入汉朝的历史进程。
汉武帝剧照
1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帝国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
在大汉朝里,汉武帝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皇帝之一,他的历史功过任人评说,比如很多人都知道他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因此在近现代受到了很多批评。但让人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儒家守护者的形象,在历史上却有着不同的评价,比如在汉武帝去世后的第六年,就有儒生在盐铁会议上抨击汉武帝的政策,而且从此以后,包括班固、司马光在内,历代的儒生门徒们都开始对汉武帝有着很多或明或暗的负面评价。总结来说,汉武帝在对待儒家的做法上,有点两头不讨好。
那么,儒生们为什么会抨击儒家文化守护者汉武帝的做法呢?《易中天中华史之汉武帝帝国》带着我们分析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首先我们看一下独尊儒术给中国带来的价值:在秦汉之前,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的百家争鸣固然是思想史上的幸事,但同时也导致了人们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而独尊儒术正是解决了这一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在当年面临了哪些困难。汉武帝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他的祖先不喜欢儒家,比如刘邦喜欢往儒生的帽子里面撒尿,而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相比儒家更喜欢道家,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汉初之际,国家为了恢复生计,实行的主要还是黄老之术。而汉武帝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他自己其实也不信儒家,比如他重用酷吏,在他当皇帝的时候,丞相是一个高位的职业,就连他的大臣都曾经直接揭他的底:你的内心充满了欲望,何必装模作样的装仁义呢。
那么汉武帝为啥非得和自己和大家扭着干去独尊儒术呢?其实这和当时的社会形态有着密切关系,在文景之治后,国家的元气已经逐渐恢复了,国库里堆满了钱,但同时那些中层的豪强也开始冒头了。他们收容各地的江洋大盗,甚至会跑去各个王国兴风作浪。因此,对于汉武帝来说,这是在挑战天子威严的行为,必须根除。
那么要打击这些豪族,首先要除去的就是支撑豪族到处兴风作浪的理论基础,比如纵横家、法家学说,但是这一点被扩大化妖魔化之后,就成为了我们常说的罢黜百家。但实际上,汉武帝并没有把诸子百家都灭掉,他更没有派兵去烧掉民间的书籍,他的目标一直都很明确:纵横家。而法家这个武器,只允许掌握在皇帝手中。相比于秦始皇,他们两人都是为了统一思想这同一个目标,但是秦始皇的手段过激,而汉武帝却找到了合适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儒家。
为什么说儒家是合适的统治工具呢?其实我们翻开儒家的思想就可以发现,儒家和法家都是维护君主制度的,但是法家更多地依靠绝对权威、严刑峻法,结果秦朝传了两代就结束了。而儒家却相反,他们是用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管理百姓,相对来说显得更有人情味,对于君主和百姓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程度。也正是因此,当儒家成为官学的地位之后,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三纲五常也逐步确立了。
不过这时候的儒术,可不再是孔子时代的理论,而是经过演化的新儒术,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董仲舒,他提出了用思想的大一统来维持政治大一统,这一点非常符合汉武帝的口味。不过汉武帝是一个实用主义之上的人,所以在他的时代里,董仲舒一直只是诸多儒生的一员,并没有特别高的地位。
而新儒学的真正领军人物是谁呢?竟然是秦帝国时期的博士叔孙通和曾经做过狱吏的公孙弘。叔孙通很明确知道,在新的时代里,儒家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会非常有用,所以他一直在等到大汉朝的出现。
而公孙弘,他很清楚汉武帝是拿儒家作为统治工具罢了,所以每次提出建议的时候,都会用儒学经典作为包装,但是内容非常务实,这让他很快得到重用,甚至在后来他开创了先拜相再封侯的先例。
那么公孙弘和叔孙通为了夯实儒家的地位都做了什么呢?那就是垄断仕途。
在汉朝,国家通过提供官场的上升通道来吸引儒生,而儒家为了谋求生存空间,也会积极地向国家靠拢。最后国家有了一批职业官僚,而儒家也确定了自己的官学地位。
按理说,儒家既然确定了官学地位,那就没必要对汉武帝心存愤恨,但他们没想到,汉武帝只是将儒家当做了工具罢了。比如在用儒家官吏的同时,汉武帝也重用了很多酷吏,比如张汤,这导致在大汉朝做官,随时有可能会被刀笔吏所逼迫,这一点就是汉武帝沿袭秦制、使用法家的体现了。
所以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汉武帝不论是打击纵横家、还是用法家、甚至是将儒家确定为官学,其实本质都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罢了。法家和儒家在现实中存在着某种互相制约的关系,甚至可以直接威胁到成为官员的儒家子弟的生命,因此儒家自然对汉武帝没啥好印象了。
2 “重用酷吏,维护统治”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这就是汉武帝,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实用主义者。
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汉武帝在登基21年的时候,就开创了自己的帝国大业。而实际上,前半生他已经实现了他帝国的霸业。在这个时候,在其施政的纲要上,尊儒把当时大为购并秦政变成汉政,推恩把分权变成了集权,举贤明把贵族变成了官僚,同时讨伐其头号敌人匈奴,把当时的夷为平地变为了华夏。在那样的时代里面,独尊儒术,施行王霸之术,创造了中国文明的巅峰。
实际上,在20几岁的时候,汉武帝就具有了理论和制度的自觉。他知道,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巩固政权,特别是巩固皇权,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他不惜使用各种手段。所以,我们表面看起来的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尊的并不是儒术,而是尊他自己,比如他建太学、兴儒术、建人才,同时流行经济,把很多的产业变成了国有化,比如筑田、造铁、煮盐,这样的关注民生的三大核心项全部转为了国有企业。
西汉疆域版图
实际上,在汉武帝时期,所重用的并非只有儒生,还有刀笔吏,所谓刀笔吏指的是那些私法的官吏,其残酷我们可以讲一个人,叫于广,当年于广被汉武帝所猜忌的时候,他曾经说宁愿自杀,也不愿在刀笔吏下,因为太过残酷。所以,汉武帝时期,他并非尊崇纯粹的儒学,而是用各种各样的学说,不管法学,还是儒学,只要能够巩固皇权,他就用什么。比如在那个时候,为了更好地巩固皇权,他不拘一格,任用人才。
尽管汉武帝本人实际上并不尊儒,汉宣帝更明确主张王霸法用。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的统治往往是外儒而内法。
3 “征伐匈奴,开疆拓土”汉帝国版图疆域上的“大一统”
作为被后世公认为“一代雄主”的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几乎是穷毕生之力在攻伐匈奴,解决北方的边境问题,这位精明强干的帝王为什么犯了“中二病”一样跟匈奴过不去呢?
积怨已久
匈奴跟华夏冲突由来已久,战国时秦国、赵国、燕国为防止匈奴入侵修筑长城,赵武灵王因为匈奴军队强悍的战力而要“胡服骑射”,学习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安排蒙恬率精锐部队镇守北边,没有让蒙恬参与征伐六国。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困在一个叫白登的地方,给单于老婆送金银珠宝吹枕边风让放自己一马,刘邦死后匈奴单于调戏吕后“你也是单身,我也是单身,不如你嫁过来”,这口气吕后和汉朝的文武大臣忍了下来,汉文帝(刘彻的爷爷)和汉景帝(刘彻的父亲)时期也只能送宗室公主过去和亲,到刘彻这儿已经是忍了60年的屈辱,对匈奴可谓有深仇大恨。
猜疑链的作用
猜疑链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文明不能判断另一个文明是否会对本文明发起攻击。边患对于古代的封建王朝来说是心腹之患,如果不乘自己强大的时候打击对方,将来王朝弱势时会有倾覆之危。在后世的例子中,在金比较弱的时候辽有机会消灭金,辽没有去做,结果金灭辽,金有机会打击蒙古,金没有去做,结果蒙古灭金和南宋。明代表面亡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实则亡于东北部的后金(即后来的清)。汉武当然无法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但一个强大的对手的存在对自己及子孙政权的威胁是可以感知到的。
匈奴之患,像悬在头顶上的剑一样,让汉朝的君臣寝食难安,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给你来个烧杀抢劫。因此,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未免将来自己势弱被匈奴欺负,不如趁自己兵强马壮将匈奴击垮。
太子刘据是汉武帝刘彻最钟爱的儿子,刘据是刘彻和卫子夫的孩子,性格比较温和仁厚,常常劝谏父亲不要连年征伐。汉武帝说“我如果不为汉家订立制度,后代将没有东西可以依鉴。这些武力上的事情我帮你做了,你就可以做一个太平天子。”可见,为子孙后代计,刘彻也必须打击匈奴。
西汉征伐匈奴路线图
卫青和霍去病
汉朝的骑兵采取深入敌境,出奇制胜,远程奔袭,迂回包围的闪电战。卫青为此种战法的开创者,霍去病将之发扬光大。在卫青被授予“大将军”,统帅全部军队后,闪电战的任务就交给霍去病来完成了。
征伐匈奴的战场战术层面是由卫青和霍去病负责执行的,其中卫青是真正的全军统帅,运筹帷幄,霍去病是先锋将领,冲锋陷阵。
“卫霍组合”中卫青所率领的军队包括步兵、骑兵等各个兵种,讲究整体推进、协调作战,这种作战方法的好处是稳扎稳打,能让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其次能牵制敌人,不足在于机动性不强。
霍去病在汉军中是骑兵统帅,他所率领的骑兵速度快,机动性强,对匈奴人有极强的针对性,可以主动寻找敌人进行作战,同时这种作战方法是无后方作战,给养必须得靠自己在战斗中劫掠补充。
卫青重视实际效果,打击敌人的经济基础,霍去病简单粗暴,战场收割机一样的存在。
战争双方拼物质基础,汉的物质基础是粮食,战马,钱等。匈奴的物质基础是牛马羊,水草丰美的草原。牛马羊,水草丰美的草原,同时也是匈奴人的生存基础。
基于此,卫青打仗,并不重在杀人多少,而是重在实现战略目标,重在给敌人经济以重大打击,并重在获取敌人物资,以战养战,使敌人失去生存的基础。从而打败敌人。
这一特点从河南战役卫青战楼帆王,白羊王,杀5000余人,获牛马羊百万头,收河南地可看出。漠南战役,更说明了这点,卫青战右贤王,俘男女15000人,获牛马羊千百万头,完全击垮了右贤王。这两次战役虽然杀人不多,但却从生存基础上完全摧毁了楼帆王,白羊王,右贤王所部。占领了匈奴的水草肥美之地。对匈奴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使该三部只剩下等待饿死的人,只能各奔东西,自找生路。以后数十年不见楼帆王,白羊王,右贤王所部,对汉朝侵略。
卫青的这种战略思想,还可从卫青采取的春天烧匈奴草原,饿死匈奴牛马羊的战术中看出来。该战术也为后人所称道。
霍去病的作战风格很简单,就是杀敌,这从数据统计可以反映出来,卫青七击匈奴,杀匈奴五万多人,霍去病六击匈奴(其中两次随卫青出征,自己为将四次)杀匈奴11万人。太过锋利则易折断,霍去病24岁时就病死了,即使这样霍去病也被称作千古名将,可谓功名之盛。
对后世的影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汉武帝时期并没有彻底消灭匈奴,但仍然极大地打击了匈奴的实力,威震西域。西域各国仰慕汉朝的威仪和文明,纷纷同汉朝做生意,建立了一条“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汉武帝征匈奴为华夏民族塑造了强劲的风骨,整个华夏民族此后虽多次沉浮,但始终没有被彻底击倒,一代又一代的强人们出来力挽狂澜,救民族于危亡。
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取得了成就,但这是前后几代积蓄的结果,秦始皇统一中国也是依靠前后几代努力,史家称汉武帝很像秦始皇是非常有道理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汉武帝:“在征用民力,发动战争方面与秦始皇没有什么不同,秦之所以速亡,汉之所以久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尊重儒家,知道用人,能虚心接受忠直的言论,憎恶被人欺骗,喜好贤士,赏罚分明。到晚年能改正自己的过错,能把江山社稷托付给霍光这样适合的人,因此有败亡的征兆而没有实际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