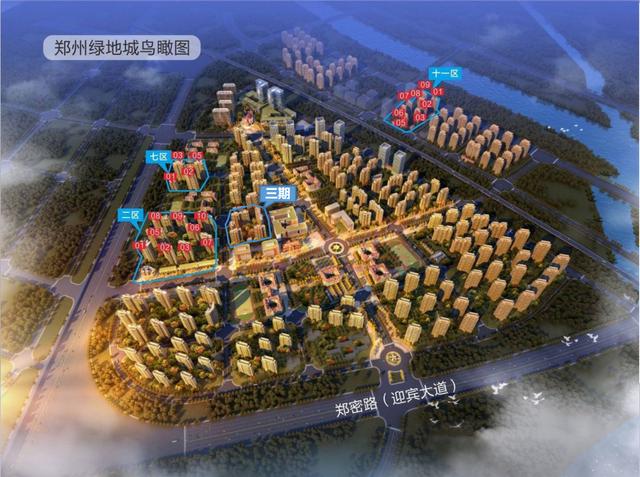△ 浦泽直树
浦泽直树自述:
我不妨先举个例子吧。
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有人犯了桩滔天大罪;黄金时段的新闻栏目必然会趁势借其大作文章,那架势就像是恨不得把你脑壳剖开,然后把「人性沦丧突破历史新低」之类的观点硬塞进去似的。
然而事实是饱受舆论摧残的观众们久而久之,大多也就潜移默化地相信了这些。

△《20 世纪少年》开篇
然而这样的结论真的可信吗?
从时代大局上看,在摇身一变成为经济强国以前,日本远比你我所设想的更加动荡不安:
大型罪案层出不穷,其程度之重甚至会令人怀疑社会。
而正因如此,我认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去看待事情的本质显得尤为重要。在『20 世纪少年』中,你可以感受到我对于那些早已化作陈辞滥调的旧日美梦的恼怒与愤慨——就像是咆哮着:
「为什么你非要把时钟往回拨呢?行行好,放过我吧!」

△《20 世纪少年》
赌上你们吃奶的劲儿——去拼搏努力吧!
只是不停地复制我们早已玩透了的那些过了保质期的旧货的话,你们是永远都无法夺取我们的皇冠的!
我无比确信的一点是,我们这代人举肩并进了半个世纪,如今俨然是站在了年轻一辈的上头;而我更为确信的是——尽管这完全是我的一己之见——自从进入 90 年代之后,文化变革的气息便几乎是彻底地销声匿迹。

△《20 世纪少年》
可要是知道,在我所成长的 60 年代完全是迥然不同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象征着变化与革命。
我是说,那可是 Beatles 每年至少发行两张新专辑的年头啊!
人们看去年的新闻,就像是看到了史前恐龙般惊愕。与当时那股革新万变的思潮相较比,今日发生的种种无一不是空洞乏味的旧酒装新瓶。

△《20 世纪少年》
因此我发自内心地,对拼命追赶着我们背影的年轻一代,感到无限的同情与怅惘。
——然而,我的父母那辈却并未能取得多大的成功,那是因为他们必须从二战的断壁残垣中白手起家、重建一切。
与我们相反,时代并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的馈赠。

△《20 世纪少年》
这更显得我,或是说我所在的那代人可谓是天时地利皆备的超级幸运儿。
战后文化的幼苗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抽枝、茁壮,然后这颗大树在世纪末的狂风骤浪中,连同碎裂的泡沫被一起砍倒。
我们就在那里,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而这是生于其他任何年代的小伙子们都无法去触碰和理解的独特感知。所以啊,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代人真是远远地凌驾其上了——这甚至令我感到有种莫名的负罪感(笑)。

△《20 世纪少年》
即便如此,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早出生那么几年。
要知道,验证你是否属于这个「无与伦比的一代」一员的决定性因素,那便是你对于东京奥运(1964)与大阪万博(1970)保留着怎样的记忆。在东奥举办的时候,我只有四岁。
……还真是年轻得过分啊(笑)。如果当时我能年长那么三、四岁——也就是意味着如果我是在昭和 30 年(1955)出生的话,那么一切就截然不同、天翻地覆了啊!

△《20 世纪少年》
桑田佳祐(流行音乐之神)、江川卓(日本职棒天才)、千代の富士貢(相扑力士大将)、明石家秋刀鱼(搞笑艺人兼演员)——他们所在的这耀眼的一代造就了现代的日本文化体系,至今仍被后世传诵。
试想一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1955、昭和 30 年:如果我生得太早,那么我将会身处繁杂沉重的战后废墟之中,无法自拔;如果我生得太晚,那么我将被「昭和 30 代」的身影压得难以喘气,然后变得自私、中二、愤世嫉俗。

△《20 世纪少年》
在我心目中,唯独「昭和 30 代」才是真正经历了日本社会文化的进步与循环的见证者;啊啊、我想我大概是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生日啦(笑)。(浦泽生于 1960 年 1 月 2 日。)
那么,作为与战后文化一同发芽成长的「无与伦比的一代」的一员(尽管年龄上稍微有点偏差),我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这样一句话:

△《20 世纪少年》
赌上你们吃奶的劲儿——去拼搏努力吧!只是不停地复制我们早已玩透了的那些过了保质期的旧货的话,你们是永远都无法夺取我们的皇冠的!
你们要创造真正属于你们的新文化,创造出独立于战后文化的、焕然一新的东西。
你要让我们恼怒、让我们气愤,要迫使我们嘶吼「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都是些什么混账玩意啊!」之类的感慨。

△大阪万国博览会,摄于1970。
因为今时今日,我对你们的所思所想早已了如指掌;你们挂在嘴边的那些段子与笑点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货——因为那可是我们写出来的啊!
我希望你们能继续前进、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就像当年 Beatles 的狂潮占据了每一块荧幕、或是猫王 Elvis Presley 扭起他那风靡全球的美臀一般——年轻人哟,如今是你们的时刻,去撼天动地、呼风唤雨了!

△《20 世纪少年》
冈本太郎所设计的「太阳之塔」,至今仍作为 70 万博的象征屹立于大阪市内;它与所有其他的那些世界级的天才建筑师与设计师——包括……等的作品一起,在名为万博园的角斗场中争奇斗艳。
在它短短半年的服务效期内,大阪万博的游客记录突破历史新高达到了 64,220,200 名。每日入园的人山人海几乎拥挤得令人窒息。
在『20 世纪少年』中,1970 年的这场大阪万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作者的浦泽而言,它又象征着怎样的记忆与意义呢?

对我们「无与伦比的一代」来说,真正的二十一世纪,是从 1970 年开始的。
当万博开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还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就像『20 世纪少年』中的贤知一样,我最终也没能去成。
用我家人的话来解释,「去一趟那么贵,而且又是人山人海」!取而代之地,我被拉去了勝浦浜海岸(译者注:福冈县福津市的海滩度假区)。

当我到那的时候我迈着大步抗议,「这里可不是万博啊啊啊啊啊」!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大阪万博,我哪里也不想去。
直到今天我回想当时的自己,也必定是会抱着同样的想法吧。那就像是某种天经地义、不去不可的地方,然而我却去不了。是啊,如今想起,我也依然会黯然流泪,愤愤不平(笑)。
诚然,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非去不可的原因,我想自己一时半会也很难归纳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20 世纪少年》
在漫画中,我用了不少分镜去描写年幼的主角们热议着他们该怎么去看那非看不可的月面陨石(美国馆登月计划的遗留物),或是其他展馆的随便什么有趣而拉风的东西。当时的我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只是单纯地把想看的东西列了一大长串便作罢。
然而那并不是我想要去看的原因——确切地表达出对于万博的那种热诚渴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20 世纪少年』,也无非是我的一次尝试罢了。

△《20 世纪少年》
在『20 世纪少年』电影版的制作期间,我所负责的正是这种「热诚」的自然过渡。
这部漫画中既融入了代表我个人体验的成长剪影,也彰显着代表公众与时代的精神思潮——那么能将这种内在气质嫁接到电影上的人选,自然是除我无他。
漫画与电影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分隔线,然而我想我已将你读完漫画与看完电影的两种心理感受,尽可能地做到协调与一致。
对我来说,所有发生在 1970 年万博之前的事件都被归结为「过去」,而所有自 1971 年以后的才是「现在」的区间。

△《20 世纪少年》
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划分:
1970 年之前的世界是黑白的;而从那往后,则变成了全彩。
这好比说我在报纸上看电影版块的介绍。如果片名后面标注的是「Made in 1973」,那便表示它是现代的;
反之,若是它写着「Made in 1966」,我可要认为这是史前古董了(笑)。于我而言,这一线之差的意义,可谓是隔了千里之远。

△《20 世纪少年》
而那年恰巧相撞上了的则是另一项转折的时间:
我们眼中「未来」的基调,由银色变成了白色。不必说在每一个少年的心里,「未来」便是那宇宙火箭飞船的代名词,而火箭飞船向来都是银光闪闪的。
然而在 1968 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带着他的『2001 太空漫游』横空出世,在一夜之间把我们的银色梦想涂成了白色。
相传库布里克本已把所有素材布景都做好了银色,然而在拍片途中他去了 NASA 做取材用的访问旅行——可想而知,目之所见,一片纯白。和我们天才导演的初衷真是相差甚远呀(笑)。

△《20 世纪少年》
于是当他重返布景场地后,所有道具都被改成了白色。这便是我们那代人见证未来从银变白的过程。时至如今,每当我看到银色的冰箱,也还是像看到 1970 年前的那些岁月向我击鼓鸣冤一样。
因此时代需要一束屹立不朽的腰封,在「过去」与「现在」分隔的 1970 年,将两者完美地衔接在一起——我认为那便是大阪万博。

△《20 世纪少年》
『20 世纪少年』已被翻译成多门外语、在不少国家与地区销售刊行,并在 2004 年法国的安格雷姆国际漫画节(欧洲最大级的漫画盛事)上荣获最优秀长篇大赏。
巴黎与巴塞罗那都曾主办过多次万博,不是么?对于法国人民来说,『20 世纪少年』中贤知与大阪的那种近在咫尺的激动与兴奋,他们感同身受。

△《20 世纪少年》
每每追溯往事,回想起那种包裹着整个日本的 1970 年时的独特气息,回想起那种凝聚着迎接未来的希冀的激动与渴望,仿佛在强烈地呼喊着我们需要大步前进、迈入 2000。
对我们「无与伦比的一代」来说,真正的二十一世纪是从 1970 年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