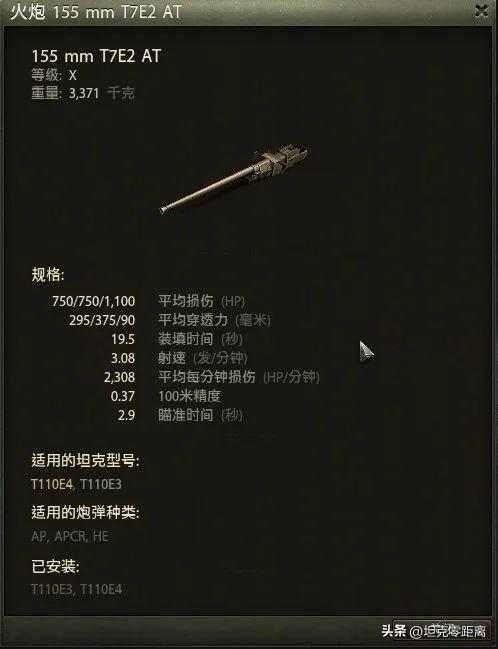有人问我,自留地背后的靠山,是不是人民公社?我回答说:既是,也不是。
于是,我把我小时候就知道的事情告诉了他。因为时间久了,记的不是很清楚。我的回答好像是,因为它是农村合作化的产物,虽在人民公社时分下户,但在人民公社改名换姓以后,它依然由农民们耕种着……
这是什么话,既啊又的,没个准确。他显然是对我的回答不甚满意。
不过,他离开的时候,我也就醒来了。
这梦中的情景,我依然十分清晰。于是,我找来相关资料对照,生怕因自己的解释不得体,而让别人蒙受了损失,就与问路的人、把相反的信息输入了人家的大脑、导致走弯路的后果一样。
好在我的回答与现存的资料还比较吻合。
醒来以后,感觉离天亮还早,再睡去已不可能了,我也就显得无所事事,但依然是躺在那里、还一时没有要起床的意思。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居然了解我过去那么多的底细,不然怎么会把如此专业的问题拿来让我回答呢?
……管他呢,算他运气好,找对人了。
我就这样边想着问题,边进入到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 ※
在川北某个小县城的偏远农村,我的童年在那儿落脚。“人民公社” 赶巧来到了我的童年世界。
我们那儿离公社尚有七八公里的山路。既是山路,路面就崎岖难行,由于不通公路,那时候的公路连个基本的雏形也没有,每次都要走上好几个小时。
这路程与全公社十二个大队相比,算是最远的其中之一了。我记得最清楚,与公社相连的是家家户户梁旦上挂着的那个纸喇叭。上面有什么最高指示,小喇叭就在开机前重点提醒道,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注意了……于是,大人们便会立即侧耳细听。
至于分到一家一户去自由耕种的自留地,是不是靠一个小小的纸喇叭就能把这事给办了,我说不清楚。但从那时候严肃认真的办事风格来看,好像又不太像。
也难说是公社书记召集各大队支部书记开会,就把上级指示给传达下去了,最后由各大队支部书记召集各生产队的队长具体抓落实,谁说不是呢?
反正从我记事起,我们家的自留地就像生产队里其他人家的自留地一样,都放在房前屋后的。只不过,家家自留地里种的东西大同小异,基本没什么区别。
由于前后周围都是四合院的缘故,我们家没有多少劳动力,直接导致的后果仿佛是吃“下喉食”般被人冷对。我们的自留地被划在了离老屋还有一段距离的山岩下。而其他人家的自留地就在他们房子周围,并且土地肥沃,还没什么遮挡物。
大人们忙外,我们几个娃娃只要一放学回来,就争分夺秒积肥往牛圏里倒,这是母亲的分工。父亲不是农业户口,他自然没时间管家。
那块土壤贫瘠的自留地,在我们牛圈农家肥的催肥下,基本还是达到了种什么都有收入的效果。只是四周树木对菜园子里农作物的影响没办法解决。
※ ※
我从茅坑里挑一担粪到自留地,路上要停留两三次,从牛圈背一背牛粪,也要歇息两三次……这是我最初的情况。那时,两只粪桶与我,我们“三爷子”一样高,从茅坑里吃力地把粪水舀起来的时候,还是满满一担,一路簸簸浪浪之后,到自留地时就只有半桶了。背的牛粪哪怕只有半背篼,也觉得相当沉重……都是路程远了的缘故。
那时,好像我们一有时间,从早到晚就到自留地里薅草施肥浇水。
地里那些家伙们,也还算争气,长出的苗子壮硕得很,结出的果实,满足了我们“主粮不够,副食来凑” 的希冀。
生产队的好田好地,种出的包谷麦子稻谷等主粮,常常让肚子还闹着饥荒,要不是我们平时勤快些,恐怕自留地里也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所以,母亲才让我们在自留地里多下些功夫。
现在,我回味母亲当年那句安慰我们的话: “只要努力,它就不会对不起我们的”,觉得它很有几分道理。
我们的邻居,他们当初尽管靠“强者”的力量,分到了尚好的自留地,却在吃光了远比我们分得多的主粮后,光秃秃的自留地里到底还是常常让他们饥肠辘辘。
每当这时,我就有了一种要报复的快感,而母亲却要把我们辛苦种出来的白菜、莴笋、冬瓜、南瓜之类的疏菜瓜果,拿给邻居们去应急,这就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的了。
母亲那时候的种种善举,表面上看是换来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却让我后来遭受了一顿黄荊条的痛打。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地存着。在心里增加了对他们深刻的记恨。
“桐麻树的枝子老歇你们的菜园子,我看是可以砍掉的,只是要选在没人的时候下手……”
我们的那些蔬菜瓜果送出后,母亲很快就收到了别人的这些“好心提醒”。想想也对,只砍些可恶的枝桠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她便示意我把遮地最厉害的那几梢给拿掉,我却无所顾忌地顺势就发泄了平时积压在心底的怨气。
放倒的那棵桐麻树像一座山,气息将尽时还打倒了我们地里的一大片长势喜人的青苗儿。
我胆怯地慌了神。心想这下肯定必有打挨无疑了。后来事实也是如此的。
尽管心里有了小小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这以我个人挨打的方式,居然代替了生产队对我们家庭“应有” 的处罚。
几天以后生产队像扯什么疯似的,居然开天辟地检查起自留地周边的树木情况来。
每天忙于挣工分的母亲,自从把别人的好心建议转告给了我以后,直到检查组拿出证据来,她也不知道我闯祸的事,而且还是那么严重。
她即刻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教训了我,几根黄荊条下去后,我的身上肿起了很多被打的 “轮”。
也许是母亲的举动,惊动了在场准备要追我们家责任的人,也许有心追责的人,想想到底受损的只是一棵桐麻树,犯不着大惊小怪的,后来我砍倒桐麻树的 “罪责”,才没在生产队里小题大作。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有些笑意的给我说,桐麻树是经济作物,你晓不晓得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去年,杨查芳才剁了她园子边上的一梢桐麻树枝,就为此弄来一场批斗……
她是地主,我能和她比?我想如此说出,却没有张口。怕影响了她难得的兴奋。
※ ※
自留地里要种什么,队上是有规定的。为此,前任老队长,还常常带人去一家一户抓落实。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句家喻户晓的口号,谁不记得谁就要倒霉。队长晚上开社员大会的时候,还专门抽人回答,回答不上来的直接扣粮。要是检查发现哪家自留地里种了粮食,对不起,要当场铲掉,平时生产队里是随时开通了举报热线的。
如果你狡辩说你不知道,那他肯定要问你家广播是干什么吃的,你难道没听广播吗?一句话就把你问得哑口无声了。
实际上,自留地里种出的东西,只有生产队的好田好地里没种的有,你才能去种。说白了,自留地里只能种黄瓜茄子四季豆之类的蔬菜。像冬瓜、南瓜之类的瓜果也可以种,就是不能把自家的苗伸到别人家,尤其是伸到生产队的公共地界上去的。否则,将按侵占公家财产论处。
应该说,我们家是生产队里最胆小的其中之一户了。为了不违规,母亲还专门拿上纸笔,把自留地里能种什么、不能都什么,都记录下来了。每年都按纸上的记录下种。
按母亲的说法不要去惹祸,所以那几年,我们家的自留地种的全是“听话”的苗。
老政策没维持几年,新的政策就来了。新政策来的时候,纸喇叭也不再宣传最高指示了。我们家梁旦上的那个纸喇叭,好像就是在那时候坏掉的。
后来自留地自由了的消息,还是在生产队晚上的社员大会上公布的,队长像个指挥官,只是他没有喊出突围吧,冲啊……之类的话。
他说,现在自留地放开了,你们想种什么都可以种,只是不能种大烟……
受这句话的鼓舞,生产队好多人家的自留地,都种上了包谷和麦子,但主粮之一的稻谷是没法种的,因为“地”与“田”是不能同日而语。不存水的自留地,显然不具备收水栽秧的条件。
我们家的自留地,在那次社员大会之后,第一年先 “观望”,第二年才种上了麦子与包谷。收获的时候,麦子只有地板凳那么高,包谷叶在骄阳的午后卷了筒,包谷并不满仓。之所以要观望,大概是经过一些事情后,母亲那胆小的性格还没有改变多少吧!
但那第一年我们还种的蔬菜瓜果,像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一样,除了自给自足外,多余的还拿去卖了钱,以此方式,换回了暂时还不能种的包谷麦子和稻谷。
那些继续歇着我们自留地的桐麻树呢,桐籽没人收购了,连炸油坊也撤了,我们便把桐麻树连根拔起了。
※ ※
别说小小的自留地能神奇个啥,就是那些好田好地也神奇不起来了?
去年回到乡下,面对眼前辽阔的荒芜,它们长着大片的野草,被萧瑟的寒风吹拂。我在那曾经丰沃的土地上站立。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心中的感慨。
是我们今天不再需要自留地了吗?我在竭力地区分着“自留地”与“集体地”的界限,没想到它们已经混为一谈会是这么快啊!
你知道自留地曾经都种过什么吗?我问身后的妻子。
应该什么都种吧!她含糊而笼统地回答。
你知道什么叫自留地吗?我转向走在前面的儿子问。
他摇摇头。露出了一脸的茫然。
走了几步,儿子又反问我,老爸,自留地是干什么用的?
自留地的事情还有多少人知道呢?再过几年,恐怕连自留地这个词语都要消失了吧?我陷入了沉思之中。
回过头来的儿子,又重复问了他刚才的问题。
自留地是用来糊口的。我这才回答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