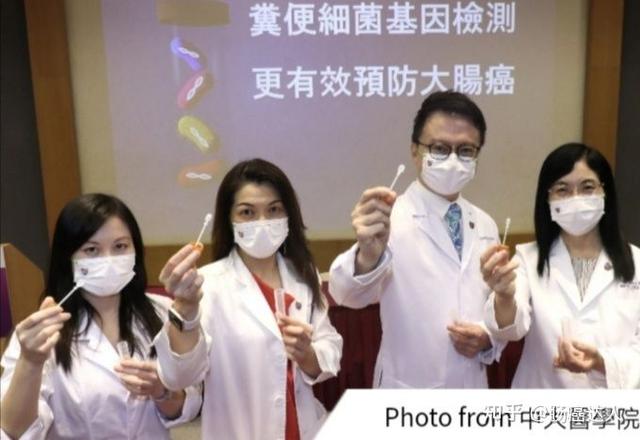孔德罡
随着《沙丘》上映,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再度成为影迷关注的名字:有人已将他追捧为好莱坞新一代“大师”,甚至“封神”。然而这位“大师”实际上颇为独特——一个矛盾的说法是,维伦纽瓦的独特在于,相较其他“神”级导演,他相对“平庸”。

丹尼斯·维伦纽瓦
他没有什么一鸣惊人的“神作”,他的业界地位是依靠他从加拿大独立电影界,到好莱坞独立制片界,再到好莱坞大厂的一路爬升,稳扎稳打推出“佳作”挣来的,事业虽说是稳步推进,直至《银翼杀手2049》(以下简称《2049》)和《沙丘》的巅峰,却也不见“天才式”厚积薄发的绚烂;要谈论维伦纽瓦的个人影像风格,也要面对他从小成本新浪潮艺术片起步,到好莱坞中等投资警匪片再到大制作科幻电影的阶段性变化状态,想要抓住他终其生涯不变的私人特质是困难的——这本身就意味着其作者性的模糊。
更有趣的是,作为一个能够掌控2-3亿美元投资的顶级科幻制作的大牌导演,维伦纽瓦相较于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克里斯托弗·诺兰甚至扎克·施耐德,竟然至今都还是一个只有影迷津津乐道,大众浑然不知的小众导演,无论是《2049》还是《沙丘》的推广,都是依靠IP本身的影响力而非他个人;提起《焦土之城》《边境杀手》《降临》这些奥斯卡提名电影,甚至很难有人会记起它们是同一位导演的作品。更有甚者,维伦纽瓦在商业成绩上也是糟糕的,根据boxofficemojo数据,他至今还没有一部全球票房超过3亿美元的作品,大多数票房数字都是勉强持平成本线。

《沙丘》剧照。
我们需要谈论的是一个从《沙丘》上映后持续发酵的“维伦纽瓦现象”:他始终隐身于大众视野,但却时刻提醒着一些疑问:维伦纽瓦独特的影像风格是什么?他究竟如何成为如今好莱坞的顶级导演之一的?为何没有什么亮眼的商业成绩的他,能够步步爬升掌握更高的预算和更重大的项目?为什么《银翼杀手》《沙丘》这样的伟大IP都放心交给他,观众们也都觉得合情合理?在诸多“佳作”映照下,他有通往“杰作”的潜质吗?他到底缺乏什么呢?他会是这个时代的“大师级”导演吗?抑或是,他已经什么都不缺,新时代电影作者的“作者性”是在发展的,维伦纽瓦就是这个时代我们能够拥有的作者导演最好的样子?
没有难度的《沙丘》:除了视听影像的情动体验之外,我们还拥有什么?
在维伦纽瓦之前,拍摄《沙丘》并获得成功是一种近乎神话的奢望。因为把电影完整地拍摄出来就算了不起的成就了:1974年,智利魔幻现实主义邪典导演佐杜洛杜斯基费时两年要拍摄《沙丘》,一度传说萨尔瓦多·达利和奥森·威尔斯都要参演,然而计划胎死腹中;1984年,大师级导演大卫·林奇为《沙丘》推掉了《星球大战3》的导演机会,却因为丢失最终剪辑权,上映了他职业生涯最差,他本人都不愿回首的一部电影。面对这部弗兰克·赫伯特1965年开创的“太空歌剧”鼻祖,仿佛将其按照导演的预想成功拍摄出来并上映就是一个胜利。为什么会如此艰难?是什么让《沙丘》的电影改编“完成即成功”,到了令评论者失语的境地?
纵然丹尼斯·维伦纽瓦交出了一份精彩的答卷,2021版《沙丘》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太空歌剧科幻电影之一,其带来的超凡视听体验更是在近一两年无所匹敌——甚至上一部达到如此美学成就的作品正是维伦纽瓦自己的《2049》,但是相比于1974年和1984年,我们不应高估现在拍摄《沙丘》的创作和技术难度。实际上,相比于当年彼得·杰克逊一腔孤勇,在新西兰三部套拍另一本曾经被认为不可能被搬上荧幕的伟大幻想类作品《指环王》,投资商华纳兄弟对《沙丘》的拍摄计划早就充满了既定性和精确的计算,《沙丘》显然只是投资商日常的影片上映计划中普通的组成部分,他们按部就班地根据第一部的反响公布了2023年上映《沙丘2》,完全没有片子可能拍不出来,“背水一战”的孤注一掷,只有对票房是否能够达到启动续集的标准的理性判断。
在电影拍摄的技术领域,还原《沙丘》文本中的影像奇观的技术难度早已被攻克。对比1984年大卫·林奇版《沙丘》肥皂剧般的场景,夸张滑稽的人物造型与尚在初级的电脑特效,尤其是基本把影片搞成喜剧的“数码方块防护罩”,2021版《沙丘》固然天上地下,但其实也并未给予观众多少超越技术限制和人类想象边界的奇观:无论是恢弘壮阔的沙漠风光,巨大可怖张开尖牙大口的沙虫,还是见怪不怪的星际战争场面——至少在视觉还原上,《沙丘》的拍摄难度已经被怯魅。
那么现在《沙丘》的拍摄难度,只在于原著复杂详细的世界观构建,和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的情节而已。况且,这个问题用拍摄篇幅不受限制的电视剧就可以解决,投资商为了商业成绩要求拍摄电影,属于强行增添难度。而且,维伦纽瓦将电影情节停留在了原著第一本的中段位置,基本解决了“篇幅”的限制问题,他都没有做出什么颠覆性的删改,按部就班156分钟还算轻巧地就完成了电影作为序章的叙事任务——隔壁007的丹尼尔·克雷格谢幕篇《无暇赴死》都花了160分钟。

《沙丘》剧照。
如今拍摄《沙丘》可能并没有多么艰难,甚至在创作上《2049》也许更难些。一旦这个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被“怯魅”,原著集中体现在国内院线观众的评价中的缺陷就被暴露:原著作为一部1965年出版的“太空歌剧”,现在看来太“软”了,而且虽然是鼻祖,但也因为后来模仿者众多,观众已然见怪不怪。沙漠为主的星球?《星球大战》拍了好多次了;以星际航行为基础的跨星系封建大帝国?《星战前传》都拍了皇帝和议会;莎士比亚式的宫廷斗争,最终高尚者命运悲剧式地陨落?乔治·R·R·马丁甚至说,《冰与火之歌》第一部奈德·史塔克的陨落就是在致敬《沙丘》的厄崔迪家族;保罗·厄崔迪作为“救世主”的自我认知和重新发现之旅?有没有发现任何一部好莱坞英雄电影的背后,主角都带有耶稣和俄狄浦斯的隐喻?而无论电影还是原著都做了解释和设定补完,一万多年后人类的星际战争依然是街头棍棒茬架和马其顿长枪阵,还是很难让热爱“多铆蒸刚”、“多即是大,大就是好”的当代中国科幻影迷满意,再加上本身维伦纽瓦的动作戏就是短板,更让原著文本氛围中无限深沉的宿命之战显得轻描淡写;电影最终选择停留在原著一个不太起眼的位置,虽然“保罗第一次杀人并融入弗雷曼人”对角色个人成长是一个绝佳的标记点,但却还不够华彩到能作为一部史诗科幻的终章——维伦纽瓦善于起范儿但不善于结尾的缺陷再次暴露了。
拍摄技术上不再有难度,想象力和视觉奇观表现也只是“足量”,不曾突破想象达到超凡,原著更因为年代的久远,显得过时陈旧甚至带有后殖民主义偏见,那么除了赋予我们绝致的视听体验和一堆视觉符号学隐喻,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感官情绪和对史诗幻想的渴望之外,《沙丘》到底给了我们什么?这恐怕是电影评论者噤若寒蝉,不太会深入讨论的——他们只会说,维伦纽瓦居然把《沙丘》拍出来了而且质量尚可,这件事情就很伟大了:这就是现代神话学的运作行为,所有人只关心“拍没拍出来”这个能指的真实。
回顾维伦纽瓦的科幻三部曲:BDO与当代美术馆语汇
丹尼斯·维伦纽瓦的职业生涯并非是一个“天才”“大师”从天而降的传奇,相反他树立了一个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电影作者,如何稳步提升自我的“成功学”范本:在加拿大拍摄了多部带有新浪潮、戈达尔风格的以浪漫爱情喜剧为外壳的艺术片,最终以《焦土之城》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从而进入好莱坞;在好莱坞迅速转化为一个称职的独立电影导演,专注警匪题材,最终以《边境杀手》获得广泛声名;接拍中等投资的科幻电影《降临》获得成功,旋即掌握科幻电影领域最头部的投资和IP,拍摄了《2049》和《沙丘》,接下来他将以世人对他“维神”的期待,继续《沙丘》的续集拍摄,向一个“伟大”的科幻电影系列稳步迈进。
尽管从《边境杀手》开始,维伦纽瓦多变的影像风格就开始统一,但如今维伦纽瓦展现给观众的个人特质,还得是《降临》《2049》和《沙丘》,他个人的科幻三部曲所奠定的。作为导演,维伦纽瓦曾经热衷跳接、快剪、长镜头、运动手持等新浪潮特色,曾经迷恋多线和分章节叙事,喜爱多角度叙述造成叙事迷障,曾经热爱用流行歌曲做配乐,让歌词与故事情节形成互文关系,这些都是曾经的维伦纽瓦,也已经不再是现在的维伦纽瓦。从《边境杀手》开始,维伦纽瓦的影像风格开始拥有强烈的可辨识度,大致可以概括为:
对BDO(Big Dumb Object,巨大沉默物体)和宏大静态全景的影像崇拜;极尽雍容、缓慢稳重的镜头语言和与之相配的舒缓、注重细节和潜台词的叙事节奏;干净、凛冽、空旷、纯色、极简主义,一切场景都是当代美术馆的场景刻画;“多就是多”,运用覆盖性质的音场垄断观众听觉,操控观众情绪的“满溢”式配乐;最终,以宏观的视听语言来叙述人性内部细腻微小的内容,将私人化的微观体验提升到宗教和人类精神的宏观平面之上。

《降临》剧照。
维伦纽瓦热衷于将一切电影中的“机械造物”都转化为BDO,“巨物崇拜”症已是他的个人名片。《降临》中12艘降临地球的外星飞船不仅初见就给予观众强烈的视觉刺激,更跟随着主角们与其中一艘中的外星人的交流变得具象:观众跟随镜头体验到要进入飞船所要付出的距离和时间,以人的感官亲身丈量了这“崇高”的巨大物体。《2049》中,镜头几乎无时无刻地在提醒瑞恩·高斯林细小微末的身影,要么出现于高度空旷的纯色场景中,要么是在恢弘巨大的巨物面前,这个后赛博朋克废土世界的“游荡者”仿佛这无情世界中无人在意的蝼蚁,随时都会被扭曲撕裂;《沙丘》里无论是哪个家族的星球,宫殿都超出实际使用范围的庞大,雷托·厄崔迪最后死在了宛若“中心筒”广场般的挑高穹顶式美术馆空间中,宫廷的走道都宛若美术馆长廊般没有道理的宽阔,保罗·厄崔迪站在卡拉丹星球绝高的山顶,也无法丈量以极其缓慢的速度从天而降的“巨蛋”飞船,而他与母亲的身影在沙虫和沙漠面前相形见绌甚至都不再让人惊奇了。这一切的“巨物”和“美术馆白空间”同时也是极简主义的,毫无复杂的花纹设计,杜绝了一切细微的雕饰和附加,只以纯粹的“巨大”和“空旷”,配合始终不息的,垄断听觉,隔断理性思维的噪音式配乐,来映照静态全景中只占一丁点面积的人物形象内心无比巨大的枯寂而荒凉——
“小小的人产生了巨大的阴影”。
其实一言以蔽之,维伦纽瓦的科幻电影语汇,就是当代艺术的语汇,是可以无缝对接当代美术馆装置作品的现代语汇——他的科幻电影与其说是电影,更是装置影像;他相较于一个电影导演,更是以一个当代装置艺术家:他的科幻电影美学,始终集中于作为微小个体的人,与作为宏大完满的外部宇宙之间的本质冲突,而这正也是从包豪斯设计学校起步的20世纪当代艺术背后的一条思想进路:对“崇高”人造性的实现。“崇高”固然将吞没人类作为微末尘埃的感知能力,但如若这种“崇高”同时也来自人造,那么本质上这意味着一种尼采式“超人”的超越可能。总有人诟病维伦纽瓦的叙事“格局不大”,总集中在一两个角色的内心世界里,人物的“小格局”与环境的“大格局”不相符——可这种“不相符”,正是维伦纽瓦个人特质的核心:他始终在讲述个体的故事,把个体“抛入”到超凡巨大的世界里,以小感知大,然后小就等于大。在《降临》里,这意味着人类在挑战超出自身理解维度的崇高;在《2049》里,意味着人类面对自我设下的宏伟屏障无力挣脱;而在《沙丘》里较为乐观和简单一些,是对人类未来审美“后人类化”的一种可视化想象,但却也与《沙丘》情节中人类对残酷的自然和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斗争相共鸣。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解释尽管维伦纽瓦的三部科幻电影都不是票房出色的大众喜爱型,勉强保本的成绩看起来并不亮眼,但却能收获压倒式的好评,并且推动其拿到投资更高,美学诉求更加鲜明的项目,每一部作品都能实现自我跨越的原因:维伦纽瓦的科幻电影语汇是来自于当代艺术的,是纯粹当代的,本质上走在对未来人类进行“异化”或是“进化”的临界点,他就站在艺术家们最热衷的边界之上——它意味着一种将最微观的个体存在,提升到最宏观的“超人”形式的期待与可能性,而这也是被观众解读为、甚至在《沙丘》中被具象化的“宗教”色彩:对纯粹的“神性”对“人性”进行哺育、达成提升的呈现。
正因其处于边界,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但同样,只要理解,没有人不会迷恋这种未来。可以说,是艺术家和艺术批评的共同体支撑着维伦纽瓦,让钻进钱眼中的资本家暂时接受对维伦纽瓦投资不能翻倍只能保本的现实——这近乎是艺术能够做到的,最极致的反资本主义斗争。
《银翼杀手2049》:维伦纽瓦与21世纪的“作者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没法把话题局限于《沙丘》——《沙丘》本质上是维伦纽瓦成熟的科幻影像风格的增殖生产,至少在对原著情节的表现尚未触及到核心冲突之前,《沙丘》没有太多诉诸于主题探索的努力。不过,国内观众对《沙丘》没有拓展科幻的边界的批判,虽然建立在对科幻作品必须要求“硬”的思想钢印中,但却也客观说明了一个事实:维伦纽瓦的三部科幻作品,尤其是《银翼杀手2049》,作为他三部科幻电影中最具作者特质的一部,体现出当代人类在思想上的无法前行的“绝境”:这个绝境本身意味着我们的“科学幻想”已然无法再向前一步。将《2049》追捧为伟大的科幻电影其实有失偏颇:因为《2049》令人窒息的创作成就,并不以科学幻想为主体。相较于前作在1982年被后知后觉奉为经典是因为其开创了前所未有超越时代的科幻命题,《2049》无关未来,而只在于总结;它不是一本天启书,它是一部对当代世界的互文百科全书。
《2049》依附于1982年建立的世界观中,维伦纽瓦无力对其拓展甚至颠覆。时过境迁数十年后,和《沙丘》遭遇到的问题一样,无数的“科幻高概念”已经耳熟能详,被很多其他的科幻文本所彻底探索过,不再有所谓的处女地。因此,维伦纽瓦令一些科幻爱好者不可能不失望的是,《2049》的三个半小时内都笼罩着无所改变的僵化氛围,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早已被定型、规训、分化,只剩下技术的添砖加瓦与精益求精——这就是《2049》这部电影本身的地位隐喻:它不是一部伟大的、划时代的科幻电影,因为它完成的只是对现有科幻世界的一种再现,对现象的某种重组与再生,对已有命题的再诠释,而在新的空间与概念世界里乏善可陈。

《银翼杀手2049》剧照。
这仅仅是维伦纽瓦的问题吗?并不是。是我们人类如今走到了想象力的临界点,走到了科学幻想的“绝境”。曾经的科学幻想一个个变为技术上可实现的现实,而新的幻想却始终没有来到。作为创作者对此的痛感应该更加深邃,因为相较于《降临》还充满着葱郁的人类超脱既定思想维度的勃勃生机,《2049》与《沙丘》更加“末世废土”。这两种对未来的幻想迥然有别,前者有明确的理想、价值,有鲜明的立场与情绪的直接宣泄,哪怕是极致的“反乌托邦”,也有明确的“美好”作为寄托;而后者则立足虚无,质疑存在,没有准确的价值取向,只有双重思想、自我矛盾的情绪纠结。
维伦纽瓦的2049废土世界,甚至又不存在直观的生存危机问题,这就抽离了情节链能够依附的最后一块主心骨。高斯林饰演的K,名字取材于找不到城堡的卡夫卡,而他也完全是一个流浪者的诗意性功能主角:这样的主角是多余人,是观察家,是浪荡子,从根本上说,他没有本体存在的根本目的。他在2049的废土世界里意外地遇见了新奇,这之后才获得行动的意义。这是一个来自《奥德赛》的古老的文学范式在科幻电影中的复生,这个复制人警察K,简直就是一个苍茫大地里孤独前进,没有家可回的,多愁善感的诗人:《乡愁》里的音乐史学家,《尤里西斯的凝视》里的东欧导演,总而言之,一个存在却又缺席,试图通过经历和思索寻找自我价值的知识分子,一个没有家的乡愁者。
这正是维伦纽瓦惯用的所谓的“格局缩小”,因为这个广袤的2049废土,任何人都是自以为特别却又普通的。完成存在主义式的心理建构,成为K角色本身的价值,华莱士公司、复制人起义军这些宏大的政治存在,都不过只是一个飘渺的背景:对于一个漫游各地的旅行者来说,他的感受与自我的追寻之旅,无关于历史的进程与车轮,宛若维罗妮卡回家路上,看着卡车运送的推倒的塑像经过,只是经过的一个镜头流逝。影片的最后,K最后只是进行了一次水中搏杀,杀死了他的一名普通的敌人,协助了一次父女团圆,整部电影因此看似没头没尾,那些宏大叙事都是不完整的:他本来就是一个意外有着敏感心灵的普通存在,对于其他的,他不知道,无能为力而孤独莫名。

《银翼杀手2049》剧照。
黄金时代科幻世界里的人性往往是极为古典传统的。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加强科技发展对人性的改变和冲击的力度,而另一方面,也是科幻文本的创作者们本身对人性还抱有的,启蒙时代传承下来的信心与高昂。而问题在于,哪怕不用科幻文本,不用AI、VR、星际旅行、时空扭曲这些高概念去拷问人性,人性本身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演化了:汉斯·季默在《2049》和《沙丘》中尖锐而刺耳的单音,制造的就是当代人和当代艺术的精神分裂症——在维伦纽瓦电影中的小大对比中,是对纯粹的极致追求所造成的崇高美学,与解放人性、探索人性异化的主题所必然导致的原始生命力之间难以分离的相生与互相取消。
所以,维伦纽瓦的“格局小”,他的“不表达”,包括他的“平庸”,不像一个天才,难道不就是对当代世界存在着的我们最明确的注解吗?一股存在着无数悲哀,却又根本无法阻挡的洪流。人类为了更加自由而寻找规训,然后在痛陈规训的不自由。这是某种“后-人性”,它存在着法西斯式的极端渴望,但同时又是真诚的。在维伦纽瓦的科幻世界里,所有存在的角色无论是真人、还是复制人、还是外星人,在面对远超出自我存在维度的巨物和“崇高”时,都必须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本质。当一个叫做“人性”的东西被异化或者是进化之后,我们对这种传统的“人性”的思索、坚持,对空泛的“自由”的追求有什么意义?
因此,《沙丘》好像什么都没给我们,但却也什么都给了。
你尽可以说,维伦纽瓦现在的影像风格只不过是电影界对当代艺术语汇的运用,他个人只是一个风格的代号,而不像一个“人性”的,“活生生”的作者,一如他现在隐藏在IP背后,小众而不为人所知,可这样的批判还有意义吗?维伦纽瓦已经当之无愧是未来好莱坞的“大师”之一,他可能就是21世纪作者导演理想的样子;
也许未来我们的其他“作者”,我们自己,所有的“观众”,也都不会再“活生生”拥有明确的表达欲和鲜明的自我判断:他们会像维伦纽瓦那样,安静、舒缓、洁癖,沉溺于对崇高的接近和冒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寻找飞升的天堂——赛博世界提供了一种人类生活的新方式:成为神灵。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