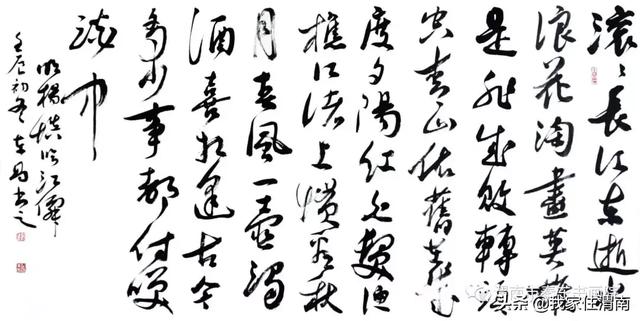年夜饭上,都有着必备的主菜,这主菜,天南地北,各地不同。
家在广东的人,必然是白切鸡和蒸鱼。而在飘雪的北方,饺子必是主菜,但到了江南,汤圆不可或缺。重庆的年夜饭上,会有一盘烧白,江苏则是滚圆硕大的红烧狮子头。陕北的蒸花馍,五彩缤纷地堆满热炕头。东北的冰天雪地,则是热腾腾的小鸡炖蘑菇和杀猪菜。湖南的剁椒鱼头,常常用青红剁辣椒堆出两种浓烈,福建是一锅名贵海鲜大集合的佛跳墙。而到了上海,切得静静细细漂漂亮亮的扣三丝,分外美丽。
这些食物是否真的好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但之所以这些食物成为自家年夜饭的主菜,与食材珍贵烹饪独特的关系都不大,最宝贵的原因就是这里的人自从出生以来,最熟悉、最接受的味道就是它。
* 红烧肉
红烧肉是一道需要很用心才做得好的菜,小时候总以为表皮那诱人的酱黄色是用的酱油,后来自己试做,才知道红烧肉是不用放酱油的,而是用糖在高温下熬成的焦糖挂色,这个步骤需要十二分的耐心,一不小心就会煳掉,糖煳在锅里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洗很久都洗不掉。
挂色之后,就是加水小火慢炖了,慢炖也是需要十二分耐心的事情,水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炖时得用心留意,以免水干锅煳。所以红烧肉虽然平常,其实是需要无限爱心才能完成的一道菜。外面做得再好吃,你还总是最惦记家里奶奶和姥姥的手艺。

图/淮扬府官方图片
* 烧鹅
北京最有名的美食是烤鸭,能与之抗衡的,大概只有南方的烧鹅。
听起来差不多,但其实大有差别,鸭子是平和随意的动物,而且长得快不挑食。而鹅则是性情高傲暴烈的动物,只吃青青河边草,却能与大人“打架”、“欺负”小孩,很多地方都养鹅当看家狗用,前一阵有一个刷屏的视频,大鹅成群结队过马路都无人敢惹。鸭肉肉味清淡性凉,鹅肉味道丰腴浓厚,部分人吃多了易上火。

烧鹅之美,在于又厚又脆的烧鹅皮里,里面藏着一层香气绕梁三日的脂肪,用荔枝木慢慢烘烤,脂肪慢慢渗入松软的肉中,一口咬下,皮脆肉软,那种香味就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能满足潜意识里对脂肪最深切的渴望。
烧鹅最美妙的是鹅腿,很多在粤港澳长大的人认为是因为鹅睡觉的时候,是用左脚单脚站的,所以左腿比较有韧性,比右腿好吃。还有个听起来有点好笑的说法是:鹅跟狗一样,是抬起左腿尿尿的,于是,尿会顺着右腿下来,而左腿非常干净。家住南方的人,回想下小时候长辈是不是都会把烧鹅的左腿留给你。
* 白菜
白菜是少数可以天天吃而不腻的菜品之一,无论过去现在,无论贫穷富有。
四川有道名菜叫开水白菜,是用火腿、老鸡、干贝、肘子等熬出的清澈高汤来煮白菜,有这么多美味做幕后英雄,这样的开水白菜才上得了国宴的台面。白菜可以做成清心寡欲的豆腐白菜“永保平安”,也可以变成加入鱼露、梨汁、韭菜、辣椒粉,五味纷呈地发酵成强烈鲜味的朝鲜族特色的辣白菜。到了东北,白菜以微盐腌渍,经过漫长时间的发酵之后,脱胎换骨成为极鲜的酸菜,用来炖杀猪菜,甚至能取代猪肉成为美味的主角。
白菜就是这样,能“安于”任何的贫穷困苦,也“享受”得了无限的富贵与风光。因为平淡,所以成为习惯,因为习惯,所以变成许多人的“真爱”。

* 饺子
年夜饭的菜单无论怎样更迭,C位的饺子永远都是压轴。饺子的前奏是腊八那天开始腌制的腊八蒜,蒜由洁白变翠绿,年就跟着一天天走近。
饺子的讲究可就多了,各地不同。除了猪牛羊肉,山东沿海是鲅鱼饺子和皮皮虾饺子当家,大连人还有人会用海肠包饺子。据说海肠在没有味精的年代是绝对的调鲜佳品,经验老到的老厨师会将海肠晒干磨粉,偷偷放在小瓶子里。教徒弟时候,永远在最关键的时刻把徒弟支使开,放入海肠粉,以避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除了馅料,各地的饺子皮花样也多,有翡翠的、三色的、五色的、蛋皮的,不胜枚举。包括包饺子的方法,有的是捏饺子,有的是挤饺子,有的能在饺子褶上捏出麦穗。有人甚至觉得包饺子方法的不同非常影响口味,只有小时候奶奶给他捏的饺子才能胜过世上一切珍馐。
年夜饭的这顿饺子,很多家里还会吃得很有仪式感,比如在饺子里包一个花生、包一枚硬币,谁吃到了,就是来年最幸运的人。小时候,长辈会在包饺子时候偷偷做个记号,自己故意不夹这一个,吃到的孩子总是会高兴地跳起来。有人说,速冻的叫饺子,妈妈包的才叫过年。如果您今年没法赶回家过年,也请一定要吃碗饺子,开启这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
* 汤圆
北方人钟爱饺子,南方人过年偏爱汤圆。都是洁白包裹香甜,都是热气腾腾、团团圆圆,北方人是“饺子喝酒越喝越有”的浓情,南方人则是“吃了汤圆好团圆”的蜜意。
作为糯米制作的食物,汤圆最早的名字叫做“浮圆子”,原因是它刚下锅的时候是沉在锅底,煮熟了自然漂浮水面,好像人的一生一样,几经浮沉,皆无定数。软滑洁白的糯米粉,更是像极了性格细腻又坚韧的南方人。汤圆里可以包着豆沙、花生酱或者芝麻,也可以是咸香的鲜肉丸。牙齿、舌尖碰到清淡柔软的汤圆皮,一口咬下,满嘴的浓香糯甜,寒冷的冬天或清寒的初春来上一口,都是说不清的幸福感。

* 辣椒
辣不是味道,而是情怀。据说,味觉只有四种,酸甜苦咸,辣不是一种味道,只是一种对舌头的刺激和挑战。然而,要说到关于口味的乡愁,许多人都认为是辣。
湖南喜欢剁辣椒,用来蒸鱼头再好不过。贵州喜欢糊辣椒,再做成蘸水,蘸包得很漂亮的“丝娃娃”。四川喜欢辣椒油,辣椒炸香出来的红油,伴在猪耳朵里“巴适得很”。江西喜欢辣椒粑,做成红彤彤的糍粑,大口吃下去。云南喜欢糟辣椒,闷透的辣椒就可以能够凉拌或红烧“一切”食物。客家喜欢酿辣椒,把肉末香菇酿进去,吃到辣的还是不辣的要看人品……以上种种对辣椒的诸般“蹂躏”,只是冰山之一角,所有热爱辣椒的地方,都能把辣椒做得风情万种、口味各异。
不过要比辣,各地人民都不会服输,就跟争哪里的姑娘最漂亮一样。辣椒红彤彤,红火、热闹,正应了好年景,就对了。
汪曾祺笔下的过年,是“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的岁朝清供,也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温柔团圆;鲁迅笔下的过年,是近处燃放着震耳的大音未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也是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煮熟之后横七竖八地插些筷子,以做“福礼”;丰子恺笔下的过年,是自八仙桌拣出白而肥、又香又燥、比炒米更松、比蛋片更脆的谷花拿来泡糖茶,也是买来大大的万花筒,摆在河岸上一齐放,河水反照映成开满银花的火树……故乡的味道习惯而顽固,就像卫星定位系统,一头定位的是千里之外的异地,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故乡。一顿年夜饭,既简朴又丰饶,很多人半生闯荡,带来家业丰厚、儿孙满堂,最终会发现行走一生的脚步,起点终点都是家所在的地方。中国人秉持千年的信仰,朴素而有力量:认清明日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
新京报记者 王萍
图 资料图片(除署名外)
编辑 彭雅莉 校对 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