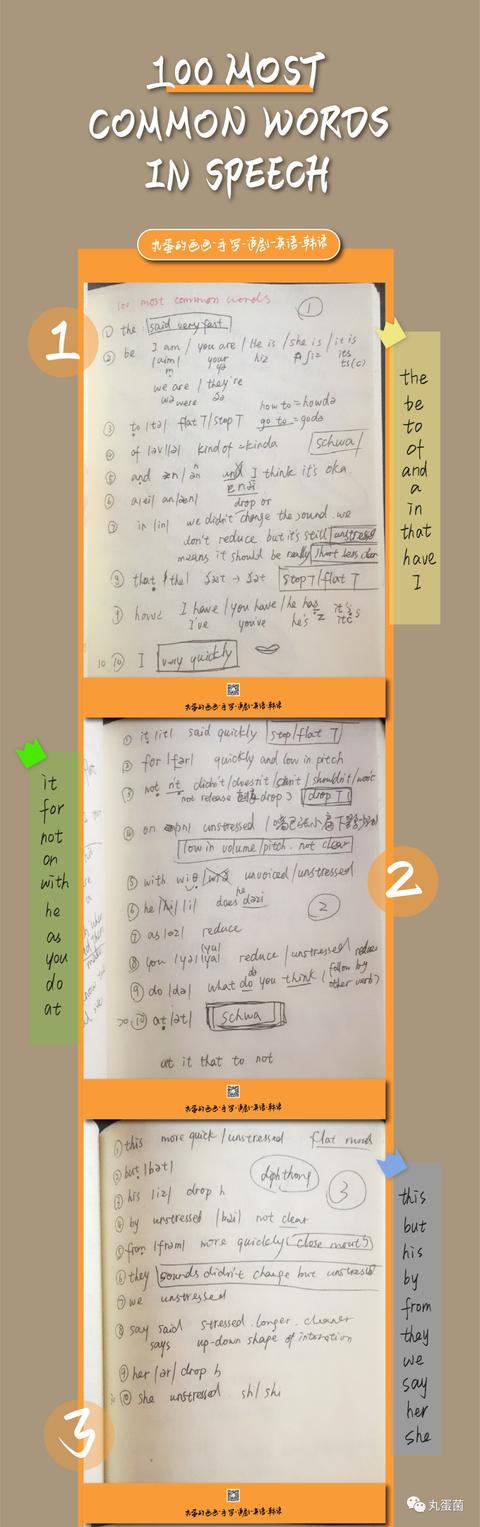文 | 张 林 泉
抗日战争期间,我的母校嘉兴一中(前身为“嘉兴中学”,简称“嘉中”)曾经在新塍设立分校,供初二以下学生上课。日寇平湖登陆当天,嘉中本部师生也紧急疏散至新塍,并入分校。
嘉兴沦陷前夕,在嘉中校长、爱国教育家张印通主持下作出了“应变迁校”壮举:嘉中师生从新塍分校出发,千里迁校,闯出了一条可歌可泣的“教育救国”的道路,书写了嘉兴乃至浙江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影响深远!
当年嘉中新塍分校初二学生查良镛(金庸)1992年曾为母校嘉中题词:“当年遭寇难,失哺意彷徨。母校如慈母,育我厚抚养。去来五十载,重瞻旧学堂。感怀昔日情,恩德何敢忘。”
那么,当年嘉中为何要设立新塍分校?设在新塍什么地方?最后结局如何?今天还能寻到踪迹吗?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总想弄个清楚。经遍查史料,多方求证,经历了辛苦、曲折、有趣的寻觅过程,终于走近了历史,寻到了踪迹。
适值母校百廿周年之庆,谨撰此文,聊表学子之心。
(一)为 何 要 设 分 校查母校校史。嘉兴一中《八十周年史稿》这样记载:“一九三七年七月,本校改称为浙江省立嘉兴中学(简称“省立嘉中”)。是年秋季,添办高中,增建三层楼一幢,计十二教室,未及竣工而抗日战争开始。于是设分校于新塍,为低年级上课之所,高年级仍留禾地,筑防空壕以避空袭。”简明扼要。
查母校老校长张印通档案。2019年11月5日,我和秀洲区政协文史委叶加先生赴嘉兴学院平湖校区档案室,见到了老校长张印通的“人生档案”。
相关资料显示:
1937年6月底,张校长奉命上庐山,参加蒋介石亲自挂帅的“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一期训练,编在教育组。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抗日干部,为长期抗战作准备。蒋公亲自训话一共四、五次,每次训话前,把学员一个一个“叫出来”,点名点到。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蒋公下令抵抗。自7月10日起,许多受训的军事学员和高级将领从庐山走上前线,在军乐声中开赴战场。7月17日,蒋公在“庐山传习学舍”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对日作战全面开始。
7月18日,“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一期提前结束。对此,张校长有亲笔记述:“这个训练的中心要点,在我学习当时看来……以为训练我们对日准备长期抗战……因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对日形势紧张,所以提前几天结束”。
庐山受训,使张校长进一步确立了“教育救国”的理念,更加坚定了应对战争,艰苦办学的决心和信心。
据其子女回忆,张校长庐山受训回来,曾在笔记中(老校长一生留下的所有笔记本均在“文革”中销毁)提及:
“我是校长,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手中握着学生的命运,肩上扛着国家的未来”;
“我心里,怀着教育救国的理念,装着青年学生的理想,藏着中华民族的梦想”。铆足了劲为全面抗战作应对准备。
1937年8月13日,时局突变:淞沪战争爆发!这样一来,嘉兴瞬间接近前线,常受敌机侵扰,人心惶惶。有的学校开始停课,放假。
张校长立即采取应变措施。他通过关系(传说是通过“新塍老土地”,当时主持抗敌后援会新塍分会工作的张木舟先生)在新塍设立了分校,将初二以下(包括“师训班”)低年级学生在开学不久就安排到新塍分校,避开敌机空袭,让他们安心上课;初三、高一新生继续留在嘉兴本部,并筑防空壕,在空袭警报声中坚持教学活动。
1937年11月5日,日寇平湖登陆。浙江省教育厅电令浙北“省立各校”应变疏散,各校执行结果大多解散。只有嘉兴中学因早有“备胎”“新塍分校”而及时有序退出禾城。当日下午,张校长即率领高年级师生冒雨步行三十多里疏散至新塍,并入分校,继续上课。
(二)分 校 校 址 寻 踪嘉中新塍分校究竟设在新塍哪里?很遗憾,张校长档案资料没有提到。好在王梓良先生在《终身奉献教育的张印通先生》一文中说: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嘉中亦向北乡之新塍借该镇之蚕种场安顿新生及师训班……”。
蚕种场,令人惊喜!可蚕种场又在新塍哪儿?
于是,我到新塍找到母校同学虞大兴。他退休后在新塍镇“镇志办”帮忙,任副主编,有这有利条件,便委托他协助调查,并建议查实后在新版《新塍镇志》中提上一笔。大兴兄一听,事关母校,事关新塍,一下子来了劲,说理当尽力而为。不久,便有了回音,说经过走访多位老人,确定蚕种场的地理位置在现新塍镇虹桥北路出名的“罗汉松王”所在地,这地方原先叫“乐善坛”。我再赶新腃,大兴兄领我到现场,将“乐善坛”遗存的古树名木——“罗汉松王”拍照留存。
值得一提的是,“乐善坛”的出现,使我想起了叶加先生在《民国贤达张木舟》一文中提到过:“……‘九一八’事变后,张木舟回到家乡……和友人在新塍开设‘兴农蚕种场’……抗战胜利后……张木舟在新塍乐善坛办蚕种场,恢复生产蚕种……”(查1998年版《新塍镇志》人物“张穆舟”,号木舟,也有相应记载)。由此证实,分校的设立,张木舟先生确实帮了大忙,出借的“蚕种场”即“兴农蚕种场”,抗战胜利后恢复生产,地点在“乐善坛”。
有意思的是,这“乐善坛”可能是后人叫别了。据当年在分校读初一的新生沈如淙回忆说,那地方叫“六禅坛”。
那是2019年12月5日下午,我通过学弟沈震拜访了他的父亲——百岁老人、离休老干部沈如淙伯父。沈老是新塍本地人,曾在“张印通先生纪念会”上亲口说过“我也是张先生的一名学生……”
这天,沈老精神很好,跟我聊了足足一个小时。关于新塍分校,他回忆说:“……考上了,当然要读书!就到嘉兴读书了……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张校长把我们这些初中生先转移到了我老家新塍镇……校长早就生心,那儿有个分校……那地方叫‘六禅坛’……”
“六禅坛”和“乐善坛”,两者谐音,叫别是常有的事。那么,哪个更符合历史事实呢?
一个意外收获,在沈老家里看到了另一位当事学生董民瑞写的《九十自述》的书。董民瑞也是新塍人,是当年嘉中初二学生。他在书中提到“……到1937年……嘉中迫于情势,决定将学校内迁。首站是新塍镇,地点选在东栅北郊的‘六禅坛’,该坛为道观,房舍不多,匆忙中因陋就简开了课……”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六禅坛”得到了当事人有文字记载的明确佐证。

2019年12月5日下午三时,嘉中学生沈如淙(左,百岁离休老干部)在家接受笔者访问时的情景(照片系其子沈震所摄)
至此,我以为新塍分校的校址可以认定了,就在当年新塍东栅北郊六禅坛(亦称“乐善坛”)的兴农蚕种场。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又发现了新的说法,有当事学生张景馨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大当铺”。他从江苏金山中学逃难出来,后被嘉中收留为借读生。他说:“……在新塍一家大当铺中找到了逃难中的嘉中,蒙张校长允诺,当天下午便随嘉中乘船西行……”
面对这一说法,我顿时懵了:难道分校有二个校区?
据1998年版《新塍镇志》记载,当时新塍镇共有三家当铺:三元街的“泰来当”;西北大街的“泰亨当”;问松桥西的“同和当”。哪一家呢?无法确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找到了当年学生“鹅”(即徐凤吾)在《寄友人》(刊1940年1月嘉中校友会旅沪分会编印的《友声》创刊号)一文中回忆说:“……从制种场搬进阴森的泰来当不久,分校也停了课,接着便听说松江失陷了,学校不得不再移动。”
毫无疑问,“制种场”即“蚕种场”,说明后来分校又从蚕种场搬到了三元街的泰来当。

1940年1月嘉中校友会旅沪分会编印的《友声》创刊号
这样,有关嘉中“新塍分校”的校址问题,终于理清,概述如下: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后,嘉兴中学为应急避险而设立了新塍临时分校。一开始设在新塍镇东栅北郊的六禅坛(亦称“乐善坛”)兴农蚕种场。后来,又从蚕种场搬到了三元街的泰来当。
经过八十多年的历史变迁,六禅坛(蚕种场)和泰来当均已毁。今天唯一还能见到的是新塍镇虹桥北路原六禅坛遗存的古树名木——罗汉松王。

六禅坛(乐善坛)遗存古树名木“罗汉松王”
(三)分 校 终 局 揭 秘揭秘一,关于嘉中决定迁校离开新塍分校的日期。史料说法不一,包括校史记载,均不太靠谱。
母校校史《八十周年史稿》记载:1937年“十一月五日……本部的全体师生转移到新塍分校。翌日……即由张印通校长及部分教师负责带领转移……”。
母校110周年《嘉中春秋》对此日期表述一致,未有异议。按此“翌日”推算,嘉中离开新塍应是当年11月6日,而很多当事人回忆在本部师生退至新塍后又呆了数天,显然,校史记载有误。
嘉兴地方文史作者徐元观老先生有《张印通率嘉中学生千里撤退纪略》(刊《秀洲文史》2015年第三期)说“于11月15日从新塍出发,为抢救青少年学子而走上了避寇的千里撤退之路”。其依据未作交待,虽接近“数天”事实,但不见出处,很难认可。
张校长亲撰《母校史略》有“当城陷前数日,印通偕员生暂退新塍,旋复西退,步行抵于潜,借地继续上课。”一个“旋”字,意即“不久”,令人猜测。
那么,嘉中究竟哪一天离开新塍?
为揭开谜底,经不懈努力,综合各方信息,终于复盘了当年迁校的决策过程——
1937年11月8日,日寇飞机对嘉兴城实施狂轰烂炸,县政府法院及国民党县党部被炸成瓦砾堆,天主教仁爱堂育婴所也被炸,惨不忍睹。城中百姓,四处逃难。此时的嘉中,一部分有家可归的师生,纷纷离校,尚有“师生百数十人”,家乡沦陷,无家可归。
学校何去何从?
必须作出决断。张校长紧急召集全体在校教职人员开会,主持议决学校出路。当时,大多数主张迁校办学,也有人主张就地解散。章克标先生认为这场战争一时胜负难料,不知何时结束,带这么多学生逃亡办学,万一出事,责任重大,无法向学生家长交待。
张校长认为“嘉兴中学不能放假,不能解散!嘉兴中学的师长不忍看着自己的学生沦陷在嘉兴当亡国奴,校长和师长有责任带领学生撤离即将沦陷的嘉兴……”。
通过民主表决,作出了事关学生命运,事关学校命运,事关“教育救国”的重大决定:迁校。
有人提出:校产怎么办?“整理好,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的寄存起来”张校长掷地有声地说:“若把校产比学生,校产是有价的,青少年学生是无价的……”
思想统一后,决定于当年11月11日下午装船,傍晚出发,离开新塍。为何选在傍晚出发?天黑敌机不易发现,相对安全。
这个日子的揭秘,全靠一位笔名为“萤”的当年学生,写了一篇《从嘉兴到丽水》的文章,发表在1940年1月张校长题词的《友声》创刊号上,文中提到当年在新塍“人心惶惶地住了几天,起先我们还想上课,然形势是越加紧张,终于在十一日下午乘船离开了这我们生活过许多时候,永远带给我们美丽回忆的新塍”。
这是最早最明确的记载,文章发表时间距离迁校仅两年多一点,且《友声》创刊号题词、编辑大都是当年亲历者。可见,这一史实,可勘校史记载之误。
揭秘二,关于校产存放去向。
嘉中作出迁校决定时,由教务处负责带领学生撤离新塍分校,由事务处负责转移存放校产。师生去向,跋山涉水,艰难到达丽水碧湖的壮举,感天动地,名闻遐迩。然有关校产去向却成了秘密,鲜有人知。
现据张校长档案中的亲笔记述,结合相关史料,整理后“透露”如下——
留存新塍之公私(师生衣物)物件,由学校事务处人员钱辅庭、陈国源负责分散存放,有的存在乡下教工家中。其中物理仪器由老校工“平湖老二”负责搬运存放在教员陈宝铨家里。“平湖老二”不幸在战时亡故。
这些校产,很多在战乱中损失,一部分尚留在陈宝铨家中,还有一部分被一所私立义务小学借用。据1998年版《新塍镇志》记载:1938年下半年,新塍镇私立正风义务小学筹建,“教学设备、用具暂借省立嘉兴二中寄存在新塍的设备”(“省立嘉兴二中”即嘉中前身)。
抗战胜利后,张印通重返嘉中,继续担任校长。有关校产,张校长托原经手陈国源及新聘事务员钮介春(新塍人)暗中调查了解,摸清情况后由学校向嘉兴专署文教科请示,并经文教科查明详情后,由嘉兴专署交新塍区公所处理,追回部分仪器和桌椅,计装一船回校。
嘉中新塍分校,存在时间虽短,但她作为嘉兴中学战时应急避险而设立的临时分校,其使命特殊,意义重大:保护了学子,抢救了人才,功不可没。
附注:作者为嘉兴一中第八十二届(1966年7月)毕业生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