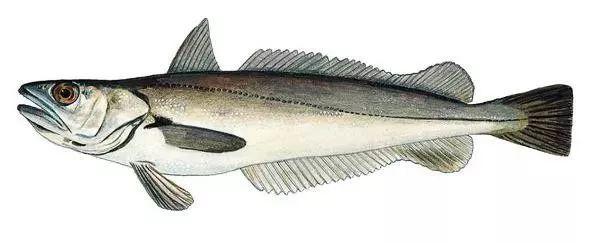佛教以离苦得乐为修行初因,以发菩提心为成佛初因。
关键词是:离苦和发心
这和他们以人情&心识为出发点的原始教义分不开,这里简单分析下:
离苦,来源于我心太重。离苦太重,才会以我情好恶苦乐为出发点。离苦得乐,完全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这是佛教继承身毒以身为毒地域特色的一种宗教基因,和早期佛教自我轮回善恶报应相呼应。
后来,大乘出现是另外一个改革。只怕可能是面临自私的指责,进行的改革才是大乘龙树化的肇因。而那段时期,正好是汉武帝没事就打西域,输出汉家儒学时代前后,所以没准就是受到儒家兼济天下的影响,佛教才来了一次彻底的大转型。
不要总以为我们的文明对印度的没有影响。季老那本《糖史》的历史地位就在于充分证明了中印早期文明的交流是双向的。四个凡是后的佛教逐渐丧失了客观平视事实的能力,很难真诚交流是个遗憾。而正因如此,小大乘之间的分歧很明显。后面洗地圆融的说法虽多,但宗教神学性严重,其实对于修行不利,还不如干脆些承认得了,而不论怎么圆融洗地,很多初始佛教的烙印非常清晰。
早期佛教追求个人解脱,那么必然的前提是个人得失。舍身取义的儒家精神只怕和佛教这个根本出发点是正好相反的。
大乘,在汉地兴起的原因,或许恰恰是扩大到众生的儒家兼济仁义之心。

发心这种修行的方式,如果没有配套的行动,也就是戒律辅助,几乎就是跳大坑的行为。发心是为了成佛这个宏愿,但是行动不往那边走,只能是越发心越麻烦。
不说宗教修行的事,很多人做事之前都是想的特别好,愿望愿景特别理想化,总是给自己一个很高的期望值,一点不现实,结果实际达不到,行动力就变得越来越差。
为啥?想太多。心和实不能形成正向回路,导致逐渐丧失信心。发心,白话的意思就是去想去愿。而如果不是切实修行的俱足和尚,整天发心,行无所止,那么空有其愿。身心不匹,发心就是大坑,信心渐渐渐失,心理回路逐渐变成负的,于是每次都得重新给自己洗脑,说今天一定要如何,结果到处打游戏、看小说、排解不现实造成的紧张,进而时间越少,精神越紧张,越要分心于别处,越不能集中注意力。
为什么?习惯发心了,想太多,心理压力太大。时间都耽误了,压力就更大了。我们叫这种为空愿。
这种情况多出现于老实人身上,也就是重诺言的人啦,自己把自己的理想太当回事的人。对于另外一种根本是嘴上说说、心里胡想的人,基本的诚意都没有,只不过需要这样的说法做点缀,那么连发心都不算,压根就不在此讨论的范围之内。
我有学生就是老实人,多少是受到佛教发心空愿的影响,总给自己定一个特别高的目标,导致生活学习上沾染了这些缺点——越到要紧的时候,越很难平静专注于当前。每次紧要关头,总是用其他方式分散注意力,这是人的自我保护机制,试图缓解这种压力,其实,也就是以前修习佛教没人讲解发愿是怎么回事的原因。
自修真的坑太多:观心分念而不知,精神杂乱而不静。而所谓的抑郁,很多就是这样积久而来,心意和结果总是差太多,总是达不成,日子久了,对自己信心渐渐没有了,面对挑战总是担心失败,到了最后,就有点难以面对现实,所谓畏难的拖延症,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很多人的真实水平很高,但是因为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而严重影响自己水平的发挥。水平都不错,但发挥不出来啦。想太多就是拔萝卜,太理想化就是拔萝卜。而守根,就是每天一点点,积细成巨,久而无匹,不成而成,所谓诚者自诚也。所以我们不以发心为教法,不提倡初学发什么心。

道家儒家皆不以人情苦乐心识为出发点。
儒家以人伦入手,以人我关系为修行的基础,忠恕以推之,以家国天下昌盛不衰为追求,对于个人得失并不那么看重。
儒家对于家族的血脉延续更看重,所以中国的善恶报应,往往祸福延及子孙——也就是所谓的承负。
道家以人天不离为入手,认为人是天的一部分。苦乐乃人之情好,故皆处之以淡然,并不会特意以此为修行动因。甚至不会以人情好恶为出发,而只是追求返本还源,参悟大道,长生只是这个路上或许会出现的副作用。
if not,so be it.

道教,综合两家,提出的入手出发点是结合人伦天道:敬天法祖躬行。
最后,落在行上。
不单看你啥心,但也不否定由心出发的可能,也不管你是欲参大道,还是怕死,还是好奇,还是求解脱等等心愿都可以,但光想光说没用,算不得修行初因。需要做了,而且方向要对,才能算入道修行初因。
切身践行守根,就是广义上的信士。即便不皈依于道教,也是儒道两家的践行者,我们并不外之,因为你的方向和行动必然会趋于敬天法祖躬行。所以,我们以行动来衡量人,入道修行必须经过基本的考验,三年五载看看这人到底做到没有,不会因为你的言语发心下定论。
大家看到的所有资料,都以这种视角去理解就不会有问题了,因为行动的方向对,不用去管啥心咋说^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