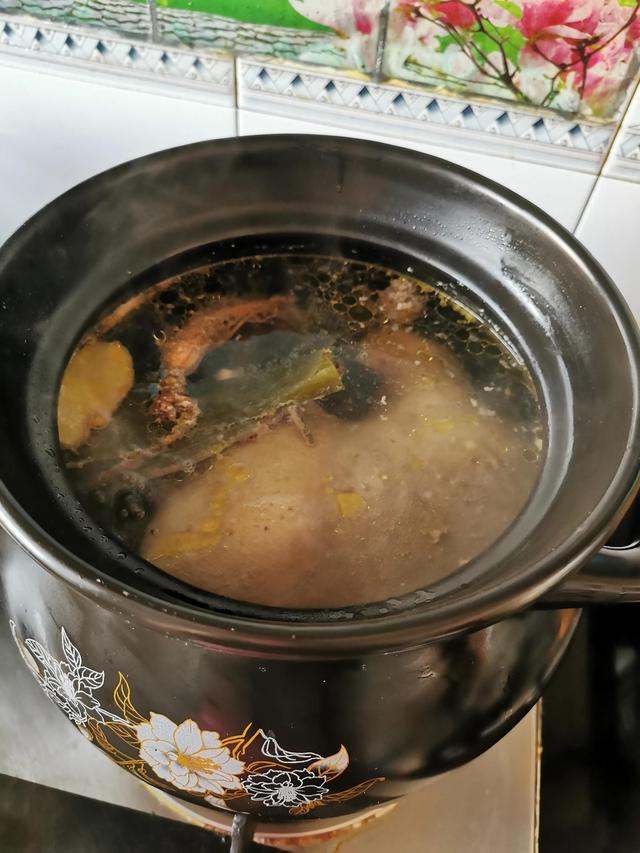今天从《论语》中关于吃的一句说起,那便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出自《论语》的“乡党”篇,但不同的人的理解还是不太一样的。按照一般的理解,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大概是说,粮食舂得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形容食物要精制细做。当然也有不同的解释,比如钱穆先生认为,这句话中的“厌”是“餍足”的意思,即饱食。这样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截然不同了,就是不因食脍之精细而特别饱食。当然,孔老夫子的原意是什么,我们现在大概也无法确证了,每种理解似乎都有道理。但我还是偏向于第一种,因为《论语》中跟在这句话后面的,是一连串关于孔老夫子在吃饭方面的讲究的记载,比如“色恶,不食”、“失饪,不食”、“割不正,不食”等等。合而观之,此句的意思理解为强调饮食要“精耕细作”似乎更为妥帖。由是有人认为孔老夫子其实是个十足的“吃货”,这真是极有道理的。更有甚者,有人由此诊断出孔老夫子肠胃不好,长期患有胃病,这真是目光如炬,华佗附体。
但我想,《论语》记事极简,但竟毫不吝惜笔墨,对于孔老夫子之“饮食”做如此细致之记载,大概不是为了告诉后人这位老先生是个十足的“吃货”。《论语》中不仅记载了孔老夫子之饮食,而且记载了其穿着。《论语》明言:“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用今天的话说,光真皮大衣就得有好几种,用以搭配不同颜色的衣服。由这些衣食细节我们可以管窥孔老夫子衣食住行之全貌,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大多数时候,这位老先生绝不是一个粗糙饮食、鄙陋穿衣的俭朴状态,甚至我们可以推测出,孔老夫子非常注重饮食之色香味俱全,服装之华美得体。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说过,《论语》的核心是谈如何修养成为君子的,而君子立世,是脱离不开“衣食住用行”等方方面面的“俗事”的。君子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不是不修边幅、放浪形骸的浪人。我甚至觉得,正是在对这些“俗事”的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考校当中,才能完成君子之修养,即王阳明所谓“洒扫应对皆为致知”是也。君子内修其德,外塑其身,德行华其性,威仪彰其形。但我们不能忘了,这种“考校”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换句话说,君子是需要“谈钱”的。
或许有人会说,儒家不是讲“安贫乐道”吗?不是讲“君子固穷”吗?不是讲“箪食瓢饮”吗?怎么还会讲究吃穿用度?怎么还会去谈钱?这真是对儒家思想的莫大误读。
君不闻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字面解释就是:如果可以挣更多的钱,哪怕就是做给人驾车这样卑微的事情,我也是愿意去做的。这不活脱脱一个孜孜以求富贵的形象吗?只不过我们不能忘了,这句话还有后半句: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里便有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可求”?什么情况下“不可求”?君子之“好”到底是什么?其实,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这个“可求”和“不可求”的界限是很清晰的,那就是“合乎道”。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简言之,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的“道”有方法的意思,也有道德的意思,当然还有“天道”的意思。而君子之好,也是这个“道”。《中庸》云:道,不可须臾离也。当然,儒家所讲的“道”历来众说纷纭,争议极大,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们可以另起一篇再论,此处暂且略过。
由此我们可以说,儒家并不鄙视富贵,他鄙视的是“无道”。如果一个人生来富贵或者能够合乎道地去获得富贵,他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做一个对衣食住行非常讲究的人,当然可以尽己所能地去过更好的物质生活。孔老夫子作为曾经做过鲁国大司寇这种正国级干部的人,收入自然是不差的,所以他老人家的生活水平自然是比较高的。当然,如果不幸生而贫贱,则也应先解决生存问题,而且要尽可能地让自己生活的水平更高一点,哪怕是通过从事“执鞭”这样卑微的工作。自然,如果实在没有挣钱的机会和本事,那就只好像颜回那样“箪食瓢饮”了。但我们需注意,孔子称赞颜回,并不是因为他“箪食瓢饮”,而是因为他“不改其乐”,也即他对“道”的坚守。其实如果我们细读论语,是能够感受到孔子对颜回“不得其时”、“不得其位”而困顿的惋惜之情的。

昌明之世,君子得其“时位”,物质生活必定优越。如果我们反观周边,有君子之德的人大多困顿,那么只能说明,我们的时代其实并不比孔老夫子的时代更文明。如果颜回生活在现代,还是只能过“箪食瓢饮”的生活,乃至营养不良而早夭,那只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