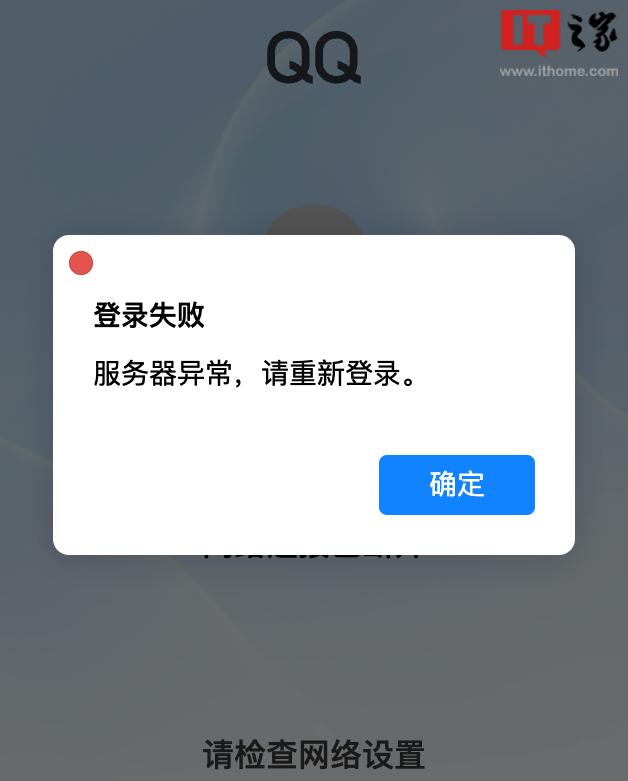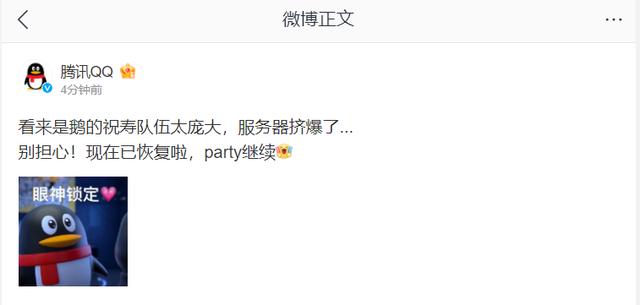“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王熙凤的出场,显得非常突兀。
你可以将其与这一回中其他人物的出场比较一下:贾母出场前,丫头们说:“刚才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贾氏三姊妹则是贾母派人去叫来的:“贾母又说:‘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众人答应了一声,便去了两个。”宝玉出场前,王夫人已经说得很清楚:“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庙里还愿去了,尚未回来,晚间你看见便知了。”
唯独王熙凤的到来事先没有任何铺垫和交代,这就是一种写法上的变化。王熙凤一露面就显得与众不同,全场的气氛和焦点顿时为之一变。前面的话题,多少有些沉重,气氛也有点沉闷,而“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一句,则转得异常轻快,如风行水上。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
在交际环境中,身体空间与人的关系亲疏是有关系的。有人把交往中的安全距离分为四种类型:亲密距离(45厘米以内),私人距离(45~120厘米),礼貌距离(120~360厘米),公共距离(360厘米以上)。林黛玉进贾府后,之前只有贾母一见面就搂着她哭,因为就跟见到了自己最疼爱的女儿一样,其他人在介绍相认的过程中都保持着一定距离。按理来说,王熙凤也应该这样,但她一进屋就“携着黛玉的手”,这样的身体距离和肢体语言,传递的是一种毫无隔阂的亲切感。
“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与前面急切的快人快语不同,这时她反而不急于说话了,“细细”二字,表现出她的认真,如果没有这个细节,而只是写她看了一眼,那么后面的夸赞就会让人觉得敷衍。
“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仍然不急着说话,真沉得住气。这一细节,一般人想不到,这是凤姐细致周到的地方。王熙凤这个人,她要想对你好的时候,可以做得让你每一个毛孔都觉得熨贴;反之,她恨你的时候,会把你往死里整。
“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儿才算见了!”在这里,我们要先说一下黛玉的年龄。曹雪芹在开篇第一回中说,此书“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但在人物的年龄上却问题很多。以黛玉为例,在第二回中,黛玉五岁,从雨村读书,一载有馀,母亲即病亡,随后贾母迎接入京,这样算起来,黛玉到贾府时不过六七岁。如果从宝玉这方面来推算,黛玉入荣府在己酉年,其时宝玉十一岁,据黛玉母亲的说法,宝玉比黛玉大一岁,那么黛玉十岁。这两种推断,都与我们的阅读感受不太符合。因此,台湾学者蒋勋抛开这些考据式结论,直接从书中人物言行所表现出的心理特征来推断,认为黛玉、宝玉、宝钗、湘云这些人大概就是十二三岁。也就是说,黛玉当时顶多相当于现在初中低年级的年龄段。王熙凤用这样的话来夸她,显然有点过了,感觉偏成人化了。在这一回中,众人眼中的黛玉,“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宝玉眼中的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这都是很客观、准确的描写。相比起来,王熙凤的评价虽然最高,却很空洞,并没说到点子上。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倒是觉得,王熙凤虽然“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其实并不一定是在认真观察,她可能是在考虑话该怎么说,否则按曹雪芹的风格,这里是会有一段肖像描写的。不过,在那样的场合下,这种无以复加的高度赞美倒也并不显得特别肉麻,毕竟只要说得喜庆,让人听了高兴就好。
但是这样一说,就显得站在一旁的迎春、探春、惜春都相形见绌了。女孩子很在意这个的,这种地方稍不注意就会生出矛盾来。所以,王熙凤接着说:“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这里还是在夸黛玉,但把她和贾府的嫡亲孙女相提并论,这就把三春都夸了。而且听起来,三春才是正版,黛玉虽然标致,毕竟还只是“像”嫡亲的孙女儿,相当于复制品,在三春听来,似乎还是略胜黛玉一筹。这人夸的!
接下来就说:“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这倒是实话,但贾母不会说,王熙凤替她说了,说得黛玉心里暖和,贾母心里舒坦。
当一个人悲伤的时候,有两种方法可以减轻他(她)的痛苦,一种是宽慰他(她),还有一种就是陪他(她)一起哭。贾母一见黛玉,顿时大放悲声,“当下地下侍立之人,无人掩面涕泣”,属于第二种。随后众人“慢慢解劝”;后来贾母说起女儿的死,再次“呜咽起来”,“众人忙都宽慰解释”,都属于第一种。王熙凤这两次都没赶上,只好自己创造机会。“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这一下转得非常自然,毫不生硬。更令人叫绝的是,话锋一转,情绪马上随之变化,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情绪的控制达到了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切换的境界,而眼泪就像自来水,说来就来。真可谓不是演员,胜似演员,那些演哭戏还要滴眼药水的演员可比她差远了。这一哭的感染力是显而易见的,把贾母都感动了,倒反过来劝慰她。王熙凤这时“忙转悲为喜”,一个“忙”字,非常生动,传神地写出了她的曲意承欢。
这一段描写,总共才一百多字,写得不疾不徐,自然舒展;寥寥数语,口吻逼肖,内涵丰富,滴水不漏;转瞬之间,情绪数变;方寸之内,一波三折。把人物写到这种程度,该对人物性格有怎样深刻的理解,该有怎样丰厚的生活积累,该有怎样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和高度娴熟的描神绘像技巧!

中国的古典小说,在写人的时候,往往通过叙述者来介绍其身份。曹雪芹打破了这种千篇一律的简单写法,让人物身份通过其言行逐步显现出来。如果你第一次读《红楼梦》,不看前面的内容,直接看这一回,读到这里,你还只知道王熙凤是“琏嫂子”。随后王熙凤对黛玉说“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以及王夫人问她:“月钱放过了不曾?”你就明白了,原来王熙凤是贾府的管家太太。这种写法就显得更自然、巧妙。
王熙凤在回答王夫人的问话时说:“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想是太太记错了?”这句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你还记得王熙凤进屋前说的那句话吧,我说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悬念,王熙凤这时才说出来:原来她是带人到后楼去找给黛玉做衣裳的缎子去了。这话是说给贾母听的,但她不会自己很生硬地说出来,而会在有合适机会的时候不露痕迹地点破。这样的照应,也可看出小说针脚之细密。其次,黛玉进贾府,小说没有像元春省亲那样正面写贾府的准备工作,而是通过王熙凤的话来提示。王熙凤在前面说,贾母对黛玉“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这里则告诉我们,她连给黛玉做衣裳用什么面料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到了,还亲自过问。至于其他方面的准备,自然就可以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