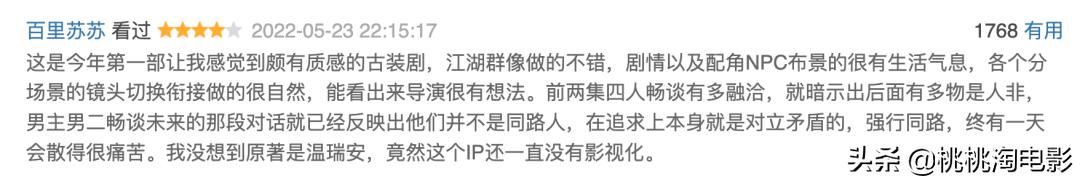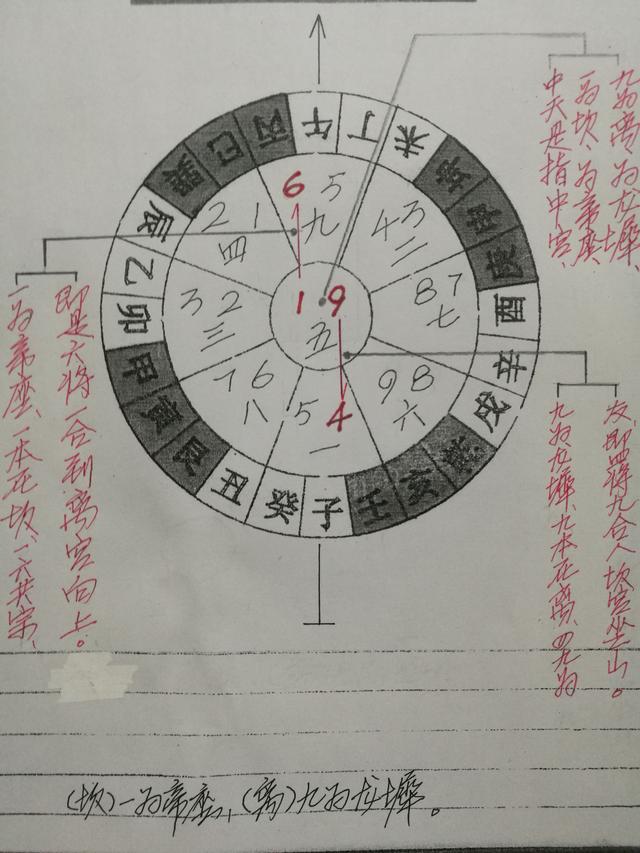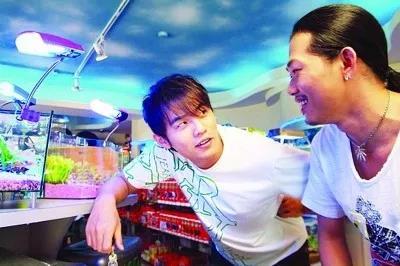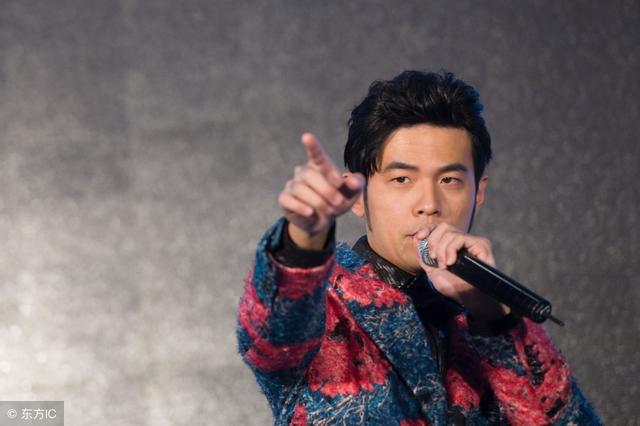佛教发源于印度,公元 1 世纪传入中国。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而迅速盛行起来。南朝梁武帝萧衍甚至把佛教定为国教。

盛行于中国的佛教是经过了一番吸收改造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刚刚传入的佛教神学在许多方面能够补充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但是也与传统思想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因而遭到中国思想界的抵制和反对。为了在中国站得住脚,扩大其影响,佛教经过了自身的改造,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玄学靠拢。大乘佛教空宗的理论,宣扬一切皆空,与玄学贵无论“以无为本”的理论极其相似,两者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而广为流传。当时,为佛教理论中国化做出突出贡献的是道安、慧远和僧肇。

道安是东晋时最博学的佛教学者。在本体论方面,他把佛教所讲的“空”与王弼的玄学贵无论思想统一起来,认为“空为众形之始,故谓本无”,也就是说“空”“无”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他的弟子慧远进一步发挥他的“本无”思想,认为“法性”即“无性”。他用佛教的“缘起”说,说明万物都是由各种“因缘”(条件)暂时凑合而成的,没有独立的本性,所以“有”实际上是“无”。僧肇也是东晋时著名的佛教思想家,他以深厚的玄学功底与佛教经学结合,将有和无、真和空统一起来,提出著名的“不真空论”。

不真空的意思是不真不空,也就是说世间万象“有”但不是“真有”,他们是众多的条件凑合而成的,是“假有”或称作“妙有”。一切事物现象,虽是缘起之“假”,自性为“空”,但却并不是虚无的,荡然无存的,所以,这“空”并不是“真空”,而是“假空”也称为“妙空”。即所谓“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这就是说,空宗关于“空”的理论,并不是简单地否认“有”和“无”的存在,而是说万物是有,但不是真有,假有即空,但不是真空,有是假有,空是妙空。“非有非空”,“不真不空”。有和无、真和空是统一的,都是不真实的存在,因此世界是“空”的。这是印度佛教中观哲学与中国老庄、玄学思想嫁接的成果。他以玄解佛,达到了佛教真谛的精神境界;他以佛补玄,比“本无末有”的思想更为精致。

僧肇还以形而上学的“物不迁论”,割断事物、现象之间的连续性,论证“空”的世界是永恒不变。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般若无知论”,认为对“空”的认识只能用佛教的智慧,“般若”不同于一般人的智慧(惑智),而是一种最高的智慧,称为“真智”,真智之所以最高,在于它是“无知”。僧肇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涉及到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哲学的基本理论,对佛教经学理论有很大影响。

慧远法师针对当时社会上反佛斗争中提出的问题,着重论证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论证佛教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制度之间的一致性,解决外来宗教僧侣的不娶不嫁,对皇帝不行跪礼,与中国传统孝道及封建等级秩序的矛盾。他提出:如果一个人信佛全德,其道德业绩便可影响六亲以至整个天下。这样,他虽没处于王侯的地位,但他的作用已是协助帝王对人民的治理。所以说僧侣出家看起来背离父母的人伦关系,实际上并不失其孝道,虽不行跪礼,其实不失其敬。他说:“释迦之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也。”也就是说,佛教与孔学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理论形式和方法上不同而已。慧远致于二者的调和,合而为一用。

第二个问题是“精神不灭”论。慧远结合中国传统思想,以中国人对佛教理论的特有认识,进一步论证了“神不灭”论,奠定了佛教三世轮回说、因果报应论的基石。

慧远大师
慧远接过东汉桓谭以烛火喻形神的说法,抽去桓谭的唯物主义本质。他认为“神也者,圆而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就是说,神与万物相感应,变化无穷,无所不在,无处不有,而神自身则是“无生”、“无名”、“无形”、“无象”的,因而是非物质的。这种非物质的精神是永恒的,不灭的。他引述中国道家之说,“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来证明他的神是“物化而不灭”的理论。这种不灭的“神”,可以从一个形体转到另一个形体中,就象火从这一束薪到那一束薪一样。他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传之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桓谭最早以烛火关系喻形神关系,意在说明火无烛不能独存,形亡而神灭。慧远仍以此喻,但却说明火可以传于异薪而不灭,形亡而神犹存。慧远在这里以具体的个别的薪与形来对抽象的一般的火与神玩弄了逻辑上的诡辩术。

说某一薪可以有尽时,而火却永远传下去,从而证明精神可以不依赖任何一个不具体的形体而独立存在,永远不灭。他的神不灭论影响很大,加速了佛教的传播。直到南北朝时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范缜,才从理论上驳倒了这一神不灭的唯心主义的形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