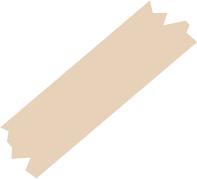父亲告别人世的那个冬季,行将元旦,连日小雨,天气阴沉沉的,学苑路上的紫荆花也开得零落稀疏,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照我衰颜忽落地?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照我衰颜忽落地
父亲告别人世的那个冬季,行将元旦,连日小雨,天气阴沉沉的,学苑路上的紫荆花也开得零落稀疏。
下午四点多,我从寅恪苑旁的紫荆路下山,天空飘着寒凉的雨丝。上午处理了一起刁钻的员工事件,心情郁闷,边走边给老家的父亲打电话,想找一点安慰,父亲电话里精神状态还好,还叮嘱我多跑步锻炼身体。挂了电话,继续往前走,与上山的总裁助理碰头,也不知为何,他突然问我父母还健在吗?我说药罐子支撑著还好,他说他的父母都过世了。然后,彼此各走各的,一上山,一下山,没有再见。
年关将近,老家下了几场雪,天气冷到刺骨。谁料,当天晚上十点多,父亲服下自己熬的中药后,体力不胜药力,猝然与世长辞了,我再也打不通他的电话,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一路风尘仆仆飞机、高铁、公交,到了家门口的路,还是原来的样子,左边种着茱萸,右边是菜地,菜地边上有几棵杨树。地里搭着的瓜架子还没有拆,干枯的藤还缠绕在上面。一时想起那些少年时候的妄言,也终于如云似雾。只是睁眼看见这从容的河山,月落星隐,瓜藤牵缠,还是没有徒然经历一场。“愿你此生有树可依”,也想起这样的祝愿,是从前说给别人听的。
走到门口,舅舅在院子里迎接来往宾客。表哥坐在木凳子上,头上戴着长长的麻布,我们并没有说上一句话,只互相点了下头。在车上时,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眼泪的,但听到邻居说:“你爸爸临走前的几天,一直念叨着你没有成家。”还是忍不住放声哭泣。三个响头,仔细端详着父亲的遗容,想去过往的一切,霎时,眼泪一滴也掉不下来。从灵堂退出来后,舅舅为我戴上孝帕子,这是我第一次戴孝。
母亲和弟弟陆续从辽宁坐车回来了,啼哭的声音,凄惨哀厉。堆红薯的空屋子里放着几匹麻布,吊唁的人陆续到来,家里的女人还在急急忙忙扯孝布,扯孝布有尺寸标准,不同的亲疏关系有不同的规格。有一种说法,孝家戴的帕子拖得越长越好,将来能发大财。这个说法有些滑稽,本来兴旺发达是很值得高兴的事,但寄托在刚死了的亲人身上,让人觉得不悦,如此情理自然的事也染上了人的私心。
窗外的细竹一直没有被斫去,还有窗户上的蜘蛛网,母亲切菜伤了手时,曾捻下来包伤口,说可以止血。现如今还有蜘蛛寄居在那里,辛勤地织网。屋角常年堆着黄皮南瓜,像从来就没吃完过似的。之前屋子里还停过寿材,我记得刷漆的那天家中还请了客、放了鞭炮,寿材上面写了“寿比南山”四个大字,红色的纸张。听说刷漆刷几次也有讲究,总之提到生死,规矩就多起来了,但一到撒手人寰,其他的人又都只能急匆匆的样子,做不到想象中的那样周全。
我和弟弟在父亲身边守灵,看着满堂宾客说说笑笑。桌上大鱼大肉,大家也都吃得很开心。母亲强忍着悲痛招呼客人,收礼,回礼。看着这一切,我和弟弟相对无言,似乎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父亲年纪轻轻地走了,我们都成了孤儿。乡下过世和过寿一样,吹吹打打。眼泪毕竟只是一时的,也只是这样。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这个家里度过的,我所写的关于故乡的文字,大多都和父亲有关。白雪覆盖着青翠的麦苗,但爸爸看不到来年的收成了,他一生守着乡下的土地,最后埋于青山。终究也是个好去处,我只能这样告诉自己。
阴阳仙早看好了坟地,立好了规矩,还是在老坟那里,埋在爷爷的旁边。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我冒黑起床,跟着挖墓坑的人过去,点了火把绕着石灰画好的圈子,转了几圈,开始用扫把扫,接着鞭炮齐鸣,开始动土。可能阴阳仙早念了安土地真言,让地下的神灵早点离开,因为要开挖。
第二天下午落葬,乡下的规矩,要按照阴阳仙算的时辰才好。风水先生做法事:第一开山立向请神。第二破土。第三封棺。第四退煞。第五才是呼龙。最后又是送神,撒五谷。撒五谷,又称接福。阴阳仙撒五谷的时候,让我和弟弟、弟媳、侄子一起敞开衣服接,说接的越多,服气越大。
我走在队伍前面,端着父亲的遗像。弟弟的儿子,才四岁,打着竹幡,小小稚嫩的手,有些撑持不住,还是坚持了下来。现在想起,既可怜父亲的早逝,又心疼弟弟的儿子,那么小,那么懂事,一切都听从大人的摆布。
送葬的那天下午,村子里几乎所有人都来了,还收到了许多花圈。父亲短暂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的乐于助人的故事,所以,他走了,人们乐意送一程。轮到我去的时候,恐怕就没有一个人了,我也早做好了准备,也留下了遗书,以防不测。
记得很小的时候,村里有人过世,父亲还帮忙抬过棺材。今朝我抬人,明朝人抬我,一个村的人似乎就是这样。很远就能听见田埂上哭丧的声音,大多时候并不是人哭的,是请人放哀乐,哭腔很重,听不太懂唱了些什么。自幼我对这些事就很好奇,还曾问过大人,他们告诉我哭丧也很有讲究,什么人请的乐,放的内容就不一样,比如哭爹妈的同哭伯伯伯娘的,唱词是不同的。开棺的时候我没有上前看,听说身体仍旧是浮肿的。封棺时,长子捧灵位,送葬。棺材又叫“方子”,抬方子的叫“八大金刚”,起棺前孝子敬酒礼谢之。媳妇们和亲友跪在后面,一路跪拜相送,媳妇们哭得最厉害。
父亲被葬在代湾,龙王庙旁边,并不是多大的地方。坟地背靠一座不高的丘陵,前有河水,远远就能看着那座笔架山,可惜笔架山的山顶有一点弯,不然我们家真要出文丞相了,阴阳仙略带遗憾地说。坟前河水以往哗哗地流淌,后来改道,现在水小了许多。阴阳仙又说:“如果水大一点,你们家的财就会多。”阴阳仙建议我家开挖河道,引财如室。父亲走后,家里不成样子,不可能再完成这样的工程了。兴许隔了好多世,坟前的河水仍旧如常,昼夜不息,又或许某一天山移河改,一切尽成尘埃。
天上星辰点点,我不禁感叹,在城里再早起来,也闻不到这样的土腥味儿。不远处就是住家户,有人也探头出来看,但没有走上前来。我很想再走前去一点,亲友却提醒我该回去了。隔着青冈树影,看着锄头在挖土,一抔抔落下去。
父亲下葬后,回来时大家心情都缓和了许多,天上疏星点点,月色稀薄。归途不能走原路,换了一条长满杂草的小路,确实有些路已经不认识了,乡里的老人说,年年涨水,冲走了土,山坡就没了。路过许多熟悉的人家,都荒芜了,草深树大,院子里青苔很厚。不知道哪户院子里种了紫薇,一树亭亭,花落结籽,枝梢还是团团的一簇,像是暗色的花球。
如今乡下还时兴给过世的人烧纸钱,我去镇上的钱纸铺看过,袱子都是打印好的,人们买回去自己填写名字、日期。念小学的时候,教室旁边有个老奶奶开了花圈铺,专门做花圈、纸钱、坟飘之类的东西。她手艺非常好,各种纸花,被他巧妙地变出来并黏贴竹片上,做成花圈。还记得花圈上彩色的纸花是要用糨糊一点点黏到白色的花圈上的,一个花圈也要费时许久。小时候不认识“奠”字,还是在铺子里学会写的。糨糊刚做出来时还挺好闻,放了一天后就有一股馊味,铺子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剩下的糨糊,我对那个味道记忆尤深。钱纸上的花纹,是用一种特有的机器压出来的,但并不太记得机器具体的样子。
花圈铺屋后有一棵很大的重瓣木芙蓉。教室另一边还有铁匠铺,里面主要是卖菜刀、镰刀、弯刀,门口一直放着一块磨刀石,月牙形的,被磨得锃亮,打铁的时候格外热闹。
现在丧葬的业务也和以前不一样。以前花圈铺主要负责卖一些丧葬用品,而这几年流行起一条龙服务,就是从死者过世,到超度法事和入殓,铺子里可以一手代办,不过费用很高。做这个行业其实并不容易,敲打唱念、写写画画,都是一整套的手艺,每个人做出来水平也不一样。故乡称这部分人为“道士先生”,这些人的手艺有很严格的师承来历,也有一个固定的圈子,还分了佛、道两派,从丧礼的形制上可以区分出来。
上次回乡时,我特意去学校附近走了走,以前那些铺子早就关了。花圈铺易主多年,土墙上用白色粉笔写了“花圈铺”三个字还留在那里。门口堆了许多干柴,还有一两袋化肥,小孩子们在空地上玩耍。那样破旧的房子,什么人家还住着呢?我透过门缝看木芙蓉还在,只是被砍得小小的,和以前的汪洋恣肆判若两物。
他日故人能忆我,青衣云履埋枯骨。想起从前写过的句子,今时看来,内心已经不觉得可惜,只有更多的决然。青山遥相望,每个人的生命各有轨迹,实在强求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