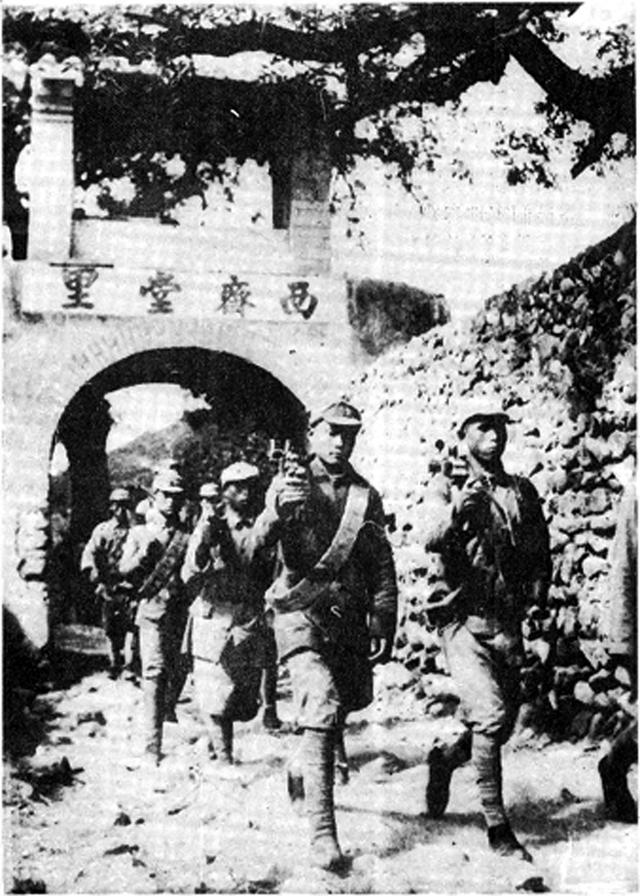作者法律读库原创部落成员李永红,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律师学院执行院长。法律读库投稿邮箱:1751490@qq.com。
尽管儒家传统主张息事宁人、中庸和谐,民间更是认为“屈死不告状”、忍辱负重是美德,但是,利益之争仍然时时发生、处处难免,人们活着的时候争权夺利,就是死了,他们的后人还要争墓地。因此有人认为“厌讼”并非儒家文明的传统。
据报道,奉行儒家文化、实行中华法系的韩国,一处墓地之争竟然持续了近400年,还导致100多万人不得通婚。尹、沈两大家族从1614年就开始争夺汉城(现名首尔)以北约40公里处的一座小山,因为这两大家族都断定,这座山是“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宝地”,把该山作为自家的墓地能泽被子孙、恩及未来,因此均说拥有它的所有权。他们一面把家族显赫成员葬在山上,一面告对方破坏自己祖先墓地,进而演变为家族世仇。两大家族墓地争夺案曾令多代韩国王室头疼不已,直到2007年尹氏、沈氏两大家族才达成和解,同意由尹氏向沈氏提供8300平方米土地,作为沈氏19位先人新的安息场所。这宗墓地争夺案不仅未能惠及子孙,反而令韩国姓尹者100万人和姓沈者25万人无法通婚,如果有子孙擅自通婚,两姓有情人是得不到长辈祝福的。
民间喜欢争执,而官方却一厢情愿地追求无讼。为了无讼,历代官府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散见中国各地的六尺巷便是古代官员奉行德治、息诉罢讼的产物;到了当代,在司改之前十几年间,在民间,“信访不信法”,于官场,司法日益边缘化,纠纷日见尖锐,非但不以法治界分权利以定分止争,反而鼓励“不按法理出牌”,使社会大众与官府法曹均无所适从。
曾听闻一则基层官员了断墓地争议的故事。某镇两个家族为一墓地归属产生争执,影响社会稳定。因事起年代久远,历届官员均无可奈何。某日,新任镇长听说此事,便亲往调解。镇长约当事人到场,并告知双方自己绝对保持中立,会不偏不倚地公平裁决,希望双方能够接受其处理方案,双方均表同意。
镇长问:墓地有何用处?
双方均答:先人安息之用。
镇长说:既然双方先人均已在此安葬,他们都无意见,生者却如此吵闹,他们何以安息?既然墓地用于安葬往生之人,双方目前均无人死亡,争执何益?
双方答:人总会去的,墓地面积有限,恐今后逝者再无地方葬入祖坟。
镇长问:本镇体谅双方的心情。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排队是否最公平的方案?
双方答:是。
镇长说:本镇认为,依排队方案,先到先得是最基本的规则。双方最先死人的一方获得墓园空地的使用权。可否?
双方异口同声:那墓地就给对方吧!
众人散去。
镇长非常清楚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利益(法言曰权利),生命当然是高于土地财产的利益,得到较小的利益(土地),须以失去较大的利益(生命)为先决条件。任何争权夺利之人都知道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因为没有哪一方会为了得到墓地而愿意先行死去。假如获得了争执的土地,则等于已方必定先死一人。谁愿意承受这个比诅咒还要恶毒的状况呢?
无独有偶。
据说,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为宅基地起了争执,因时间久远,谁也难以证明归属,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肯相让。因事涉宰相,官府不愿沾惹是非,于是纠纷越闹越大。张家只好把这件事告诉张英。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张英大人阅过来信,只是释然一笑,挥起大笔,作打油诗一首,曰:“千里传书只为墙,让人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虽败兴而归,但仔细思量只能退让。遂将院墙拆让三尺,得到街坊交口称赞。宰相家的忍让反倒令邻居吴家深感惭愧,于是也把围墙向后退了三尺。两家争端平息,便留下六尺宽的巷子。
无论是墓地之争的化解,还是六尺巷的形成,固然显示了主政者的实践智慧,而在历史学者黄仁宇看来,却也正是中国社会难以现代化的一个原因:人们耻于对自己的权利实行精确的数目字管理,法治失去了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