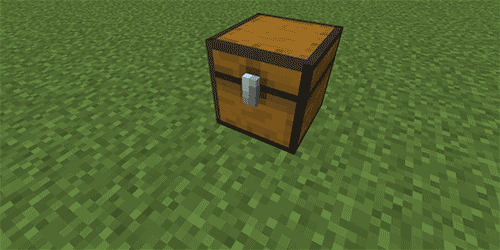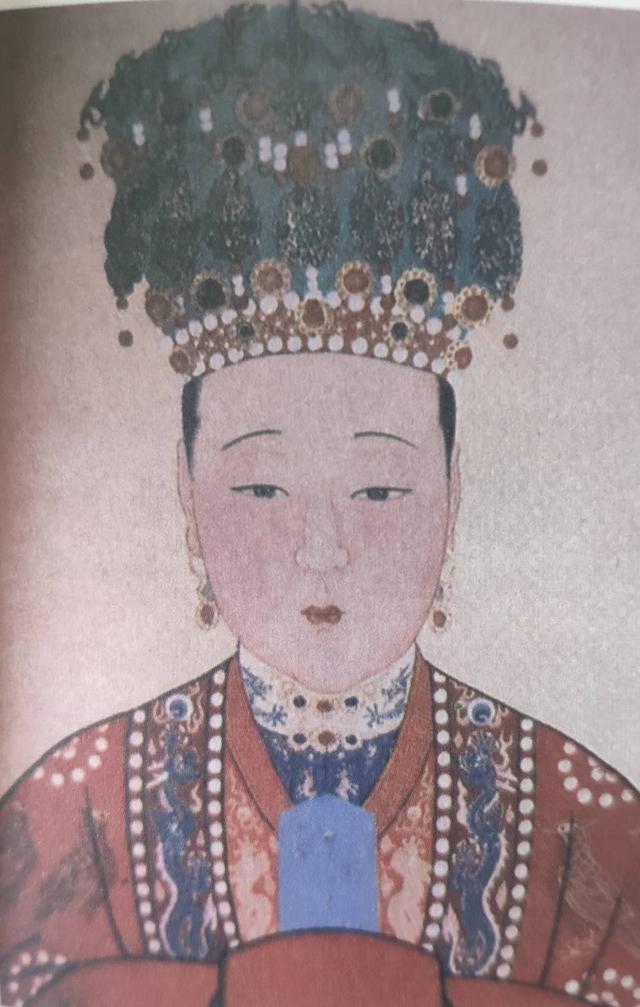从历史上看,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股市是自1929年大危机之后最好的十年。道琼斯指数几乎升至原来的3倍,从235点涨到679点。与此同时,那些精心挑选的股票表现更佳。1949年投资到标普500指数上的每1万美元资金,到1959年可以上升到6.7万美元,年化回报达到异乎寻常的21.1%。这个无与伦比的纪录,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
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的股市表现是令人沮丧的,始终是上上下下起伏不定,每一次上升都会被扼杀。但是,在整个50年代,牛市却是持久不衰,买进股票、持有股票这样的行为,又恢复了先前的好名声。在这样的牛市中,即便遇到市场回调,也只是暂时的。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令投资者惊慌失措,但“市场先生”的损失很快就得到补偿。同样,1957年发生的各类事件,诸如苏伊士运河问题的争吵、苏联将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以及成功发射人造卫星进入太空轨道等,都会引发短暂的恐慌。两次下跌都伴随着经济的短期衰退,但这两次经济都轻松复原了。公司的利润在增长、股票的市盈率在膨胀,投资的游戏可以轻松取胜。
在应该持有股票的最佳时候,人们却常常避而远之,这是大众对于股市的典型行为方式。在30年代,股价达到数字上的底部之时,人们花了更长的时间才达到心理的底部。进入50年代,大众继续对是否应该持有股票这个问题保持着首鼠两端、狐疑不决的态度,这考验着人们的智慧。
毫无疑问,1950年的股价极其低廉,道琼斯指数还没有超越1929年的高点。除了个别公司(例如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克莱斯勒等),平均而言,蓝筹股依然深陷长期衰退之中,毫无起色。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的股价比“柯立芝繁荣”时期还要低。阿纳康达铜业公司和RCA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价大跌了50%。著名的财经杂志《巴伦》在1952年的一期中选出全美50家杰出的公司,其中有35家在股市上是长期输家。整整一代人在对牛市的期待中老去。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拥有股票是为了获得分红,而不是差价。与此同时,税务当局还在进行着不厚道的瓜分:最高税阶的税率达到收入的80%。这时,共同基金的倡导者约翰·邓普顿建议客户可以买那些快速增长的公司的股票,这类公司通常仅支付很少的分红或者根本没有分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规避沉重的税负。他建议,当投资者需要用钱时,可以卖出一些股票,资本利得的税率会低很多。邓普顿的观点——把股票当作收入来源——并没有得到大众的广泛响应。
20世纪50年代初期,股市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弹,戴维斯借此晋身百万富翁之列,但即便如此,大众还是疑虑重重。1954年出版的《财富》杂志反映了这种心态,它的封面文章是《华尔街已经过时了吗?》。此时,美国的企业生意兴隆,但股票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令人昏昏欲睡。每100个美国人中,仅有4个人持有股票。
纽约证券交易所里依旧保持着30年代中期以来像牛皮糖一样没精打采、不死不活的走势,每天的交易量仅有100万股。操盘手、券商、承销商都对大众的默然以对感到茫然无措。为了打破这种毫无生气的僵局,纽交所发起了一场时髦的推广活动,主题是“在美国经济中拥有自己的一份”。
纽交所总裁G.基思·芬斯顿(他曾经将自家的夏季度假小屋租给戴维斯一家)发起了一场活动,鼓动未持股的中产阶级参与投资。小投资者们被邀请,可以分期付款购买股票,这种付款方式就像他们买车、买家具、买电器时的分期付款一样。尽管开始之初纽交所称这场活动“大有希望”,但最后仅有2.8万人参与了这场“先投资,后付款”的活动。在活动的第一年中,仅仅吸引了1150万美元的新投资资金。
结果证明大众并不认为会有什么牛市,人们缺乏购买的热情,进一步导致持股者也同样缺乏卖股的热情。卖的人越少,股价向下的压力就越小,因此,相对少的买盘即可推升股价。
尽管经济的繁荣开始渐渐减轻人们对于萧条的担心,但通货膨胀的警示灯开始闪烁。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结束后,通货膨胀如期降临。一如既往,大幅的军费开支由过度活跃的印钞机解决。1950—1951年,CPI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美联储以提高短期利率的经典方式作为治疗通胀的手段。但这种治疗手段具有习惯性的副作用——经济的温和衰退,就像之前提到的情形一样。
长期债券恶化崩溃的开端1951年,美联储放开了它数年以来紧紧压在长期国债利率上的盖子。从管制的束缚下释放出来,长期利率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飙涨。极少有人意识到这是长期债券恶化崩溃的开端。实际上,1957年的股票熊市再次将投资者拉回到“安全”的债券上。
1929年以后,为了遏制那些狡猾的股票投机者,当局制定了严格的新政策,例如,不允许以10%的定金购买股票。但是,对于那些狡猾的债券投机者,当局却没有什么制约政策出台,他们甚至可以以5%的定金购买债券。1957年,那些债券市场的大户、中户们饶有兴致地玩着赌博游戏,他们用银行贷款去抢购那些最新发行的政府债券。为了满足市场这些大胃口的需求,财政部发行了17亿美元新债,到期日为1990年,年息为3.5%。留意到这批债券直至1990年到期这一特点,华尔街爱开玩笑的人将它们称为“无拘无束的90”。
“人们为了购买这些债券而排起了长队,”詹姆斯·格兰特在描述“无拘无束的90”债券时这样写道。但是,没有多久,债券市场沉没了。如果债券买家没有使用融资杠杆,那么损失或许不会如此惨烈,但是,猖獗的投机行为造成了债券价格巨幅下跌。在投机者损失殆尽后不久,美联储的应对方案(提高短期利率)平息了通货膨胀,恢复了债券交易市场的平静。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通胀率维持在2%上下的水平。
戴维斯双击以及三重获利戴维斯并不太关心债券的上上下下,他专注于保险股票,特别是那些小型、进取类型的保险公司股票。到1957年,在他自己创业七年之后,终于跻身富人行列。市场中的每一个板块都有利可图、令人垂涎,但戴维斯摘取的是最为甜美、最少人关注的果实。没有声张的喧哗,保险公司的利润增长速度极其惊人,就像日后的电脑、数据处理、医药公司以及著名的零售商例如麦当劳、沃尔玛一样。
数字可以让人更具灵感:1950年,保险公司的市盈率仅有4倍。十年之后,它们的市盈率达到了15~20倍,而且它们的盈利增长到原来的4倍。让我们假设,戴维斯以4000美元持有1000股美国保险公司股票(这是一个虚构的假设),此时,每股盈利为1美元。他一直持有该股,直到每股盈利为8美元,这时人们会蜂拥而来,涌向如此优异的机会。这样,当年戴维斯以4倍市盈率购买的每股盈利1美元的股票,此时市场出价为18倍市盈率,每股盈利8美元,18倍市盈率的价格是144美元。戴维斯当初的4000美元投资,现在市场先生给出的估价是144000美元。折算成利润,戴维斯获利36倍,外加持股期间他信箱里收到的分红支票。戴维斯将这种有利可图的转化称为“戴维斯双击”。当一家公司利润提升,推动股票价格上涨,投资者赋予该股更高估值,推动股价再次上涨。由于融资杠杆的运用,戴维斯甚至从中实现了三重获利。
戴维斯从来没有借钱消费的行为。对他而言,如果借钱购买一辆新车或冰箱,简直是对金钱的侮辱。但他热衷于通过借钱去赚更多的钱。与制造商相比,保险公司具有一些无与伦比的优势。保险商提供的产品永无过时之说;它们的利润来源于用客户的钱进行的投资;它们无需造价昂贵的工厂设备和研究实验室;它们也不会污染环境;它们还具有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在世事艰难的时候,消费者会延迟对贵重物品(房屋、汽车、电器等)的消费,但是,人们却无法承受让自己的房屋保险、汽车保险、人寿保险失效。当艰苦的经济环境迫使人们更加节约时,人们会更少开车,这样就会减少汽车事故,索赔也就更少,如此一来,汽车保险商也会从中受益。经济萧条时期,利率会降低,这导致保险公司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价值上升。
这些因素将保险公司的盈利状况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周期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其可以抗御周期性经济衰退的能力。同时,以持有债券为主的投资组合仍在持续不断的增值中。
戴维斯购买保险股并非一视同仁,不加区别。在他并不算太长的政府监管生涯中,他开发出一套自己的方法,以区分赢家和输家。1952年,他曾经在纽约保险经纪协会的演讲中描述过这种方法。他演讲的主题是:“你的保险商有多健康?”在字里行间,听众们可以得到如何挑选股票的真知灼见。
首先,他以数字来说明如何发现“一家公司是赚钱机器、财源滚滚,还是捉襟见肘、经济拮据”。这需要了解业内一些广泛使用的会计手法。一旦确定一家公司是盈利的,他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公司资产赖以取得复利增长的投资组合上。在这里,他将可靠的资产(例如政府债券、按揭、蓝筹股等)与前途未卜的资产分离开来。他曾经打算投资一家具有明显吸引力的保险公司,但当他发现该公司的投资组合中满是垃圾债券时连忙收手。不久之后,由于一些高风险的垃圾债券违约,这家保险公司倒闭。戴维斯与其擦肩而过,毫发无损。
之后,戴维斯对于出现的机会采取非公开市场的估值方法进行大致的评估。换言之,如果一家大公司决定收购该标的时会出什么价格?对于戴维斯而言,他想买的保险公司的股票在他心中的估值必须远远大于市场给出的价格。能为公司贴上自己的价格标签,这给了戴维斯信心和耐心。
心中有底对自己的持股价值心中无底的投资者,股市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惊慌失措,逃之夭夭。他们衡量价值的唯一指标就是股价,所以,股价越是下跌,他们就越是倾向于卖出。戴维斯具有一种“恐慌免疫”特质。华尔街行情每天、每周、每月以及每年的上上下下、跌宕起伏,都不会让他改变既定的策略。即便在市场崩溃、士气低落的大跌中,他依然坚定地持有自己的股票,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投资组合的真正价值被市场错估。熊市无法令其恐惧,因为他心中有底。
股票价格的波动是戴维斯所关注的指标中最不重要的指标,但他依然会留意报价单。如果一家公司的股价陷于“长期的下跌之中”,对他而言,这或许意味着其背后有不为人知的麻烦,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知晓内幕消息的人在抛售手中的股票。“这可能意味着,就像他们曾经提到的《老人河》中的歌词那样,”戴维斯对听众说,“有些人‘一定知道一些事’,因此,它不会‘静静地流淌’。”
在戴维斯充分了解了一家公司的财务数字后,他会将注意力转向管理层。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会与管理层会晤,询问CEO有关公司的每一个方面,从销售队伍到理赔部门,再到公司如何抵御竞争对手,以及赢得新客户的策略等各个方面。
即便对一家公司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也未必总是可以发现公司存在的致命缺点。为了说明这一点,戴维斯举了一个在朝鲜战争中成为牺牲品的著名汽车保险公司的例子。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整个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鲁莽驾驶风潮”,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爆发,这一切都使得汽车的维修和处理意外事故索赔变得更为昂贵。由于当初肆无忌惮、不加选择地承保,现在保险公司遭受着双重打击,屡屡现身破产法庭。谁还顾得上道德良心?持有足够多的保险类股票,使你遇见不愉快的惊吓远远多于愉快的惊喜。
多元性格的戴维斯戴维斯是个具有多元性格的人。他特立独行,喜欢结交名流。他与普通大众亲密无间,但同时,他又是根深蒂固的亲英派,花大量时间研究家中的“黑皮书”家谱,他陶醉于自己与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之间存在基因关系。他曾加入一系列的爱国组织:殖民战争协会、美国革命之子协会、朝圣者协会、五月花协会。他还设法成为辛辛那提之子协会的成员,虽然他并不符合基本的要求:因为他不是乔治·华盛顿将军麾下军人的嫡子后裔。
在华尔街,他培养分析师,了解他们的观点,但不会妄加评论,不会强加于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避免跟风,不会理会大众的想法,但当他的公司的经纪业务和承销业务无人问津时,他也会发脾气。他在教育孩子方面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人,以事例教育他们保持道德操守和遵纪守法。他不允许在办公室里闲扯,也会斥责员工为什么不在家里读报而在办公室里读报。他不会赌咒发誓,不讲也不喜欢听黄段子。但他喜欢参加聚会、庆典、晚餐会以及男兵休息室里的趣谈。
他不会穿着奇装异服,但如果穿上燕尾服,戴上三角帽,系上绶带,胸前配上勋章,举着旗帜,参与他参加的那些组织举行的爱国游行,他会满心欢喜。他在每一个所参加的组织中都跻身最高层。除了偶尔的男女共同出席的晚餐舞会,所有的聚会参与者一般都是男性。一次,戴维斯去伦敦参加一次朝圣者协会的活动,发现忘带了礼仪绶带。凯瑟琳在伦敦各家商店里寻找,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一条替代品。
此时,戴维斯已经在保险界声名鹊起,业内已经有人将其称为“美国保险业主任”,尽管他从未在任何一家保险公司中供职。他是一个活的名片簿,或行业名人录;他是一本保险业的年鉴,无论公司规模大小;他是一本保险精算的百科全书;他是一个关于利润、资产和负债的数据库;他还可以充当满是注脚和出处的附录,他可以回忆起很多名字和面孔。他精于数字,但不仅仅依靠数字来挑选股票。“你可以把会计当作兼职来学习,”戴维斯告诉自己的儿子,“但你必须学习历史。历史会给你更宽广的视野,并教会你,与众不同的人会成就与众不同的事业。”
戴维斯的邮箱里总是源源不断地涌进邀请函:参加行业仪式、在大会上发言、参与CEO年度的国内外交流活动。他的办公室经理兼小合伙人肯·艾比特经常是通过电话知道老板在什么地方,他的老板或是在苏黎世,或是在巴黎、罗马、伦敦,每当一场演讲结束,就会有电话打给肯,想买戴维斯在演讲中提到的那些股票。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演讲,这位“保险业主任”都会吸引大批听众。华尔街的投资公司也会派人到现场去,并在问答环节问一些选股的问题。戴维斯很享受这种被关注的感觉。
有时候,当戴维斯在外交流时凯瑟琳会去旅行。1953年,她和妈妈伊迪丝去了印度。这两位沃瑟曼家族的女人有幸与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他大吉岭的家中一起饮茶,当时希拉里爵士刚从珠穆朗玛峰登顶回来不久。凯瑟琳回忆道,希拉里爵士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全美式厨房,厨房里有魔幻烤炉和冷藏柜,那是印度政府给予他的奖励。凯瑟琳的妈妈坐在院子里,没有进入厨房参观,因为她害怕希拉里爵士家的狗。
登山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很多新的皈依者,其中包括凯瑟琳的侄子斯蒂夫·沃瑟曼。15岁时,斯蒂夫就登上了法国阿尔卑斯山。两年之后的1957年,他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一展身手。他和一位朋友在一个矿区工作,以此谋生(斯蒂夫的爸爸狂野比尔拥有这个矿区的部分股份)。工作之余,他经常爬山。一个周末,在攀登险峻的惠特尼山东面山坡时,斯蒂夫不幸坠山而亡。
在西弗吉尼亚的华丽的绿蔷薇度假村,戴维斯和凯瑟琳曾经出席过保险界的年会。这样的活动通常是业内的,拒绝外界人士参与,尽管戴维斯不能参加正式的会议,但他被邀请参加餐会和庆祝活动。他倾听业界趣闻轶事,获知业内的人事变动,会见新任的管理层,判断他们是实干家还是空谈者。他在年会上往来,就像一名记者,抢在华尔街之前获得独家消息。
增值32倍尽管戴维斯社会关系广泛,并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但他的公司的经纪业务却不是很景气,很少吸引到新客户。人们总是在听了他的投资见解之后通过别的券商下单买卖,对此,戴维斯一直很郁闷。他认为采纳了他的投资建议的人,如果不从他的经纪席位下单,就欠了他一份佣金,是缺乏尊敬的表现。
他的公司做股票承销工作,也就是帮助保险公司上市,但是戴维斯在这些交易中,由于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资金,无法承担主承销商的角色。所以,他不得不与摩根士丹利以及其他大的投资银行合作。在报纸上关于最新消息的“墓碑”式广告中,这些大银行经常出现在顶端,而戴维斯的公司名字常常只能出现在这些“墓碑”式广告的底部,偶尔他的公司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墓碑的右侧,那是次级主承销商的位置。
他在6个城市成立了小型办公室(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位雇员)。他几乎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只是希望雇员们自己能赚到足够的钱,覆盖办公成本并养活自己。他的这种打了折扣的经纪业务勉强度日。实际上,他的公司很像保险公司,以销售收入支付每月的费用成本,而真正的利润来自投资组合。公司业务的不活跃反而让他能专心于自己的投资。
通过持有保险公司股票的方式,戴维斯使自己的身价远远超出那些保险公司的高薪管理阶层。20世纪50年代,他的资产净值飙升。他在32家保险公司中的投资价值160万美元。这样,凯瑟琳当初的5万美元已经增值了32倍。
那些投资组合中最初的名字已经消失不见了,历经6年的摸索,戴维斯发现了一些令人满意的、可以长时间持股的公司:大陆公司、联邦人寿等。从那时起,他便牢牢持有这些股票。随着资产价值的上升,他会得到更多的融资额度,他会用这些借来的钱投资新的股票。到了1959年,他的融资杠杆为800万美元,因此,他的净资产可能在800万~1000万美元。
大约在这段时间,戴维斯遇见了一位奥地利朋友——迪克·默里。默里向他介绍了再保险业务(再保险是指一家保险公司支付给另一家保险公司一些费用,用以分担部分风险的行为)。为了降低未来发生的灾难带来的巨大风险,例如飓风、地震以及类似的重大灾难,欧洲的保险公司会支付一些钱给再保险公司。默里将再保险的概念带入美国,他和戴维斯经常在戴维斯喜欢的俱乐部——城市中心协会一起吃午餐。当戴维斯邀请默里到他缅因州的夏季居所时,默里忽然发现他在与一只铁公鸡打交道。
“两间客房,共用一个卫生间,”默里回忆道,“你必须敲门,看看里面是否有人。有一次,我在里面,一位住在另一间客房的女士来敲门,于是我大声喊道:‘如果你需要热水的话,就不用想了,这里的水槽已经坏了三年了。你试一下浴缸里的水管吧。’”
返回纽约之后,默里安排戴维斯会见一位法国保险公司的CEO,这家公司计划在纽交所上市。“我们三个人在戴维斯位于松树街的一间办公室里交谈,”默里说,“戴维斯坐在办公室中央的办公桌前,他的几名员工忙前忙后,毫无隐私可言,交流难以正常进行。法国人和我都注意到了戴维斯的旧皮鞋。后来,法国人给戴维斯一些建议:‘在办公室放置隔板。在办公室谈事时,还是买一双新皮鞋为好。’”
在每一次交谈中,戴维斯都会追问默里有关再保险的问题。默里向他提到了数家大有希望的杰出的外国保险公司,这使得戴维斯有了投资海外的想法。“一个哲学的信徒”对于赚大钱并无兴趣,默里总是给别人推荐股票,自己却从来没有买过股票。
自从戴维斯开始自己投资,之后11年,他从股票上获得的股息远远高于从政府债券上获得的利息。整个20世纪,在任何时候,只要股息超越债券利息的时候,持股者都会获益匪浅。
195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股市牛气冲天,债券收益一度追上股市分红。道琼斯成分股的市盈率达到18倍,已经达到当时较高的状态。10年来的牛市渐渐将那些股市怀疑论者转变为股市的忠实信徒。经济复苏的曙光非常明显。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 T&T)的退休基金自1913年以来首次购买股票。知名投行莱曼兄弟公司新发行的公募基金,一经推出就被一抢而光,远远超出预期。股价越是上升,大众越是抢购。尽管坏消息时有发生,无论利率在上升,还是中东面临战争威胁等,股市热情依旧。评论家们将这一股市上升现象比喻为“印度神仙索”魔术,认为股市的上升并无明显利好支持。
《生活》杂志的记者欧内斯特·哈费曼撰写的报道反映了1958年发生的这一令人好奇的现象。文章的题目为《人民的股市:乐观及不可预料的购买让华尔街的专家们大惑不解》。“我们今天生活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哈费曼写道。他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无知无畏的投资者如何用融资杠杆去赌博,也提到50年代的投资者“常常像购买保险或日常存款一样购买股票。投资者身处一个长期的牛市之中,短暂的股市回撤无法打击他们的信心”。
随着牛市的再次降临,大众开始重新转而买股、持股,股市老手们对这种突然的转变并不意外,他们曾经见过熊市如何在一夜之间将那些所谓的长期投资者变为恐慌的抛售者。但相较于狂飙突进的20年代,哈费曼将50年代描述为一个开明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公司以及股东们会从企业管理的新兴“科学”中受益。除此之外,他说,华尔街也变得更加保守,监管更严,在与个人投资者交易时也变得更诚实。“买家当心”这样的警示已经过时了。
然而,在繁荣的表面之下危机四伏。当美国繁荣时,它的消费者已经累积了惊人的贸易赤字,美国消费者购买的外国货物超出了外国消费者购买美国的货物。通常,美国以美元作为支付手段与贸易伙伴交易,但是,英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开始质疑美元是否能维持其价值稳定。于是,他们要求美国以黄金支付,基于已经修改的金本位制依然有效,美国不得不遵守执行。曾经,美国政府手中的黄金比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多,但是到50年代末,黄金被大量运往国外,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
经济预言家和货币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很快就不得不调高黄金的价格,这样就可以用更少的黄金解决其债务问题。黄金价格更高会令美元自动贬值,因为需要更多的美元换得一盎司的黄金。让国外商品变得更贵,便宜的美元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胀高企对于股市和经济都是坏消息,但这个糟糕的结果一直到1971年才发生,当时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正式宣布美元贬值,于是黄金再次耀武扬威。詹姆斯·格兰特在谈论50年代的贸易赤字时说:“货币号飞机的确是飞进了山区,但是飞行员的计算错误并不严重,因此在数年之间不会发生撞机事件。”金融剧变的冰山移动缓慢,一场未来爆发的灾难往往距离最初埋下的祸因已经过去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