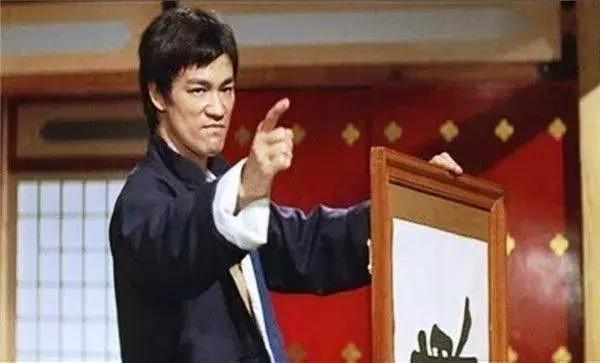文 / 采访 顾北
“我希望这部电影不要发生什么,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同时,又什么都发生了。”在接受猫眼电影专访的时候,《八月》导演张大磊如是说。而现实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金马奖以黑马之势夺得最佳影片后,《八月》以3%的低排片率平静的上映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什么都发生了。
电影厂长大的童年:反复看的老电影《八月》与其说是根据导演的个人经历改编,张大磊觉得更重要的是那种感觉,“这个电影更多的并不是说某一个情节,某一个事件会怎么样,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整个电影散发出来的那个整体的感觉,那是我似曾相识的。”
张大磊的父亲是一位电影剪辑师,从小在电影厂长大的他也分享了成长经历,“小时候经常看电影,各种各样的都有,那时候其实电影种类没有现在那么丰富和完整,跟体制有关系,那时候是电影厂制度,国家有配额,每年完成几部影片,而且都是由国家的那叫电影公司吧,统一租售和管理的。具体的不太清楚,但不像现在有自由的竞争,进入市场,所以看到的就是那些,反复在放,甚至是不分新旧的,只要没看过的都是新的。《八月》里面有讲到94年的第一部引进片,在那之前各种片都有,都是老片子,包括九十年代大批的城市电影,都特别优秀。”

中国第一部引进片《亡命天涯》
九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在张大磊看来更为开放,大家都在追求新的东西,“那时候电影厂也不一定就是一个绝对的文化单位,比如说我父亲在入厂之前就不是做这个的,他们那时候全是分配。所以说电影厂里是从全国,都有很多外地人,从全国四面八方分来的人,进入到这个厂子里的。但是我觉得文化氛围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共有的,就是一些新的文化思潮,或者是新的文化现象出现,新的音乐,然后包括时尚的东西,都出现了。当时人们就普遍都在追求新的东西,美的东西,很理想化的去追求。可能是电影制片厂就稍微集中一点吧,这样的人多一些,或者是外面的人也会到这里来找他们的朋友。所以就看到的比较多,看电影我们又不花钱,所以经常会看。包括音乐啦也是,我们家我父亲的朋友或者同事经常会……那时候分享文化,分享美,分享艺术,当时是这样的,大家会在一起聊,这也是一种形式。比如录像带、磁带,大家要翻录,肯定要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就要聊。这一点他肯定也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大的问题是自己对想要的东西不够清晰08年开始想要拍这样一部电影,12年完成剧本,15年开拍,这中间其实是张大磊不断确认自己想要的电影的过程。“剧本的完成,就实际完成的工作是12年,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很快。一个月时间写出了第一稿,但从12年到15年这之间其实一直在修改。”
在拍摄完成之后剪出的首个版本是一个6小时的版本,张大磊直言那个版本令人失望,“我父亲第一次看不是这个版本,他第一次看是我粗剪的那个,六小时的版本,但是那个特别不成形,而且是看了挺让人失望的。毕竟是素材,只是单纯的按照剧本,按照我拍摄的顺序,把它拼接到了一起。还谈不上结构,或者说没有样子。后来就是一点点的做减法,直到这个电影该有的样子,或者是我想要的样子出现为止。”

谈到拍摄期间遇到的困难,“外部来看肯定是资金的问题,因为电影要实现的话,肯定要有这个资金做保证。但是我后来细想,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对自己要什么还没有很清晰,只是直觉上有个感觉,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电影,但是具体呈现在剧本里,或者是整理出来的时候可能还不够准确。中间经历了慢慢不断的优化和改善,最终是在剪辑的时候(我才清晰的明白自己要什么),我剪辑花了大量的时间,将近三个月。我自己在家,拿笔记本一点点剪出来。”
取景地就选在了张大磊的家乡呼和浩特,他平时就喜欢去这些老建筑附近待着。“我对这种老的小区,对那个环境,对还是以那种方式生活的人,我有一种亲切感,有好感。我经常会去的,并不是说因为电影去找。就是为了自己,我经常在那些地方。所以不用挑,但是这些老建筑越来越少了,拆除的速度非常快。”
非职业演员的表演:这部电影没有超出生活的范围对于演员的敲定,张大磊表示,“不用找,都是朋友。他们信任我,他们也知道我一直在做什么事情,而且大家来也不单单是觉得要演戏,更多的心态是要帮助我把这事做完。演小雷的那个小男孩,他是纯天然的,我在选择孩子的时候,也选择了好多,但最后确定了是孔维一,他本人很像小雷,他本人某种程度上他就是小雷,所以就是没必要让他过度的改变自己。”

而对于如何让这些非职业演员做出自然的表演,张大磊认为这得益于生活经验,“这部电影讲的故事没有超出生活的范围,所以大家都不陌生其实,他们可能最大的努力是适应,适应拍戏。最多的工作是这个,适应拍戏。然后就把每一个人对生活的经验展示给我,就可以了。”
而对于这些朋友以后会不会想要走职业演员的路,张大磊则觉得这是非常随性的,“我们其实除了是朋友的这个关系之外,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好像我们都,包括我也一样,并没有一定要做什么,或者一定要成为什么,一切都是,可能也没有什么计划。一切都是觉得是对的,是喜欢做的就可以了。”
《八月》是我的一个梦境,虽然用了写实的风格“写实是风格其实,就是我们定义的写实主义、或者科幻、超现实,其实他是电影风格或者说是表现手法,是在这个层面上定义的,因为我们片子里面没有科幻的,全是真的,所以他是一部写实的影片。而从气质上说,我们并没有拘泥于事件,或者拘泥于故事,而是把一个特别强烈的,或者作者的主观感觉上的一个感觉通过电影传递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气质,梦可能是他的气质。也是我想要说的。
每个人对梦的定义和感受不一样,可能梦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噩梦或者是不好的那些梦我不愿意记得。我愿意记得的梦都是美好的,甚至是荒诞的,因为它没有逻辑线,它是跳跃式的,这个是非常有魅力的一种体验。所以我的电影我希望也是这样,就是有亲切感,但是不可能得到真相。

黑白的选择也是基于这个,因为现实都是彩色的,梦境可能,虽然说梦里面也是彩色的,但是我觉得它跟我们现实是有差距的,它可能更像是黑白的,是光和影呈现的。所以这部电影拍成黑白的,是希望跟现实生活保持距离感,而且黑白的气质会更符合我想要的梦境也好,或者是简单的语言来诉说。最后DV拍摄的片场片段,影片又回到了彩色的,那段相当于回归到现实,代表着梦醒了。孩子的梦醒了,我的梦醒了,或者是父亲他们的梦醒了。现实是其实要去做事情的。”
《出租车司机》是我最喜欢的美国电影谈到《八月》中反复出现《出租车司机》这部电影时,张大磊表示,“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喜爱的美国电影。《出租车司机》应该是第一位,最喜欢的。我个人美国电影看得比较少。”

获得金马奖对张大磊来说,意味着他可以继续拍电影了,而接下来的项目,张大磊表示的都还不确定,“都有可能,没准。接下来有两个项目,有一个跟《八月》风格类似,另一个则有一些变化。还是更倾向于作者电影。”
“拍电影这件事本身,是没有带着功利心的,只是觉得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