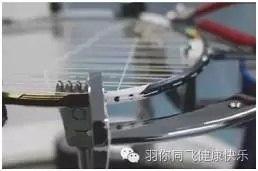文/高金业
一
那一阵,部队对生产抓得挺紧。邵科长说,高,咱也搞点生产吧,为食堂提供点方便。我说,咱搞点什么呢?邵科长说,是啊!搞点什么呢?想想,再想想!
过了几天,邵科长说,我想来想去,还是先干起来再说,先做豆腐、生豆芽。有个从东北刚调过来的许师傅,说他干过这个活,可以让他负责这个事。
许师傅是山东人,受不了东北的寒冷,就回了山东。听说了这个事后,他挺高兴,说我饭做不好,水电咱不懂,做豆腐生豆芽行,我会。邵科长说,行,许师傅,给你配两个人,再找个地方,先干起来!
于是在食堂西头的平房里,找了两间房子,收拾了一下,盘上锅台,安上大铁锅,支上两口大缸,让木工班做了些木头盒子,买了些笼布,东西基本齐全了。
任何人都是一样,只要被人重视或赏识,他都会尽心尽力地去干。一切准备就绪后,许师傅带着从食堂里挑出的两个战士,高高兴兴地在平房里忙乎起来了。泡豆子,磨豆浆,磨好的豆浆上大锅里加热,淋出豆渣,倒入大缸里,用卤水慢慢点好,再舀入木盒的笼布里,用石头慢慢挤出水,等一会,鲜嫩的豆腐就做好了。

做豆腐这个活计,看起来简单,其实是个技术活,讲究的是火候把握。豆浆上锅加热,不能糊了锅底,那样豆腐会有糊味。热好了的豆浆,点卤水要恰到好处,卤水少了豆腐抓不成个,卤水多了豆腐老了,不鲜嫩。
天还在朦胧中,借助影影绰绰的灯光,在满屋子的蒸汽和混杂的豆浆味道中,许师傅只穿一件背心,站在锅台上,和另一位战士用力地晃动着吊在房梁上的布包,随着晃动,布包里的豆浆就从布包里流下,淌到正在加热的锅中。
自己做的豆腐结实、味道浓,加之在院里,不用跑远路去市里,食堂就愿意要。每天,都有机关和连队炊事班早早地拿了黄豆来,预定豆腐。订的多了做不过来,许师傅就分开来,让每个食堂都能隔三差五吃上自己做的豆腐。
二
许师傅还会做格瓦斯。那是他在东北学会的。格瓦斯是俄语“发酵”的意思,用面包干发酵酿制而成,在俄国,有着很长历史,据说在几个世纪前,有小饭店店主将食客掉的面包渣收集起来,装瓶子里发酵。几天后,面包渣变成浓郁酵香的汁液,喝了后可以助消化、调节肠胃,于是逐渐成为俄罗斯常见的饮品,很受欢迎。
没有大列巴,许师傅自己做面包,将面包烘干撕碎,进行发酵,又将发酵差不多液体灌入瓶中,加温进行二次发酵。过一段时间后,格瓦斯制成。瓶装的格瓦斯有些像未经处理的原汁啤酒,有些浑浊,带着黄色。打开瓶盖,一股麦芽似的香甜扑鼻而来。这东西大家大都没有见过,当然更没喝过。于是都抱着尝尝鲜的心理,喝一下。可惜,制作的数量不多,工艺又有些繁琐,做了一段时间,许师傅便没有再做。
不过,一段时间里,大院的服务社还真卖过格瓦斯,当年曾在苏联留过学的,或者在东北生活过的一些干部、家属,还真得喜欢喝那个东西。而我,却似乎对那个味道不是十分感兴趣,总觉得,格瓦斯甜不如汽水,酒精度数不如啤酒。但是,那段制作格瓦斯的历史,却是很难忘掉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先是楼南的食堂拆掉了,楼前的那些梨树以及水杉、苹果树,也被草坪、廊道与亭子取代。继而,35号楼也没有了,变成了停车场。然而,青春里的那些美好记忆,却并没有因为楼房与树木的消失而淡漠,反而,随着年岁的增长,益发清晰与悦动起来。梨花开了会谢,梨儿熟了会被摘取。房子有人住,就会有欢乐有生机,人去了,楼即使还在,也会少了活力,少了生机。
三
岗位练兵比武开始了,各个行当都要开始正规化、专业化。用孙处长的话,也就是说,不能再随随便便,嘻里马哈地啦!
科里开了会,要对管理处下属的各食堂炊事员进行培训,邵科长要求,能训就训,尤其是新兵。高,这个事就交给你了,你全权负责,到时候我去检查。
冷库边上的大屋子腾了出来,铺上麦草,整上大通铺。各个食堂将能抽出来的人,统统集中到大屋子里。大家热热闹闹铺开背包,互相打趣着,对这个新环境,一点也不觉得简陋,倒是带着许多的新鲜感。是啊,细想想,除了拉练,到哪里还会睡上地铺。
安顿停当,宣布了纪律规定,明确了班长组长,大致的培训安排。第二天就开始了活动。
说是培训,其实是以工代训。大家都到三食堂,让三食堂的李师傅以及几个老兵帮带一下。李师傅几十年的厨师经历,有许多的拿手菜,除了本食堂的人,一般人难以学到。李师傅为人好,不保守,愿意传授技艺、这在烹饪行当里有本事的人,是十分难得的。因之,凡来了的人,都很愿意学两手。
先是磨刀,好的厨师要有好刀。那个时候,食堂的刀,都是买的工农牌菜刀。切菜切肉的刀,首推工农牌大号菜刀。菜刀木把、铁箍,刀身厚重,买时,尚未开刃,需厨师将其磨开。先在粗石上,后在细石上,一点点,慢慢将其磨得锋利、顺手。有一把好刀,可以出很多的好活。所谓好厨师“一把菜刀走天下”,并非虚言。磨刀力度一定要轻推重拉,因为前推是呛刃走,而后拉是顺刃走,所以后拉时要加力,这样既可以磨砺刀刃,又可以避免刀刃受损。
菜刀是厨师的宝贝,李师傅的菜刀,谁也不能动,放在固定的位置里。李师傅拿起刀,像拿着武器,眼里顿时有了光亮。站在厚厚的菜墩前,他像一个武林高手,菜刀在他手里,烂熟于胸,任意翻转,各种食料在杂耍似挥舞的刀下,切、斩、拍、剁,顷刻间变成了种种艺术品,令人目瞪口呆。
灶火腾腾里,只见李师傅的勺子快速在料盆中收缩,铁锅随着他的手腕惦着,菜品便在锅中杂耍似地上下起伏,只一会,一盘颜色鲜美香味扑鼻的菜肴便出了锅。尝尝,都尝尝。李师傅擦擦手,憨厚的脸上有了许多的得意。

(参加培训的人员合影)
正因为技术好,师傅愿意教,有这样的机会,谁也不愿意放过,加之大家都有一些基础,所以很快,都能学到一些东西。虽然时间短,大伙反映,收获还是挺大。培训班结束,学员一起合了个影。不知为何,那张照片里,没有李师傅,是个遗憾。
这些人中,大部分成了各个食堂的骨干,许多人后来都复员回了老家。我想,即使他们不在部队里了,多年后,当年在济空管理处炊事员培训班及其后来学到的技术,以及在部队受到的锻炼,足以影响他的一生。当他想起在大屋子地铺上,以及三食堂厨房里的情景时,也一定会百感交集。
其实人的财富有很多种,我想,那些陈年老酒般的令人意味无穷的回忆,同样是一种财富。
时间其实是最不耐磨,一晃40多年过去,那支部队也在改革中整编,大院还在,早已不是彼时的光景。想起大院里的往事,心中便有着一种荡漾,眼里也便充盈着些许湿润。

作者简介: 高金业,笔名碧古轩主人。山东龙口人。1973年入伍,在空军部队工作30余年,后转业山东省直机关工作。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特写、诗歌等各种文学作品数百篇。中、短篇小说集《真情》被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品被收入《飞向极顶》、《绽放的军花》、《军魂》、《胶东亲情散文选》、《母亲的力量》、《庚子战疫》等书中。长篇纪实文学《北方之鹰》刊于《时代文学》,被青岛出版社出版,并被“齐鲁晚报”连载,该作品获山东省纪念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征文一等奖。出版有《胶东散文十二家高金业卷》。作品曾多次获文学期刊及文学网站征文奖。
壹点号碧古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