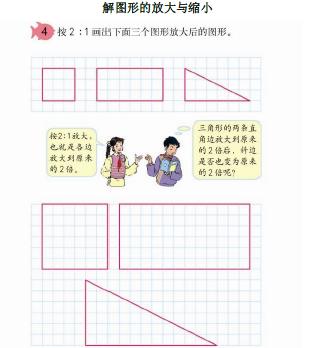作者:张金樑
我常常从日常教课接触到的中国戏曲学院学生的生活中,联想到五十年前的生活。五十年前,即一九三〇年,我和现在戏曲学院的孩子们一样,也开始了学戏的生活。我的学校就是程砚秋先生同焦菊隐、金仲荪先生创办、领导的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简称中华戏校)。
这个学校同今天的中国戏曲学院的生活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最显著的不同就是,中华戏校是在旧社会中创办起来的,然而它是在旧社会长期形成的视戏曲艺术工作者为下九流“戏子”的传统成见的污泥中,傲然挺立的一束艺术蓓蕾。正因为如此,中华戏校的生活至今还是我经常眷恋难忘的。
程砚秋先生治理戏校的最突出的思想,就是演戏要“自尊”。他常常对我们讲:“你们要自尊,你们不是供人玩乐的‘戏子’,你们是新型的唱戏的,是艺术家。”他对女学生讲:“毕了业不是叫你们去当姨太太。”现在,戏曲艺人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戏曲艺术工作者,有突出成就者则被誉为戏曲艺术家,他们都受到了广大观众应有的尊重,这在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程先生的治学思想的难能可贵也正在这里。

程砚秋
我在中华戏校学习了八年,这八年的生活是十分紧张的,也是十分充实的。在专业学习上,程先生不惜重金,为我们聘请了许多艺术名流担任教师,例如,马连良先生的业师蔡荣贵,李少春先生的业师丁永利,名丑郭春山等等。我学的是丑行,郭春山先生是我的老师。旦角的教师更是名流济济,程砚秋先生亲自任教自不必说,其他如吴富琴、陈丽芳、何喜春、诸如香、郭际湘(即“水仙花”)、阎岚秋(即“九阵风”)、张善亭(即“十阵风”)等,也都是中华戏校的教师。这些老师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的。我们在校八年没有寒暑假,连礼拜天也没有,只是到周末,家长可以来学校看望看望孩子。每天早五点半起床练早功、喊嗓,吃完早饭便是紧张的业务学习,中午午睡过后,下午还是业务学习(入学二年之后,一般下午便是实习演出),吃完晚饭后有半小时的业余活动时间,以后接上去是文化课,直到九点。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所以,我们的功一直没断,始终保持着循序渐进的良好学习秩序。

戏校练功
旧社会的艺人一般是幼而失学的,许多人演了一辈子戏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这当然要影响他们的业务深造。程先生主张把我们培养成“新型的唱戏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我们开设文化课,这也是中华戏校与旧戏班坐科学艺的显著不同。我们的文化课有历史、地理、戏剧史、国语。此外,还开设外文课以及美术、乐理等艺术修养课程,鼓励大家学书法,练绘画。我对脸谱美术颇有兴趣,经向张焕亭、张春芳、翁偶虹等先生求教,学会了这门艺术。在那个时候,陈墨香、杜颖陶、翁偶虹、吴晓铃诸先生,经常到校为我们讲学;焦菊隐先生的朋友,燕京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教我们外语,一般同学们都学会了一些外语的简单对话,外宾到校参观时,同学们张嘴就是:“How do you do?”“Sit down please! ”或“てんにちは”(你好)。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外宾向我们伸大拇指,校外科班学生则对我们羡慕不已。
学习文化课并不是为时髦,它使我们增长学识,开阔视野,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学戏中不仅知其然,而且也知其所以然,有利于演出水平的不断提高。程先生的演出是严肃认真的,程派戏的丑多,如《荒山泪》、《碧玉簪》、《鸳鸯冢》、《玉狮坠》、《青霜剑》、《锁麟囊》等剧目中都有丑,其中《锁麟囊》一出戏中就有十多个丑。丑角有个通病,容易临时抓噱头、出馊哏,这在程先生的剧团中是不允许的。程先生主张丑角也要演人物,他在台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在戏情戏理之中,不允许脱离剧情,更不许喧宾夺主。对这一点,与程先生合作终生的名丑曹二庚先生,表现得很突出,他既富于丑角的喜剧色彩,又不脱离剧情、人物,更不搞低级庸俗的东西。金仲荪先生不止一次地要求我们学丑行的学生,“要学曹二庚,要规矩!”

曹二庚
程先生排演《锁麟囊》时,我在程先生剧团里搭班,其中的丫鬟梅香(彩旦)是由丑角应工的,我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有一场戏,程先生唱的是〔四平调〕,我在一旁搀扶着,程先生的脚底下相当有功夫,我紧随着他,十分小心,多一步也不敢走。程先生演《六月雪》,其中的禁婆子也是丑角应工的,禁婆子打窦娥,窦娥哭诉了她的冤情,感动得禁婆子也哭了,有的丑角在此时又抹眼泪又擤鼻子,舞台形象很丑,程先生对此是反感的,他对我说:“演到这儿,你哭就可以了,不要擤鼻子。”程先生的这种艺术见解是以他对人物、剧情的深刻分析做依据的。我们有了文化课的底子,易于理解他的要求,并付诸行动。
学习外语是为了和国外朋友进行艺术交流。程先生的戏,知识界的观众爱看,外国朋友也爱看。记得程先生演《鸳鸯冢》时,楼上包厢里坐满了外国观众,程先生深沉委婉的唱腔,轻盈细腻的舞姿,强烈地吸引了他们,使他们得到了艺术享受,理解了剧情和人物,做出了好评。程先生很注重向国外的戏剧艺术学习,他一方面严格要求我们学好传统戏,一方面还组织我们学排外国戏剧,我们排过《梅萝香》及《少奶奶的扇子》等外国名剧,记得是请唐槐秋先生到校辅导排练的。排这些戏不是为了对外演出,是为了从中受到启发,得到借鉴。

程砚秋之《鸳鸯冢》
在程先生为我们排《孔雀东南飞》时,我们废除了布景的出将入相以及台上的检场,采用了边条幕的方式,这在当时是首创;一些持保守观点的人讥讽我们演的是“文明戏”,但事实证明,广大观众是接受的,是喜欢这样做的。程先生对我说过,将来你们不但要演传统戏,也要演现代戏。一九三七年初,程先生曾组织过一个去法国进行戏剧考察的戏曲团体,也从中华戏校选了外语水平较好的几个学生参加,其中有宋德珠、洪德佑、傅德威、王金璐和我,一切都准备齐全了,因“七七”事变,而未能成行。
中华戏校有自己的校歌、校徽及校服,我们的校服是“制服”,不戴圆帽头,不穿长大褂,走出校门个个精神抖擞。中华戏校还有严格的校规以及奖励制度等。旧戏班讲究“打戏”,学生有了过失,劈头盖脸一顿打,甚至“打通堂”,株连无辜。这种长期沿袭下来的恶习,在当时是很难纠正的。中华戏校也有“打戏”之举,但程先生及焦、金二先生坚持一点,即打学生不许打头脸、不许伤内脏,这样,“打戏”之风便收敛了许多。而促进学生好好学习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设立月考、大考、年终评奖的制度。每年评定一次优秀生,凡学戏、文化及操行均优的学生,被评选为优秀生,头五名发给十二元的奖学金以及铜镇尺、乒乓球拍子等奖品。这种制度培育了以学习好为荣,学习不好为耻的风气,促使了大家学业的进步。中华戏校也是以字排辈的,排列顺序是德、和、金、玉、永、兆、令、铭,但只排到永字辈便因战事,无法继续办学而中止了。前几辈的学生中确实出了不少人才,如德字辈的宋德珠、傅德威,和字辈的李和曾、王和霖,金字辈的王金璐、李金鸿,玉字辈的李玉茹、侯玉兰,永字辈的高永倩(后改高玉倩)等,他们有的至今还活跃在京剧舞台上,有的担负着培养青年一代的任务,在全国各地有着广泛的影响。
我陪程先生最后一次演出是在一九五〇年,那年我在武汉,程先生到武汉、四川等地考察戏剧,应武汉观众要求演了两场《锁麟囊》,我陪他演了梅香,同台演出还有高维廉、高盛麟等。在这次活动中,程先生和我师生相聚,分外亲切,演出后,程先生请我吃饭,饭席上他谆谆嘱咐我说:“要保持京剧传统,不要胡乱发挥;要好好树正气,树个旗杆。”这以后和程先生分别八年未能见面,使我终生遗憾的是,一九五八年程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一九八〇年七月
(《御霜实录:回忆程砚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