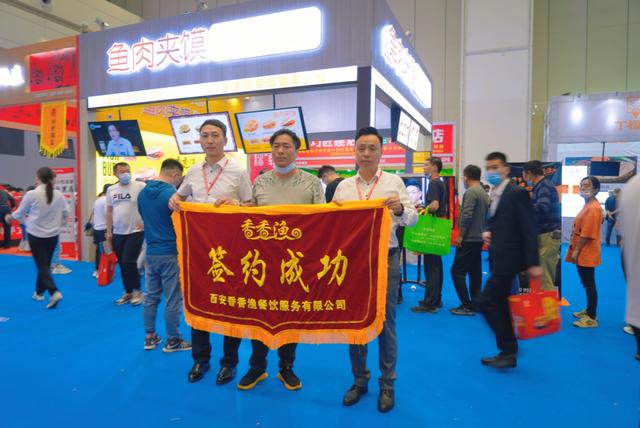这是一条古村,到底有多古老?据文史资料记载这条村自南宋绍兴年(公元1131年)开村,距今有多少年?你自已数数指头吧。
900年来沧海桑田,一一记述在庙门前这副对联里,“银河波浩荡,南山貌巍峨”。相传先祖开村时,这庙前是一片浩荡的海洋,近看似银河般波光鳞鳞,远眺可见南山之巍峨。村长卖力地向文史专家介绍着,这里是“银河”、“银塘”,那里是“银岗”、“银坑”,现在脚 踏着的这块土地是旧时的码头,是先祖扬帆出省城的地方……看着眼前这汽车飞驰电掣的公路,村长说干了口水,仍然调动不起专家们对久远年代的想象力。村长情急之下挖起“银坑”里的两块蠔壳以作佐证。

沧海桑田淹没了旧时的痕迹,但古村的古老却能从程家舅婆的脸上找到蛛丝马迹。
有程家舅婆当然先要有程家舅公,程家舅公年龄说老不算老,才七十多岁,若在省城七十多岁的老头都还只是个大叔呢。程家舅公是辈份大,据说舅公是太公最小的儿子生的最小的儿子的最小的孙子,而这最小的孙子又不知何故,五十岁才娶上老婆才生下舅公。舅公说他与我奶奶同辈,他叫我奶奶做三姐。解放初期斗地主,作为地主婆的我奶奶回乡居住了好一段时间,那时舅公只是一个八、九岁大的孩子,他常常到三姐家赠饭。哎哟,我的天!我奶奶如果还健在,现在都有一百三十好几岁了!我们居然有一个七十多岁如活化石般的舅公!这是乡村才会有的滑稽!

程家舅公娶的老婆我们叫她做舅婆。舅婆是邻村罗家女,也是七十多岁的模样,扁圆的一张脸儿油油腻腻,叫人想起“油香饼”。身子也是扁扁胖胖的,不知是因手短脚短而显得身子扁胖,还是因为身子扁胖而显得手短脚短。总之她行动迟缓,足不出三里地,终日里不是坐在暗暗的屋子里摘豆子,就是坐在巷口青石板上与对门瘦小陀背的阿婆及缺了牙的阿公打牙较(聊天)。聊来聊去也不过是东家长西家短,这村里谁家的底细不清楚,聊尽了,舅婆几个便在青石板上垂下那如一潭死水的头。

不是说古远时这里“银河波浩荡”面向海洋的吗?最大的佐证是这里的屋子都是依山岗而建。西面程家的“文奎巷”拾级而上到山岗顶上就是邝家的房子,邝家房子拾级而下就是东面的“和平里”。说到邝家,巷口青石板上那一潭死水即时流动起来、活起来了,那些如荒坟般的嘴皮子马上有了鲜活放题。
终于有新鲜事了!
“山岗顶上邝家的后人从省城回来要修建祖屋了。”……
消息首行先是从邝家大嫂发布,然后程家舅婆转身告诉陀背阿婆,陀背阿婆在缺牙阿公的耳边大声吹着风,于是传遍了全村的每个角落……一潭死水被抖动得波光鳞鳞。
重修祖屋有啥稀奇的?关键是这邝家有故事呢。
早在咸丰年,邝家的祖上就在省城经商做生意,在高第坊经营着省城最大的一间皮草店,十年八年间又在康泰路开设了省城第一间,全中国第二间的洋服店。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所穿的总统服就是邝家元字辈族人所缝制……要说这邝家的威水史真是数不尽。
这次回乡重建祖屋的就是邝家为孙中山缝制大元帅服的那一支那一脉的后人。
咸丰年就定居省城,在省城开枝散叶历经数代,按说断了与乡间的联系也是正常的,为何这邝家在这乡间东面留下了一片的房舍?据说是当年邝家祖上衣锦还乡,从省城回来修缮祠堂,置田置地置房产,才有了现今雄居村东面的这一遍邝氏宅第。当然,对于这次回乡重建祖屋的邝氏兄弟来说,他们只知道是1938年,日冠侵华,城省沦陷,爷爷回乡蛰居,才有了留下给他们的这所房子。

爷爷的房子随同中国近代史一样历经沧桑,也如邝家家族,人事几翻新。抗战八年,邝氏家族在省城的家业毁于战火,邝氏族人流散四方。爷爷原先是计划举家迁去抗战大后方桂林,但流浪桂林的途中满目苍痍,前路茫茫看不到希望。于是,打道回府,蛰居乡间至1945年抗战胜利。省城光复,爷爷举家重回省城,头也不回!国破家亡的日子不堪回首!对于这乡间的荒蛮爷爷没有半点的留恋。1957年大跃进,乡中来信说要拆了他家的房梁以支援家乡建设。爷爷回信只两个字“拆吧”!他相信亡国奴的日子不会再来!他再怎么倒霉也不会霉到再回乡间蛰居!当然,被拆去房梁的房子经历着数十年的风雨,到了孙辈的手上时,已是颓垣败瓦。房子先是被乡中的族人当成鸡舍,后又建成了平房出租,欲要据为己有了。随着乡村振兴的春风,邝家这一脉的孙儿决定回乡重建祖屋,光复祖业。
重建祖屋,光复祖业,只是幌子罢了,其实兄弟俩各有盘算。先说大孙这一房,大孙、大孙媳妇事业有成,在省城有头有脸有社会地位,在职时大孙承包单位企业、大孙媳与人合伙开广告公司,现今退休又享受着国家几级专家的待遇,乡间这房子其实并不在心上的。但见惯大场面大世面的大孙、大孙媳妇偏偏就是没有见识过乡间凡人百态的生活。而且读饱诗书,有着深厚的文学根基,满满的文学情怀要寻求渲泄的出口。于是,重建祖屋,享受田园牧歌的生活促使他们由精神向往到付于实际行动。花几十万回乡重建祖屋玩玩,大孙子这一家是日子过得太好了,有两个小钱身子痒。

二孙子这家日子过得好不好呢,不好说。说他不好吧,因为这二孙子、二孙媳妇学历不高,只是个收入平平的工人。二孙子很早就下了岗,依靠着他娘家的表兄关照着在私人企业里打工。二孙媳妇本就是农村变城市人的农转非。不知是日子过得巴紧,还是这个阶层本就不懂衣着体面,反正这俩口子从没见穿过一件得体的衣裳。但说他们日子好过吧,也可以,因为依靠着那猎德村暴富起来的岳父的资助,他们也在省城市中心买了两所房子,靠出租房子填补了微薄的工资收入。最起码他们会跑回乡村告诉乡间的族人,我们在省城市中心位置有两间屋!省城市中心位置的房子十万八万一平方的哦!听得乡间的人用崇拜富豪的目光仰视着这俩口子。于是,阴阴的胜利者的微笑挂在他们阴阴笑着的嘴边。如今回乡重建祖屋,于是,这俩公婆又幢景着在乡间出租房屋变富豪的黄梁美梦!

山岗顶上邝家四层楼的新屋就这样竖起来了。自此,舅婆那帮三姑六婆又多了八挂的材料,因为村民总能看到一对衣着光鲜、年轻的老年夫妇牵着小洋狗游走在村中的巷陌,成了这古老乡村里一道异样耀眼的风景。

不知何故,小时候乡间的古老大屋是黑洞洞的,如今新时代了,但乡间新建的楼房依旧是黑森森的。以前的古老大屋至少还有一方见天的天井,现在可好,天井也盖上了瓦顶。
黑黑的大屋里,舅婆正在摘豆子,滴溜转着的眼珠子,想着与豆子无关的事情。听老头子说过,这回乡盖房子的邝家兄弟,按理与我们是很亲的呀,是同太公的呀,他们的奶奶可是我们家老头子的堂家姐呀,但这邝家兄弟与我们像是陌路人,路过了也没打个招呼,难道他们的奶奶没有告诉他们有我们这门子亲戚吗?那天,村东面的邝家大嫂发出“邝家兄弟回乡重建祖屋”的头条新闻时,舅婆就很有点醋意:咦惹!瞧她能呢!虽然都是邝家的,但他们太公那一辈就已经是疏堂兄弟了,哪有我们亲!这条村里,我们才是他们至亲,他们家的事,我们应该是第一新闻发言人才是。舅婆恨恨地剥着豆子,她决定要和邝家兄弟认认亲戚,攀回这门子亲。
在巷口、在家门守候着,数着手指头计算着邝家那大兄弟与大媳妇该回乡的日子。终于这天,邝家的大兄弟又携媳妇回乡来享受田园牧歌了,看着大媳妇那飘逸的长裙在家门前飘过,舅婆慌忙掉下手中的活,急急脚去门前想喊住这门子亲戚。奈何只恨自己腿太短迈不起快步,恨自己身子太肥胖挪移笨拙,眼巴巴看着大媳妇一阵风似的飘走了,只得捶腰拍背地叹息。舅婆捶着腰,低头暗自思忖,听东边邝家大嫂说,这邝家大兄弟在省城混得有模有样,尤其是那大媳妇好像还是个什么文人名人呢。这样的人,说不定是看不起我们农村人,有心不认我们这门子亲戚呢。

又过了些许时日,这天,舅婆等一帮三姑六婆阿公正在巷子口的青石板上东家长西家短,隔老远看见村长又带着一帮上级领导模样的人参观村子。村长正卖力地介绍着,本村历史以来重文兴学,这里一二三排列着私塾就是最好的例证。正说着,来到了舅婆这一帮老人家跟前,村长又说,关于我们村祖上重文兴学,眼前这帮村中长老都能说出一二。文化专家们热情地和这帮村中长老打招呼,崩牙阿公用他漏风的语气介绍起他太公读卜卜斋的往事。村长向这帮村中长老介绍说,这是省城及市里来的文化专家,就乡村振兴的事来视察我们村。舅婆眼尖尖地发现这帮文化专家里竟然有大媳妇。她惊喜地发现新大陆似地说,哎呀,阿嫂,你几时翻归(回家)来的呀?然后热情地上前要拉大媳妇的手。
大媳妇礼貌地向舅婆点头微笑着。舅婆的热情,大媳妇并不意外,自从回乡重盖祖屋后,隔三差五地回乡,在村里出出入入,或者互相见过。但舅婆的亲热,大媳妇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村长见状,忙过来介绍,他指着舅婆介绍道:这是我们村最大的姓氏程家的掌门人,她背份很高,她是我们的阿婆,她的老公是我们的阿公。然后又将大媳妇介绍给舅婆,这是省城里的文化专家,她好犀利的啊!她是名人来的啊!是邝家的……村长还没有说完就被舅婆一摆手截停了。
舅婆说,不用你介绍,我比你知道得多,我们是亲戚,是自己人。所有人连同大媳妇都瞪着惊奇的眼睛。看着众人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舅婆新闻发言人的感觉来了,她对大媳说,你们家奶奶可是姓程,叫程义欢?

大媳妇张着茫然的眼睛,不置可否,显然她是不知道。的确,大媳妇从没听过夫家的人说过奶奶姓什名谁,何方人氏。现在突然有人说祖奶奶是这里的人氏,与祖爷爷是同一条村的,而且东边西边只隔十间八间房子的距离,这也太奇闻,太意外了吧。她决定要回去问问先生。
回去问先生肯定是不会有答案的,她先生只会给她一句:八挂!多事!先生对于亲亲戚戚,家家族族这些理不清的关系从来都不入脑门。
虽说不入脑门,但自从舅婆说过大家是亲戚后,大兄弟与大媳妇每逢路过舅婆家门都会顿顿脚打个招呼,与他们亲戚一下。春节会给舅公送点尤鱼冬菇虾米腊肉,端午节送箱裹蒸粽子,中秋节送盒月饼之类的。舅公会回赠些自家地里种的没公害绿色蔬菜地、地瓜叶之类的。多了一门亲戚,就多了一些不知是虚情假意,还是真情实意的亲情。

劳作惯了的舅公终日在自家菜地里浇水种菜,然后摘菜卖菜,村口卖菜摊里的一帮人舅公是最勤力的那个,每日里的早出晚归,对于邝家这门亲戚现时的情况他所知的信息远远不如舅婆多。于是,晚间昏暗的灯光下,卖了一天菜,辛苦了一天的舅公吃着舅婆为他备下的晚餐,他问舅婆:如今三天两头回乡来出出入入的邝家孙子,是三姐哪一个儿子的孩子?
舅婆说,这个我没问哦。她反问舅公:三姐有几个儿子?
舅公呷了一口小酒,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
五十年代的那一天,舅公被她母亲拉着去到山岗顶上那房子拜见从省城里回来的三姐。说是三姐,但舅公觉得她似奶奶或外婆,至少也是个伯娘,因为当时的三姐已经近六十岁的样子。听母亲说,三姐在省城被划为地主婆,所以要回乡来参加劳动改造。他记忆中,三姐清瘦精干的模样,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衣襟前总别着一方手绢。三姐爽朗大方,待人和霭,城里带来的饼干糖果总分派给孩子们吃,那时他常到三姐家赠饭。隔壁饭菜香,到三姐家赠饭的日子很美好、很香甜。稍长大后,舅公听他父亲那一辈人议论说三姐有两个儿子,搞不清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娶的老婆没生养,于是,这个儿子就在外面与其他女人生了一个孩子,抱回来交给自己老婆抚养,那个帮他生仔的女人用钱打发走了。
舅婆一听,哗!这可是个大新闻啊!就是说这回乡盖祖屋的邝家兄弟俩,其中一个是野孩子?!
舅公即时呵斥纠正道,是他和其他女人生的孩子!终归都是他自己的血脉啊!哪算野孩子!他斥责舅婆夸张。
特大新闻啊!兴奋啊!舅婆兴奋得每条神经都在跃动,嗓子里每个细胞都在呐喊!以后,每次摘豆子时,她滴溜转动的眼珠多了很多思想内容,邝家这俩兄弟到底哪个是在外面抱回来的呢?她思考着,不停地推理着,她要做当代的福尔摩斯,她要破破这几十年前的家族奇案,她要发雷人的新闻头条,她要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接受村人注视的目光。

舅婆首先是要疏理清三姐的儿子及孙子的层叠关系。原来三姐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娶妻多年才有了一个儿子,二儿子也是娶妻多年后才有了一个儿子。这就是说,三姐生了两个儿子,而这两个儿子又各人有一个孩子。就是说,这次回乡盖房子的兄弟俩是堂兄弟关系,这俩堂兄弟里有一个是抱回来的,到底哪个是抱回来的呢?舅婆不停地转着眼珠子,不停地思考着。这三姐的两个儿子说也怪呀,怎么都是娶妻多年后才有一个孩子的呢?生仔很难吗?能生的那家爽快点生多个不好吗?那就可以证明只生了一个孩子那家的是抱回来的,多么简单呀,现在这个情况就很扑塑迷离了。舅婆决定挪动自己笨拙的双脚去明查暗访。

蹒跚着脚步,颤巍巍着身子,翻过山岗顶来过东边的邝家,在邝家大嫂家的天井下,摇着蒲扇,扯开天井般响亮的嗓门,大声地互相寒暄着吃过饭没有呀?拉得顺畅吧?等无厘头的开场白。然后,舅婆话锋一转,突然伏在邝家大嫂的耳边,努力压低嗓声音说,你们邝家回乡来盖房子的那俩兄弟,其中有一个是抱回来的呀!最后的“呀”字舅婆实在是压不住奋地高吭起来,臭臭的口气喷到邝家大嫂的脸上
哗!爆炸新闻!邝家大嫂的心“咯噔”了一下,她也兴奋异常。但转念一想,这么大的事件,我居然不知道!要从程家那边传回来,我这邝家掌门人还有脸面吗!邝家大嫂把竖起的耳朵从舅婆的嘴边抽了回来,正了正身子,撇嘴一笑,一副心中早已了然的样子说,咦,以为你来有什么新鲜事,这件事我们早知道。
哼!她怎么会知道!要知道这邝家大嫂可是个守不住嘴的人,如果她真是知道早就满村里发头条新闻了!这么有新闻价值的新闻是从我这里最先发出的!哼!舅婆认定了这邝家大嫂是想要和她争抢风头。既然邝家大嫂不买她的脸面,舅婆也将自己的亲热收了回来,将原本侧着的身子坐得直直,冷眼笑着说,既然你早知道,那你告诉我,那俩兄弟哪一个是抱回来的。她冷冷地看着邝家大嫂,等她回答。
其实,舅婆内心狂抓着,一方面她是知道邝家大嫂不一定能给答案,但另一方面她又很希望邝家大嫂能给点线索或蛛丝马迹。

邝家大嫂的确是不知道这门子的事,虽说都是邝家自己人,其实既亲也远,因为从太公那一辈已经是疏堂兄弟了,到自己老公这一代已经疏堂了几回了,而且他们那一房人一直在省城定居甚少回乡,他家的事连自己老公都不知道,她这外嫁进来的媳妇更无从知晓。但告诉舅婆说自己不知道,作为邝家掌门人的脸面往哪搁呢?于是,邝家大嫂快速地思考着,罗辑推理着,她也想破个水落石出。
要说这邝家俩兄弟嘛,对大兄弟这一家,邝家大嫂总有说不出的感觉,话不投机,亲热不起来。当初这俩兄弟回乡盖房子,大嫂很是热心,跑前跑后帮忙张罗,想着房子盖好后做他们出租房子的代理人,谁知这大兄弟说他们的房子不出租,他们盖房子是要来玩的。玩的?啥意思?怎个玩法?大嫂无法领悟。房子盖好后,只见大兄弟的门前挂起了什么工作室,什么传承基地的牌子,然后乡政府、镇政府好些领导到访过,又时不时有省城的画家、文化专家到访,时不时大媳妇又带一帮人回来,出出入入,或住上三天两头,以为他家会有什么大搞作,但这些领导专家访完也就完了,也没见有什么戏码。车!这样来来往往的有什么用途!只花钱不赚钱,还不如出租,一个月赚一、二百元划算呢。
一、二百元?大媳妇听后咯咯发笑说,一、二百元,我出租来干什么!言下之意是看不上这一、二百元。
大嫂有点愤怒了,哼!一、二百元看不上,她很有钱吗?我们家姑婆在香港经商衣锦还乡,站在村口见人就派一百元,不管你是同宗族人,还是村里的邻舍,甚至是行过路过的村外人都有钱派,这才叫真有钱啊!这大媳妇回乡这么久未见过她洒金钱,有啥了不起的!
作为邝家掌门人,宗族中大小事都要听我的,尤其是省城归来的人事事都要依靠我,都要来求我这个邝家大嫂。这大媳妇虽没有不尊重我的言行,但可恨的是,在这十乡八里她一个省城回来的人,认识的人居然比我多,镇政府、乡政府、村委会干部她都认识,她到乡政府办事个个都给她行方便,她回乡办事根本不用求我这个大嫂。想到这里大嫂酸溜溜的心很不是滋味。
每次有省城、港澳等地回乡的邝家族人,都要跟着我这个大嫂的屁股后面满村子参观,个个都伸长脖子听我给他们讲乡村的新发展,听到目瞪口呆。只有这大媳妇不用听我讲,她知道得比我们这个村里人知得多得多,村长说大媳妇是乡村振兴文化调研专家组的成员。讲到乡村未来发展,没有我发言的地方,我这个邝家发言人反而要听她讲最新消息,想到这里邝家大嫂多少都有些恨意。
在我们农村,女人六十岁就算是老人家了,大都陀着背在家里带孙子。但这城里回来的大媳妇都是五十多快六十岁的人了,却打扮得似四十来岁的样子,那风骚的样呀,真是的!退休了,不在省城里带孙子,却牵着条小洋狗在乡村里游走,咦,就是看她不顺眼。巴不得那抱回来的野孩子是他们这家的。

再看看这二兄弟这家,大嫂嘴角挂着微微的笑意。房子才盖好,这二兄弟就急急求我,委托我帮手将房子租出去。一般租金都是一百元一个月,因他是新房子,我帮他二百元一个月租出去,二兄弟俩口子千多谢万多谢地答谢我。逢半年或一年将租金交给他们时,他们都会给我少少的饮茶钱,这俩口子多贴心啊。
再看看那二媳妇,和我一样剪一头的毛刷刷的短头发,阔阔短短不甚讲究的衣着,同样是嗓门大大的,说话无所顾忌,很是同声同气。和我一样,二媳妇也有一双因劳动而被操劳得粗燥掉皮的手,大家握在一起很有亲切感。哪像那大媳妇,一双白嫩细致的手,每次见到她,我都不自觉地将自己双手缩到背后。
这么一想,这么一对比,大嫂顿时觉得,那抱回来的野孩子肯定就是大兄弟。但她也知道自己这个说法没有严密的依据,是自己的推测而已,所以她不敢肯定地说出来。她只对舅婆说,那两兄弟一家的媳妇老实些,一家的媳妇涂脂抹粉些,涂脂抹粉那家就是抱回来的。舅婆收到新信息了,连连点着头。明查暗访总算有些成绩,回去继续调查,继续分析。
依然是在黑黑的大屋里,依旧是在摘着豆子,舅婆的眼睛比以前滴溜转得更快,她分析着,那大兄弟俩口子三天两头回乡,证明他们很热爱家乡,那二兄弟盖房子后至今没怎见他们回来,证明明他们对这里的感情淡啊,哼,如此一分析,那抱回来的孩子肯定是二兄弟。再有,邝家大嫂说,那俩兄弟,一家的媳妇老实些,一家涂脂荡粉。舅婆成日里只见过大媳妇在小巷里出出入入,至今未见过二媳妇,二媳妇长什么样,舅婆全然不知。那大媳妇虽然长得比我们农村人标致些,收拾得年轻些,城里人都是这样的啦,她们不像我们农村人要下田干农活,日晒雨淋,自是是会长得嫩口些。平日里看那大媳妇行路就是行路的样,绝对没有扭屁股,荡腰枝的姣婆样。而且说话也是斯斯文文有,对人热情,见到我和老头子,一口一个“舅公”“舅婆 ”地叫做,是个蛮实在有教养的人啊,根本不会是涂脂荡粉的荡妇。哼,这么一想,那二媳妇一定是邝家大嫂口中那个“涂脂荡粉”的荡妇!那抱回来的孩子肯定是二兄弟确凿无疑!

转眼到春节了,大兄弟和大媳妇从省城又回乡来了,给了舅公舅婆大包细包的冬菇腊肉,大大盒的瑶柱花胶,还封了一百元的大红包给她的孙子。舅婆扁扁的脸上充满幸福的笑意。都说大媳妇是文化人,是名人,眼角高,瞧不起人,舅婆却没这种感觉,她觉得这大媳妇很懂礼仪,很懂尊生长辈呢,为人又大方,很有些三姐当年给村里孩子派糖果、招呼孩子到家里来赠饭的风范。为了回馈大媳妇的好,她决定爆些料给她听听。
将正要溜狗的大媳妇拦截在巷口,舅婆煞有介事地问:你们家俩兄弟,怎只见你们俩口子回来,从没见另外那兄弟回来过?言下之意是那个不怎回来的二兄弟有问题。
话里藏话,打埋伏,甩包袱都只是村妇们传人是非的基本功而已,大媳妇出生在好人家,一直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哪里见识过这乡间人的弯弯肠子。她只是直楞楞地想,这次回乡盖房子,盖的是兄弟俩一人一半,各自独立门户的兄弟屋,除了一墙相挨外,互不相干。他家为何要出租?他们为何不回乡?大媳妇从来没有研究过,被舅婆这么一问,不明就里,一时间有点懵然了,不知作何回答。
进来坐坐,告诉你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舅婆一手将她拉入那间黑黑的屋里,舅婆双眼在昏暗中闪着幽幽的光,说起了大媳妇所不知的家史。
舅婆说的可不是家史,是家丑,是父辈的丑闻啊!大媳妇的心堵得慌。

三姐的大儿子就是自己先生的父亲,是自己的公公啊!也就是说自己的先生有可能就是那个被抱回来的孩子,自己的公公有可能就是在外面找个女人帮自己生完孩子后用钱打发人走的恶人!想想很恶心。
自己公公可是个知书识礼的教书先生,除了性情略为固执外,为
人正直,与人为善,平淡平和,左邻右里出了名的好好先生,那么丧尽天良的事怎会是他的所为!绝对不会!
那么会是二叔所为?二叔是工业公司的干部,平日擅书法,好诗词格律,为人也是正气正直的,感觉也不应是他的所为。
但说也奇怪,公公与二叔俩都是老来得子,都是只有一条独根独苗。
初嫁邝家时,每到晚餐,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公公便会遥想当年。抗战时,避战西南,与婆婆相遇相知,结为夫妻,很有听粤剧折子戏《抢伞》的味道。抗战时就结为夫妻,为何到六十年代才生出儿子?若说战乱不敢生孩子,或者说战乱生下孩子养不活,都倒能说得过去。但1949年解放到六十年代,有十几年休养生息的平和年代,孩子可以生一窝了!为何公公只有我先生这一个孩子,而且还是老来得子?真是很有疑问。其实就这个问题大媳妇也在被窝里揪着先生的耳朵追杀过多回,先生永远都是那句:不知道,八挂,多事。他永远都像是心里没故事的那种人。
公公有嫌疑,二叔同样存疑。二叔说过,他与二婶相识是因为抗战时他蛰居乡间,邝家伯娘是翰林公之女,古文学修养极深厚,二叔因好古诗词,隧与伯娘投缘,伯娘每日授予作诗及撰联知识。伯娘对这个侄儿相当欣赏,随将自己娘家的侄女许配予二叔。按理二叔也是抗战期间成婚,为何也是到了六十年代才生得一子?这孩子就是二兄弟,二叔是继公公得子后才生得一子,好姐妹爱约一起上厕所,难到好兄弟要约一起生仔?二叔同样可疑。
被舅婆牵着手走进这黑黑的大屋,懵懵然的大媳妇也变成了八挂的村妇,她就这么被舅婆牵引着,八挂地思考着、猜测着。她不禁也八挂地问舅婆,据你所知,那抱回来的孩子是我先生呢?还是二兄弟?
怎会是你们呢,你看你们俩口子都是正人正派的样子。舅婆拍着大媳妇的手,爱都来不急,她怎会伤害大媳妇呢。她压低声音,凑到大媳妇面前说,是你们那个二兄弟,你看他们都不回村来,证明明他们对家乡感情淡。然后舅婆又鄙夷地说,你们邝家大嫂说了,是涂脂荡粉的那一家。
一句“涂脂荡粉”把大媳妇打懵打痛了!想想二兄弟的媳妇,那是个穿不讲究,吃不在乎,话也说不好的粗粗鲁鲁的农转非。而自己呢,平日里总要擦点小口红,衣着要讲体面的人。“涂脂荡粉”的不是指自己,还有别人吗?

走出舅婆家,大媳妇的背冷嗖嗖地发寒。一句“涂脂荡粉”她读懂了邝家大嫂对她的恨意。平日里惬意悠闲的乡间巷陌顿时没了曲径通幽的诗意,那一扇扇黑洞洞的窗后都隐藏着一双双戳戳点点的利眼。抬头远望村边那一片菜地,田园依旧,但不再有牧歌了。
一连数日,心中困绕着“谁是抱回来的孩子”的问题,那句“涂脂荡粉”也时时戳痛着大媳妇的心房。再见到舅婆时,舅婆的眼神有些回避大媳妇的闪缩,显然她事后一定又与邝家大嫂交流过新情报,知道自己上回在大媳面前讲错说话了。见到邝家大嫂,她一副讲了就是讲了呗,你当我是无知村妇般的坦然。面对着这帮平日被大媳妇赞美为“纯朴”的村妇,大媳妇突然对她们痛恨之极!伤害别人却毫无悔疚之意。

望着沿山岗而建层层叠叠的村舍,大媳妇突然觉得,这乡村也真是过分的鸡犬相闻了吧,谁家放个屁,隔邻二叔婆都闻得到。家中发生个事,被人从村头传到村尾,一切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所遁形。而且还被世代相传,似抹不去的墨迹。
望着宗祠林立的乡村,突然觉得无比的压抑。想想邝家大嫂这个邝家宗族掌门人的嘴脸,突然觉得有一种久违的熟悉,大媳妇想起了小时候看的电影里那些残害人民的土司、头人。她突然对宗族主义生出无比的痛恨!就是这些宗祠令家族过分地世代牵扯,令家事丑闻被人代代相传,成为压得后辈喘不过气来的一座大山,一段想甩也甩不掉的家族历史!大媳妇突然生出一句:宗族主义是扼杀灵魂的梏桎!是套在人们心灵上的枷锁!
望着自己回乡建起的这所房子,大媳妇突然觉得毫无意义。《早春二月》里谢芳与孙道临为冲破封建枷锁,投身到革命洪流,冲出乡间小镇。而我却花几十万回到乡村里做被压迫的“文嫂”,想想真可笑。

淡然书屋里,咖啡正飘香。好友筏子刚从莫道尔卡的海拉尔小镇回来,她在那里买了一所伐木工人宿舍的小木屋,过着夏天北飞,冬天南回的候鸟式生活。呷一口咖啡,她无限回味的样子……
村庄隐掩在深山密林中,那里没有工业,远离现代文明;那里纯净无污染,人们生活简单,人心是纯朴的;每日跟着村里人上山摘野蓝莓做果酱,采野山蜜烘烤面包,茶带花香,面包有蜜的香甜……
她仰着脸儿,微闭着眼睛,轻晃着头,讲述着她的诗和远方。引得姐妹们的无限向往。
在这村子里,大媳妇也曾低头抚清风,也曾早餐带菊香,也曾田间一把青菜,细嚼无污染的清甜……听着筏子的描述,她比其他姐妹冷静多了。没有教化,没有接受过文明的洗礼,人心会纯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意味着抬头只见头顶那一小片天,低头只见那巴掌大块的地,缺乏见识,心理狭窄,心灵自然就会扭曲。大媳妇对筏子的描述有所质疑,因为她想起了舅婆及大嫂那可悲可恨的嘴脸。
筏子说,童话是自己心中营造的,与环境有关也可以无关。都市文明进入到闭塞的山村,矛盾与隔核肯定的,但不需要去碰撞。不同一个世界的人,说不清楚的。人与人之间不需要深谈,言不需尽。漫山的山花,你只闻花香就好了。
筏子的话大媳妇听进心里了,童话是自己心中营造的……你只闻花香就好了。
再次走在乡村的巷陌,勇敢直视黑洞洞的窗口,让那一双双戳戳点点的利眼在你的直视中变得闪缩;远远看见舅婆在招手,你轻轻一笑,飘然而过,不在她跟前停留;宗祠门口大嫂俨然把门的狮子,一副恶狠狠的面容,那有如何!径直进去给祖先上柱高香,同是宗祠的子孙,你需要看谁的脸面!祖先牌位静静地伫立几百年,看着这群肖与不肖的子孙。谁家的锅底没有灰!真要翻估计你家的比我家的要厚上千百倍!

回家里问先生,那抱回来的野孩子你希望是谁?
先生愤怒地一摆手,无聊!
大媳妇幸灾乐祸地想,如果是你堂弟,你觉得如何?
先生说,是就哈哈大笑几声!
大媳妇穷追不舍,不肯摆手,再追问,如果是你呢?
先生更加愤怒地说,那就更加哈哈大笑,更加笑多几声!然后去寻亲!
你就不怕村里人背后议论你?
怕什么!即使是抱回来的孩子,都是有爹有娘生的!我正正常常一个人,我有什么不见得光的!
你不怕大嫂在宗祠散布谣言攻击我们吗?
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政府有党的领导,难道她还能像旧社会一样浸我们猪笼吗?!你真是想得太多了,神经兮兮的!
哎哟,人家当事人都如此通透,我为何给自己精神压力!卷进舅婆大嫂的是非里,受她们的语论困绕,我岂不也成了丑陋村妇一名?
杨绛先生说,一地鸡毛是日常,岁月静好只是片刻……被人指指点点是日常,因为我们如此优秀,乡村如此落后。
杨绛先生说,远处的是风景,看近处的是人生。人生就是这么一堆烂人烂事,身在乡村,心远就好。
今天花棚下正闻着菊香,狗吠的乡村巷陌隐约又听到舅婆与大嫂的交头接语声,大媳妇淡淡地站起来,从楼顶天台上远远地俯视着乡村的大银幕徐徐拉开,站在高处看着舅婆大嫂演绎着她们的故事。
拈花一笑,看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