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何为谏官?
谏官又称为“谏臣”,其主要职责是规谏君王避防过失,谏臣与御史大夫在朝中起着谏察功能,谏臣侧重于“谏”,劝谏君王;御史大夫侧重于“察”,负责监察百官,二者皆在政治管理系统中其纠错作用。
为什么叫“谏官”或“谏臣”呢?
中文的“谏”包含多重含义,如《说文》释其为:“谏,证也。从言柬声。”《白虎通》史其为“闲也,因也,更也”。《广雅·释诂一》曰:“谏,正也。”《广韵》思其为谏诤,指“直言以悟人也”。《字汇》曰:“谏,直言以悟人也。”《书·说命》认为从谏则圣。
在这些解释中,“谏,直言以悟人也”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传达了谏臣之“谏”的主要涵义。
典籍中,还有不少对“谏”做出解释的,比如,《礼·曲礼》认为:“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随之。”在这里,臣可谏君,子可谏父,三次谏君而不听,就要适可而止,不要再劝谏了;子三次谏父而不听,只好哭泣着跟随着父了,孝是需要守的。
唐代著名谏臣王珪画像
宋代对谏官制度是比较重视的,专门从门下省分出谏院与“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并行,以左右谏议大夫为主官,加上门下省的“给事中”,合称为“给谏”。
宋代还将唐时的“补阙”改为“司谏”,将“拾遗”改为“正言”,皆分置右左官员。所谓的“司谏”乃专司谏诤之职;而所谓的“正言”,乃专门向皇帝直言劝谏。
元代废门下省,谏议、司谏、正言也随之被废掉了,元朝就没有专职的谏官了,谏官的职责让御史兼任。
明代承袭元朝的制度,不设专职谏官,但由“给事中”和各道御史兼任谏官职责,称为“给谏”。
清代承继明代,没有专职谏官,但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两班人马来兼谏官职责。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给事中、监察御史等,都有谏言之责。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皇帝曾下旨曰:“凡事关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大利大害,应兴应革,切实可行者,言官宜悉心条陈奏,直言无隐。”但是,清代的谏言已经与唐宋时不能比了,谏官形同虚设。
综上所述,自周设立谏官(保氏)之后,从春秋战国至唐宋,朝廷对谏官都是比较重视的,而唐代的谏官制度是最为健全的,谏官制度作为劝谏、牵制皇帝的制度,从运作机能上看是与皇权有矛盾的,而这因为这一矛盾,使谏官制度成了最有积极意义的对皇权起牵制功能的重要制度。虽然由于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的限制,谏官制度的牵制作用是有限的,但它毕竟一项合法合理的牵制制度,历朝历代大义凛然的谏官们的犯言直谏,对于皇帝决策确实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纠错作用,这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延续长久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唐初魏征等谏臣对于唐太宗的直谏,显然对于贞观盛世的形成是起重要作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前,谏官与察官是分立的。谏官司言,御史司察;谏官掌规谏讽谕责权,献可替否之策,御史掌纠察官邪之权责,旨在肃正纲纪;谏官主责是劝谏皇帝,避防误断,御史主责是监督百官,纠弹大臣。唐宋时期,谏官与御史的职责比较明显,唐代御史不得谏劝,谏官则不得纠弹。宋代初期,御史与谏官各有其责,互不兼领职务,不过,宋代谏官也有利用劝谏皇帝而间接地纠绳宰相的,宋中期之后,三省百事事有违失,谏官也有谏正之责。
所以,谏官制度在唐和宋初发展得比较成熟,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谏官对于皇帝的劝谏作用也比较有效。
第三,谏官的待遇以及权与责
谏官的俸禄和官爵在各个朝代有所差别,但与朝廷高官和权臣相比,是比较低的。比如,西汉时东方朔,是汉武帝的随身侍从,官至常侍郎,司劝谏之事,他俸禄据说与朝廷的马夫差不多,“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在唐代,谏议大夫的年俸为二百石粟,秩品为正五品,约相当于古代下大夫的待遇。这样的待遇与朝中的大多数高官相比,是比较少的。而且,谏官职务独特,引人注目,其司谏之责使得他不能有任何贪贿行为,不会有俸禄之外的收入。
可以说,清廉坦荡是谏官敢于犯言直谏的底气,谏官一般不司政务,为官职责乃是劝谏,是对君王的规劝谏止和婉言劝说,君王有过失的,包括在选贤任能、奖善罚恶、澄清吏治、军情决断、农耕决策等方面,如有不妥,谏官皆可对之进行规劝。劝谏君王,这是谏官的最主要的职责和权力。
其次,谏官有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情报权力。谏官作为朝廷命官,常常充当民情舆论的代言人,而如果没有情报来源就不知民情,也没有办法劝谏,所以,谏官常常通过各种途径来收集情报。
比如,通过门客、同僚和官场的舆论来收集情报,据史书记载,魏无忌乘与魏王下棋时对魏王进行劝谏,而其劝谏所根据的情报便由门客收集来的。(参看《史记.魏公子列传》)
再如,通过与朝中众臣的交往或与皇帝身边的近侍的交往来获得情报,朝臣的交流所透露的消息常常是谏臣们重要的情报来源,谏臣可以据之以劝谏。
又如,通过深度地参与朝政,积极收集情报。比如,自唐朝武德年间起,谏官奉诏可随朝听政,这让谏官可以及时收集议政决策的信息,这对于谏官是很有利的,能让劝谏更有针对性。
最后,谏官可以通过调查巡视来了解政局、政策状况,了解民情舆论,调查是谏官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调查的方式包括微服私访,包括利用编史书的机会收集信息,包括询问地方官员等了解实情等。显然,有情报才有劝谏的依据,情报越多越准确,劝谏越有根据越有说服力,劝谏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
再次,谏官专司劝谏,有言者无罪的权力。谏官为什么敢于谏诤呢?因为谏官职责就是专门劝谏皇帝的,是专门对皇帝直言的,说对了,皇帝可以考虑接受,说错了,也不会被追究,这即是所谓的“谏言不咎,谏官不罪。”谏官的职责就是直言以谏,而既然直言以谏是其职责,当然就不能因直言而对其加罪。假如谏官说错了便会被处置,那么,谏官就不敢直言了,而不敢直言的谏官还能称为“诤臣”吗?所以,只有话说错了或说出了不合皇帝意愿也不会被杀头或贬官,谏官才敢于犯言直谏。

魏征剧照
对于谏官,皇帝一般是宽容对待的,有皇帝对谏官说:“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谏官言而无罪,这成了古代监察制度的一项惯例,王安石说,谏官之所以敢极言以谏,正因其为谏官,“盖已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王安石《谏官》)
其实,谏官不罪或者言者无罪,这成了封建政治制度的一种礼法制度,在“道统论”或“德治”政治理念的影响下,对谏官不追罪已经成了皇帝的一种道德规范。皇帝如果因谏臣言错或言不符帝意而诛杀谏臣,便是违反“德政”规范,违反礼法的,便会被认为是昏君。所以,皇帝为了让臣民们认为他是明君,他是遵守礼法制度在治理国家的,是不会轻易诛杀谏臣的,即便是皇帝对谏臣的直谏非常不满,也常常要忍下来。
当然,谏官之所以难做,也是因为直谏有被杀头的危险,毕竟,在皇权专制的体制里,帝王的权力出至高无上的,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在乎对于礼法的遵守,谏官的直谏如果超越了皇帝所不能忍耐的程度,如果威胁到了皇权专制,谏官就有被诛杀的危险。
所以,孔子曾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谏官之所以历来坚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就是因为直谏有危险而又不能怕危险,谏官是忠臣,忠臣必须尽忠直谏,“忠臣不避重诛”。历史上有不少敢于直谏而不怕被杀头的谏臣,演绎了壮烈的诤臣风范,受到了世人的敬仰,这是古代社会维护正义的一种杰出表现。
最后,谏臣有谏言不外露的职责。谏臣虽有权劝谏皇帝,但谏臣也有责任维护皇帝的威严,为皇帝保守秘密,所以,谏言不露成了谏臣必须严格遵守的神圣职责。
谏官制度的设置,旨在纠正皇帝的缺失,谏官的使命是发现皇帝的失误或过错,并劝谏皇帝纠正失误决定或改变错误决策。对于开明的皇帝来说,谏官对其决策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开明的皇帝需要谏臣来帮助其纠正失误,皇帝虽贵为“天子”但也不可能永远正确,有时出现过失是难免的。而且,传统的“仁政”学说和“德治”传统,也使皇帝需要维护谏官劝谏的权力,以表明自己是明君。而有了这些理由,谏官的存在也就顺利成章了。
但是,皇帝的失误是不希望让众臣知道的,皇帝的过失是不可以公开的,皇帝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威,需要表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大多数皇帝都没有胆魄和胸怀在臣民面前公开自己的失误。
如此一来,谏官就必须受约束了,因为谏臣知道了皇帝的失误,为了不让皇帝的失误传播出去,便为谏臣立了一项规定,那就是“谏言不露”“谏书人莫窥”。在不少朝代,朝廷都专门规定谏官言事须“密陈其奏”。比如,唐朝时,白居易于《初授拾遗献书》中强调,谏官言事要“密陈所见,潜献所闻”,“密缄于疏,潜吐血诚”。
从皇权专制集权制度的理论需要来看,皇帝为天赐之子,有金口玉言,皇帝的圣旨即是朝廷的法规,是不会有错误的,也是绝不能更改的。所以,当谏官发现了皇帝的失误或过错时,是绝对不能够公开的,否则,大众臣民便会质疑圣旨的权威性和正确性,而皇帝的权威性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如果谏官把皇帝的失误或过错公布于众,史书就会记载下来,这将大大有损“真龙天子”的形象,也将大大不利于封建专制帝王为自己树碑立传。如果皇帝的过失通过史书流传于后世,这对于皇帝权威形象的损毁实在太严重了。
所以,为了防止皇帝的过失被写入史书,唐代专门有一项严格规定:“领史职者,不宜兼谏议”。于是,谏官谏言不外露不仅成为谏官必守的规定,而且也成了谏官的神圣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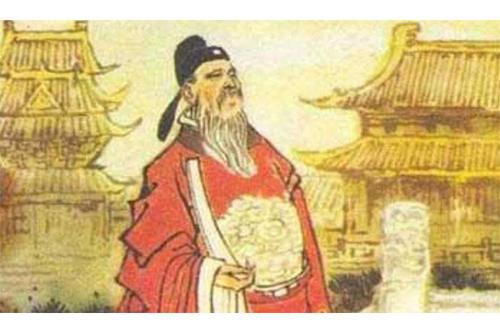
古代谏官画像
第四,谏官制度形成的原因、依据以及存在的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氏族民主制,但进入商、周朝之后,不发达的贵族制以及之后发展起来的君主制,都没有能给予民主决策机制以存在的机会。所以,在中国古代,从商周开始便没有出现民主性的决策机制,相反,在春秋战国时期,专制主义君主制逐步得到发展,而到了秦汉时期,专制主义君主集权制逐渐走向成熟,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
中国古代的专制集权体制实际上是一种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制度,其显著特点是皇帝实际上成了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于一体的最高掌权者。皇帝掌控着议政、决策和行政的最终决断权。
从法制方面看,中国古代皇帝行使权力是不受律法约束的,天下生杀予夺的权力最终归于皇帝,如此一来,皇帝的权力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而事实上,皇帝也有七情六欲,也会有思虑不周的时候。皇帝处理政事时,也是会有失误的,而且,朝政治理的失误往往会危及皇室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而为了弥补皇帝专权独断所可能造成的对王朝根本利益的损害,古代很多朝代便采取了一些纠错措施,其中,谏官制度便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
在中国历史上,谏官制度的设立和运行的确对专制管理体制的起到一定的纠错和制衡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历史上曾涌现过不少“犯颜直谏”的谏官,他们对于皇帝的劝谏有的是其重要作用的,一般来说,皇帝善于纳谏,政治便比较清明,社会也比较兴盛;而纳良谏的帝王,多数是把朝廷搞得很糟,王朝衰落得很快。
其次,谏官制度的形成与古代的“道统论”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与“王道”学说、“德治”理论的传播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道统说”,主要是强调君王要以“王道”理念来治国,要尊循“道统”,实行“德治”,而这只有依照“王道”实行“德治”的君王才是明君。
古代的“仁政”学说认为,治国的管理理念,分“道统”和“政统”,“道统”代表着圣贤们的“德治”理念,而“政统”是君王的治国理念,以儒家为代表的“道统论”者强调“政统”要与“道统”相统一,治国要符合礼制。在他们看来,“道统”比“政统”更尊贵,君王只有让“政统”遵循“道统”,所治之政才是“仁政”。
比如,唐代著名的“道统论”者韩愈就认为,“道统”比“政统”更尊贵,“道统”为儒家的“内圣之学”,而“政统”则为“外王之学”,先“内圣”后“外王”。传统儒家主张“修齐治平”,把“修身”放在第一位,认为心性修养比帝王之术更为重要。
韩愈等认为,圣贤深知天道,传承“道统”,非是帝王可以“政统”来压制的。
有了“道统”的影响,古代开明的君王都知道要遵循道义或依照“天理”来治理国家,比如,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君王必须依照“道统”论的要求来治理国家,王朝不断更替,政权经常在变动,但“道统”却一直有效地传承下来,道义是一直被维护着,君王只有遵循“道统”,尊“王道”行“仁政”,才是贤明的君主。

韩愈画像
韩愈认为:历史上有风骨有志气有担当的士人,都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他们坚持“从道”不“从政”,坚持让“道统”超越世俗政权。而杰出的士人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地维护着“道统”,演绎了可歌可泣的弘扬道义的壮举,广被赞誉,名流青史,这正是因为他们把“道统”视为是社会正义和道德仁义的集中表现。
古代士子们不屈从于皇权,坚持维护“道统”,不仅形成了一种被社会认可的道义力量,这对君王的治政是有影响的。明代理学家吕坤说过:“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
值得注意的是,谏官制度的设立,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管理机制,其实它也是一种道德监督机制,谏官既是体制内的官员,同时又是“道统”理念和道德正义的代表,谏官们之所以敢于坦然面对皇帝,敢于劝谏皇帝,敢于视死如归地犯言直谏,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德治”理念,所以,他们有劝谏皇帝行“仁政”之责。
历朝历代,面对这犯言直谏的谏官,开明的皇帝一般都是宽容对待的,即便是谏官劝谏错了,开明的皇帝也不会下旨处置他们,这当然不是皇帝惧怕谏官,也不是皇帝不讨厌谏官,而是谏官代表着“德治”理念,是施行“仁政”的监督者,皇帝如果随意处置谏官,这便会摧毁王朝的“仁政”理念,会给皇帝带来名誉上的损坏,明君是不会杀谏官的。
再次,谏官制度虽然是以维护专制君主的长治久安为根本目的的,但谏官对于君王的劝谏却表达了对“仁政”的追求,反应着“德治”的理念,并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智慧。
在中国古代,谏官体系负责谏诤封驳,劝谏君王,这种劝谏作用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作为一种对皇帝的“纠错”机制,对于保证政治权力顺畅而健康的运行,是能起一定作用的。也可以说,谏官的设置是帝王管理谋略的一项制度化措施,而这种措施十分利用制度赋予他们的权力来进行“进谏”,同时,他们巧妙地把“仁政”观念和“德治”追求转为为监督的力量,借助道德、舆论的力量来对皇帝形成制衡。
显然,有了道德舆论作为依托力量,谏官不仅有勇气,而且有“底气”,他们在劝谏皇帝时,勇于直言,也常常很有智慧得充分利用“德治”理念来强化劝谏的效果。
在古代皇权专制的集权体制下,谏官制度的设立是必要的,谏官的存在是必须的。专制皇权越是强化,而集权制越是厉害,皇权就越是不被限制、不受制约,所以,更需要有牵制机制纠错,而谏官制度便是极少数被认可的牵制机制之一,当皇权专制权力超越了律法和议政、行政制度时,谏官制度的运行就变得尤其重要,谏官担负着重大的劝谏责任。因为谏官可以借助于“仁政”观念和“德治”诉求来劝谏皇帝,这是皇权专制体制下所能容许的极少监督方式之一。
当然,谏官的劝谏也需要有约束的,一是谏官要自觉以“德治”原则作为劝谏的依据,不能扶风捉影,胡乱“进谏”,不能以虚为实,“闻风奏事”,而要“据实指参”(康熙语);二是谏官要在律法和制度的规范下进行劝谏、直言,如果谏官有法不依,有章不遵,仗着自己有道德舆论力量的支持而在帝王面前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捞取政治资本,那么,这将使劝谏行动完全变了质,谏官将完全违背原来的宗旨,成了利用谏言特权而瞎胡闹的不靠谱的佞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