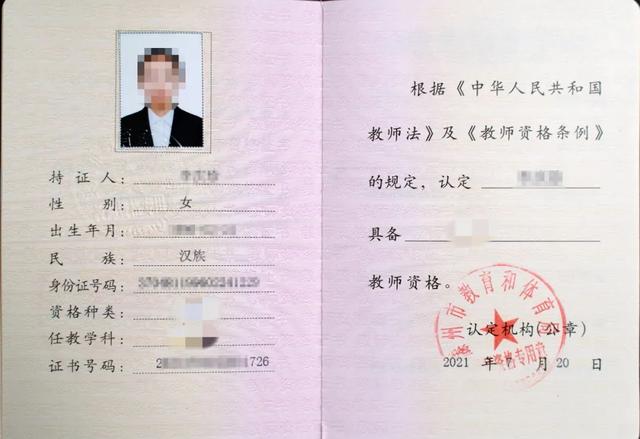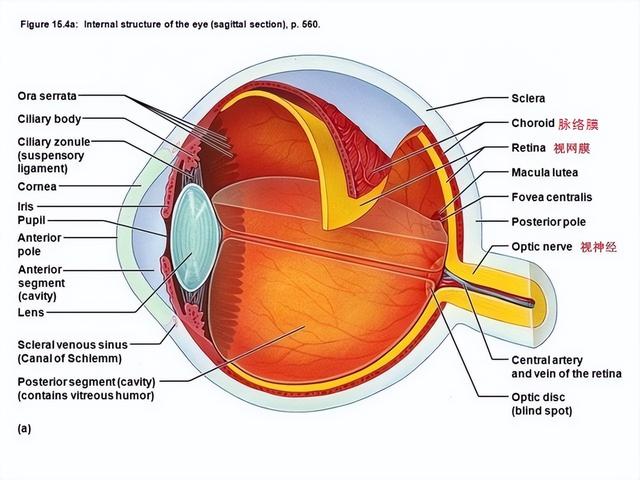以上我们对《大学》“诚意”章做了梳理,尤其对慎独做了考察,指出自郑玄、朱熹以来的误读。独并不是空间的概念,而是内在性的概念,是内在的意志、意念,是真实的自我。诚意是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学》提出诚意,意义何在?我们知道,儒家是积极入世的学说,入世有很多方式,如教育、经商、做工等等,但在孔子的时代,最重要的入世方式是出仕。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有隐者讥讽孔子,劝孔子的弟子与其跟随孔子避人,不如跟随自己避世。孔子怎么回答?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就算社会有种种不完满,我们总不能退回去与禽兽相处吧?你不与人类相处,还能与谁相处呢?这样我们的选择只剩一个,就是积极入世,把一个不理想、不完满的社会,改造得较为理想,较为完满。正因为天下无道,还不完满,所以才需要我们去治理,去改变它嘛。怎样去改变?首先当然是要改变自己,通过修身使自己成为一名君子,有机会的话,应积极出仕——出仕不是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而是去实现改造、完善社会的理想。这样由修身做起,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明明德于天下”。所以改造社会的动力在于“己”,只有从修身、成己做起,才有可能改造、完善社会,所以孔子讲“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而修身、成己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诚其意,是慎独。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既然积极入世,就不能不面对各种社会关系,面对既定的礼义秩序。所以有一些学者,例如安乐哲先生,把儒家伦理称为角色伦理,把儒学解释为关系主义。儒家确有重视关系的一面,如孔子就非常重视礼,这点与道家有所不同。当年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你所问的事情,人都早已死了,他们的骨头都朽了,只有他的话还留着。所以礼是过时的东西,已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而孔子则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认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礼就是一种关系性概念,指规范、习俗,成就仁需要从实践礼义做起。孟子重视人伦,一个人如果为了洁身自好,而否定了人伦,孟子是不能认可的(见《孟子·滕文公下》6.10论陈仲子)。荀子认为虽然人的力气不如牛,速度不如马,但却可以驯服牛、马,为我所用,原因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所以人与禽兽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人是能群的动物,而群就是组织关系,是由不同角色的人组成的。所以儒家确有重视角色、关系的一面,但这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若将其称为关系主义,就不正确了。儒家在讲关系的同时,还讲己,讲独,讲真实的自我。如果没有“己”,没有自我,又如何能去改造社会呢?不是完全被社会同化、左右了吗?儒家恰恰不是这样,越是积极入世,越是深入到社会,越是提醒自己,我们还有自我,还有独。诚其意、慎独是修身的核心内容,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就被社会所塑造,所以认识自我是一件十分困难,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各个民族都曾面临的问题。在希腊圣城德尔斐神殿上刻着一句著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这是从神的角度讲的,从人的角度讲,就是“认识我自己”。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展开他的哲学思考的,让哲学重新关注“人”的问题,关注自我的问题。印度有一位叫克里希那穆提的哲人,讲了下面一段话:
弄清楚我们想做什么是世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不但在青少年时代如此,在我们一生中,这个问题都存在着。除非你亲自弄清楚什么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否则你会做一些对你没有太大意义的事,你的生命就会变得十分悲惨 。不是吗?因为你一旦发现真正爱做的事,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了,然后你就会有能力、信心和主动创造的力量。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真正爱做的是什么,你只好去做人人羡慕的律师、政客或这个那个,于是你就不会快乐,因为那份职业会变成毁灭你自己及其他人的工具。(克里希那穆提著,叶文可译:《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
我引这段话就是想说明,认识自我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又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儒家主张积极入世,改造社会,但又强调首先要从修身、成己做起,所以首先要承认,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去追求这个真实的自我,这样才能进一步去改造这个社会。儒家承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合理性,它是入世的,而不是避世的。但承认不等于无条件的认同,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理解孔子所讲的:“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在《论语》中,只记录了这一句,没有展开。百年之后,在我们今天邹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位儒者,就是孟子。他对孔子的这句话感同身受,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撼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是引孔子的话,说从我的门前经过而不登堂入室的人,如果说我不感到遗憾的,大概只有乡愿了吧。为什么呢?因为乡愿是“德之贼也”,是对道德的最大伤害。孔子作为一名老师,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登门求教,但乡愿除外,可见乡愿不是一般的缺点,而是不能容忍的恶行,以至于连孔子都不愿与其为伍。其实孔子的道德标准并没有那么严苛,他的理想首先是与坚守中道的人相处,如果遇不到中道之人,也可以退而求其次,与狂者、狷者相处。狂者的特点是志向远大,经常以“古之人”相榜样,但实际往往又做不到,言行有不一致之处;狷者虽然没有那么高的理想,但能做到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狂者过之,狷者有所不及,都没有做到中道,没有达到中庸的境界,但都有可取之处,可以相处、来往。最可恨的就是乡愿了,他们得过且过,取悦于世人,却讥讽别人志向远大。他们很会做人,谁也不得罪,所以在乡里往往有好名声。乡愿,从字面上看,就是乡里的老好人。但他们的可气之处也就在这里,你说他不对吧,却找不出毛病;想责骂他吧,可是又没有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他很会做人,混同于流俗,迎合于浊世,为人表面上忠诚老实,行为好像也清正廉洁,所以在乡里有不错的声誉。但是这种人,你没法跟他去实践尧舜之道,没法要与他去追求理想。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孔子包括孟子憎恨乡愿的原因所在。乡愿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原则,没有自我,他们对于现实是无条件地认同和附和。你想与他谈谈理想,谈谈如何改造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儒家虽然不否定现实人生,但并不认为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就是完满的,相反是需要我们加以改造的。所以孔子一生崇尚道、追求道,道就是最高理想,懂得了道,才可能明白人生的意义何在,才有可能去改造社会,所以“朝闻道,夕死何也”(《论语·里仁》)。可是这些恰恰是乡愿做不到的,他们只会混同于流俗,不懂得还有更高的人生目标,还有道和自我。

追求道就必须有内在自我,有道德主体,所以孔子教导弟子要“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泰伯》),“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子罕》)。志就是独,是内在的意志,是真实的自我。孟子讲“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先把心确立起来,耳目五官就无法夺取你的心志。所以“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上》)。“缩”是直的意思,“不缩”就不直,也就是理亏。“褐宽博”,指褐布做的宽大的衣服,这里指穿宽大衣服的人,也就是卑贱、地位低下的人,类似我们今天说的乡巴佬。“惴”是恐吓的意思。自问理亏,并不占理,即使面对着地位低下的人,我也不恐吓他,不会仗势欺人。自问理直,真理掌握在我的手里,即使面对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不会被你的权势所吓倒。这就是独,指内在意志,真实的自我。荀子虽然讲群,但同时也讲诚,讲慎独。所以在儒家那里,是有一个重视独,重视真实自我的传统的,《大学》的诚意慎独,只有放在这个思想脉络中,才可以得到理解。
儒家重视群,但同时也讲独,所以不能把儒学简单理解为角色伦理、关系主义,儒学是群与独的统一,不是在群与独之间取其一偏,而是保持中道。到了近代,章太炎先生写过一篇《明独》的文章,对群与独的关系做了很好的总结,他提出“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大独”,真正的独,也就是真实的自我,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个体并不是与社会相隔绝,不是遗世而独立,做桃花源中的隐者,而是在社会中成就、完成自己,同时也完善、改造着社会。不能参与到社会之中,不能与人群的,就不是真正的独。同样,“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群是由真正的个体组成的,一群奴隶是无法组成群的。专制社会不准人们发展独立个性,把个人变成家族、宗派、山头、地域等宗法封建关系的附属物,只能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造成无数国中之“国”,是对社会的最大危害,“小群,大群之贼也”。只有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的真正个体,才能形成真正的群,建立起现代的国家,“大独,大群之母也”。胡适先生后来也讲,“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器,使自己有了足够的知识、能力与感情之后,才能再去为别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器》),“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也是这个思想。
所以说儒学有重视人伦关系、礼义秩序的一面,这是与其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相适应的。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儒家也有重视独,重视个体,重视人的意志自由的一面,这是其理想主义人生追求的内在根源和动力。所以我觉得章太炎先生的概括非常好,“大独必群”,不能只讲独不讲群,这样的独只是消极的独,不是积极的独;“群必以独”,真在的群只能由独立的个体所构成,现代的国家只能由自主、独立的公民所组成,这才是我们今天读《大学》慎独诚意章的精义所在,对于《大学》慎独的“独”必须这样去理解。相反,如果把“独”理解为独居独处,思想境界就低了,也不符合《大学》的原意。

来源:“新四书”公众号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