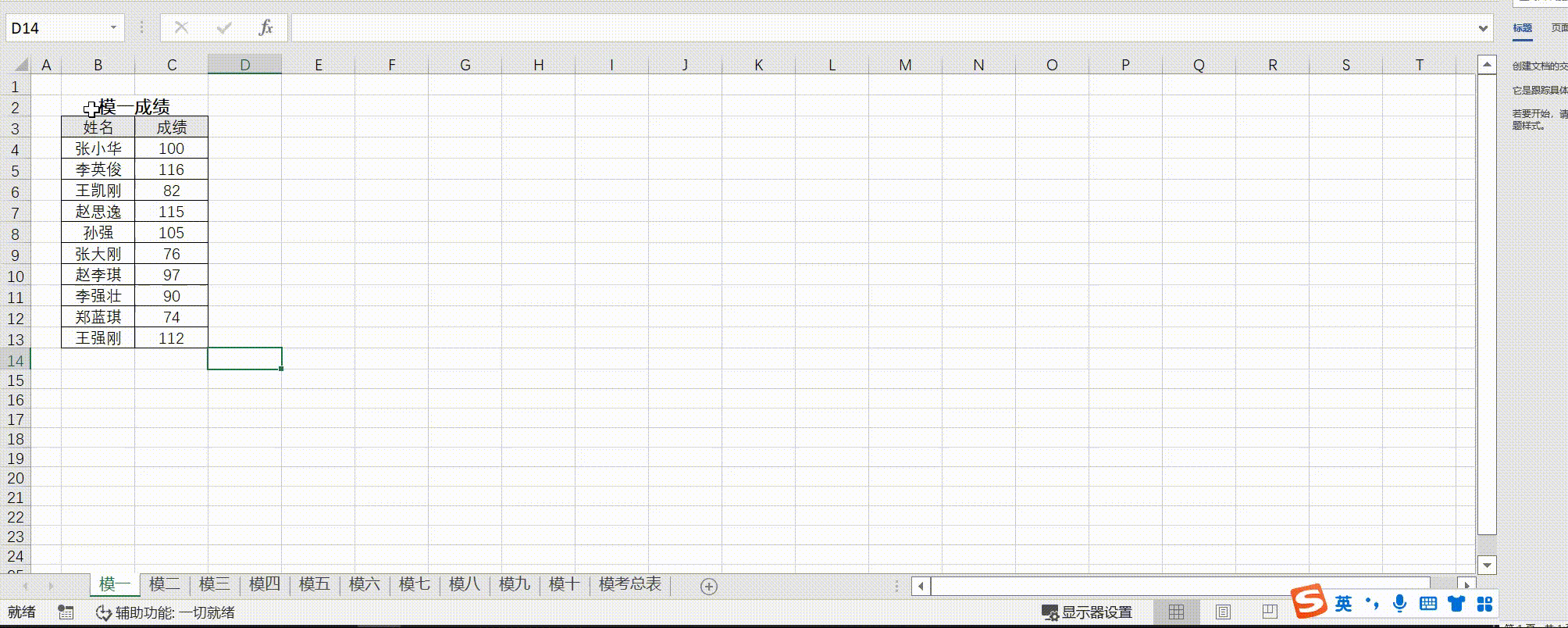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历史中,交织着鸦片在这些地区的种植、贸易和消费,以及由此引发的亚洲政治经济局势之变迁。鸦片不仅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的一个创伤,也是诸多中外史家反复书写的对象。然而,不断出现的鸦片史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近代亚洲毒品史的一个重要面相——合成毒品的历史。而那些合成毒品中尤为特殊的一种是当前依然困扰世界诸国的可卡因问题。言其特殊,主要原因之一是可卡因是一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被分离出来后迅即受到世界亲睐的“药物”,继而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之后迅即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管制。英国斯克莱德大学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s)教授治英国毒品史经年,于2016年联合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等国内外数位学者成功申请由英国维康基金(Wellcome Trust)资助的项目“亚洲可卡因危机:东南亚的药物、消费者和管控,1900-1945”。适值该项目进展一周年之际,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医疗社会史中心和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在维康基金的资助下,召集了英国、荷兰、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于2017年10月9-10日在上海大学召开工作坊,就各自以及此项目的研究进行了研讨。

工作坊现场
作为“亚洲可卡因危机”项目组成员之一,笔者有幸参加了此次工作坊并聆听了各位学者的报告。工作坊的内容之一是项目组成员就各自的研究进展所做的汇报。英国斯克莱德大学的帕特丽夏·巴顿博士(Patricia Barton)专长印度的瘾品以及药品史,此次工作坊,巴顿博士做了题为《“除了可卡因这个名字我们一无所知”:印度和早期禁毒立法中瘾品知识的建构》的报告。巴顿博士的视角是关于可卡因的医学知识如何在不同时期的医生之间传播,以及构成禁毒立法的知识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印度医生丘尼拉利·博斯(Chunilal Bose)于1913年发表的关于可卡因的言论在1935年被印度药理学之父拉姆·纳特·乔普拉(Ram Nath Chopra)引用,而其1935年的部分言论被稍加修改发表于1957年。更加饶有趣味的是,乔普拉的言论不仅被印度相关禁毒立法所参考,甚至构成了国际毒品管制立法的知识基础,而其源头却是数十载之前的“研究”成果。因此,巴顿博士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国际禁毒政策专家们所凭依的其实是过时的信息。“亚洲可卡因危机”项目组的两位博士后韦达·巴鲁阿(Ved Baruah)和阿尔诺·勒尔斯基·范德霍格特(Arjo Roersch van de Hoogte)都以《亚洲和全球可卡因网络》为题做了报告。虽是相同的题目,但二者聚焦的地区不同,韦达关注的是可卡因在印度的历史而阿尔诺关注的是可卡因在欧陆的历史,有趣的是,二者的研究视角也颇有区别。韦达基于目前已经搜集到的档案资料,分析了1905至1935年可卡因在印度的走私、消费、政府管控以及管控政策面临的困难和实施结果。韦达的研究表明,二十世纪初期,印度的可卡因起初主要从欧洲经由海路运入。日本产可卡因于二十世纪十年代出现于印度,并与二十年代中期形成垄断市场。从二十世纪初期至四十年代,法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是可卡因走私的“枢纽”,英国的相关控制政策面临了挑战。与韦达“生产—消费—管控”的研究路径所不同的是,阿尔诺的视角则是诸如德国拜尔公司等欧洲制药企业的相关活动,以及它们的活动对于彼时亚洲可卡因市场之形成的推动。基于从德国、英国和瑞士所搜集的档案资料,阿尔诺认为,与彼时亚洲所消费的可卡因相关的制药公司共有四家:德国的E. Merck和C.H. Boehringer,英国的Howard & Sons和T. Whiffen & Sons,以及瑞士的F. Hoffmann-La Roche。Howard & Sons的可卡因生产截止到1920年,而E. Merck至少在1925之前是彼时亚洲消费的可卡因最主要的生产商。较之上述五个公司更小的一些的公司,如European Trading Co 和 Bubeck & Dolder是重要的可卡因以及其他麻醉剂的供货商。这些小公司是彼时可卡因制药商和转运商之间的媒介。截至到大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亚洲消费的可卡因主要来自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制药企业。阿尔诺认为,针对可卡因的管制失效,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相关的管制政策无法有效落实。其二,制药企业以及销售公司们所结成的网络有效地保证了可卡因的供销。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了一种“集体不服从”,也即对既有政策的无视。此外,项目组的两位博士生迈克·德弗里斯(Maaike de Vries)和黄运也分别就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期朝鲜半岛和中国可卡因的历史的研究做了报告。
“亚洲可卡因危机”项目主要负责人詹姆斯·密尔教授(James Mills)在工作坊的开幕发言中指出,“参加此次工作坊的各位学者的报告不一定是关于可卡因历史的研究,甚至有些也不是关于亚洲,但是他们是各有专长,这也将给此项目的进展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及洞见。”近代亚洲毒品史的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是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米利亚姆·金斯伯格·卡迪亚教授(Miriam Kingsberg Kadia)关注该领域多年,著有《道德国家:现代日本和全球史中的麻醉剂》(Moral Nation : Modern Japan and Narcotics in Global History),此次他另辟蹊径,着眼于1918年至1948年日本文学作品对鸦片的书写。卡迪亚教授依次考察了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告白》在日本的译介,以及日本文学作品《指纹》、《鸦片夫人》、《上海》、《陈夫人》和《归乡》的出版。卡迪亚教授认为,这一时期日本文学中鸦片书写的繁荣赋予了鸦片一种折射的功能,借助于“种族”和“民族”这两个概念,鸦片折射了日本彼时逐渐改变的全球地位和愿望。可是为什么这一时期关于毒品的文学作品更多的以鸦片而不是其他毒品为主题呢?卡迪亚教授认为原因在于彼时的日本人以及西方人将中国人污名化为鸦片的吸食者,没有什么毒品比鸦片更能将中国人标签为劣等民族,而劣等的民族也就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需要清理的对象。所以,这样的文学书写既与当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相关联,也成为“合法化”日本在亚洲统治的必要工具。此次工作坊中关注日本在近代亚洲毒品史中之活动的另外一位学者是来自美国的凯瑟琳·梅耶尔教授(Kathryn Meyer)。梅耶尔教授此次报告了《日本在华鸦片专卖制度及其难以实现的诉求》。在她看来,日本在华鸦片专卖制度固然是彼时日本敛财养战的工具,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首设于台湾的鸦片专卖制度的初因是为了逐渐减少鸦片成瘾者的数量,这和当前国际上毒品政策中的减少伤害(harm reduction)政策颇为类似。而后该专卖制度才演变为支持其侵虐扩张的工具并被推广到中国东北和当时热河地区。
除了涉及日本在近代亚洲的制毒贩毒史,此次工作坊更有两位学者以自己的史学研究参与了当下欧美世界热议的大麻合法化争论。来自加拿大的教授丹·马莱克(Dan Malleck)做了题为《超越种族:在大麻合法化之际审视加拿大毒品立法的影响》。马莱克教授分析了二十世纪初期加拿大禁毒立法(1908年《鸦片法案》以及1911年《鸦片和麻醉品法案》)的缘起及其影响。1907年加拿大唐人街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暴乱,次年加拿大出台了《鸦片法案》,1911年吗啡也被加入管制之列。在此报告中,马克莱教授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结论,而是指出彼时逐渐增强的反华情绪、毒品消费和毒品立法之间存在关联。同时,他抛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鸦片的大量书写是否弱化了我们对于其他毒品的关注和史学写作?二十世纪初加拿大的毒品立法中的种族因素是如何体现的?著有毒品史研究经典之作的《二十世纪的毒品外交:一项国际史》的美国学者威廉·B.麦卡利斯特(William B McAllister)在此次工作坊做了报告《国家安全的考量如何形塑了美国1937年〈大麻税法〉》。麦卡利斯特认为关于美国1937年《大麻税法》之缘起的既有研究缺乏说服力,而他本人通过细致的档案爬梳,发现这一立法的起源其实是确保当时马尼拉大麻(Manila fiber/Manila hemp/abaca)这一战略物质的供应。除了上述关于瘾品史之多维度的研究,此次工作坊更有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朴世英(Saeyoung Park)博士对既有的瘾品史研究所做的批评。在题为《“长时段”如何破坏了生活:基于阿伦特档案的研究》的报告中,朴博士指出既有的瘾品史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学界过于关注瘾品管控的历史,抑或以国家建设为路径的研究占了主角,而从消费的视角进行研究的作品却很少。其实,国际学界关于瘾品史的研究自上世纪末期起,已经出现了一种转向,即更多地关注瘾品之消费者,以及社会文化史的路径。朴世英博士的呼吁可视为是对这一瘾品史研究趋势的呼应。
此次于上海大学召开的“亚洲可卡因危机”工作坊,既召集了该课题组相关成员汇聚上海,分享各自的研究进展和信息。同时,它也聚集了国际治瘾品史的诸位杰出学者,为学界呈现了他们新近的研究动态,以及对于“亚洲可卡因危机”这一课题乃至瘾品史研究的新思考。种种思考,既得益于诸多新资料的挖掘和利用,也源于新研究路径的出现。除此之外,更有对既有的瘾品史研究所做的史学史回顾和理论思考。此次工作坊的召开不仅有助于推动“亚洲可卡因危机”这一课题的进展,对国内外学者的对话以及瘾品史研究的再思考都裨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