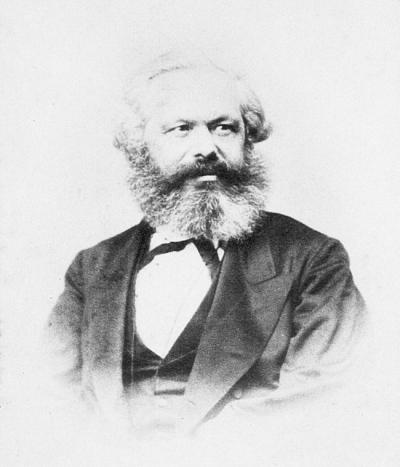7月15日,深圳公布了“5·18”赛格广场大厦振动事件调查结果,专家组认为:桅杆风致涡激共振和大厦及桅杆动力特性改变的耦合,造成了赛格广场大厦的有感振动。论证过程非常技术流,在此不赘述,但结论是:赛格广场大厦在设计荷载范围内和正常使用情况下主体结构是安全的,可继续使用。
尽管如此,对于在大厦内上班的职员以及亲眼目睹大厦摇晃的公众来说,大楼摇摆的恐惧感怕是短时间内难以消弭。
赛格大厦有79层、高355.8米(一说72层、高345.8米),兴建于2000年,建成时高度是深圳第二,不过如今已经跌到了第八。21年来,摩天大楼的高度不断被刷新,深圳第一高楼几经易主,如今暂时交棒到了2016年竣工的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手上,高度为599.1米。据悉,目前深圳还有一栋在建高楼——深港国际中心,建成后将达700米,有望成为全国第一高楼。
深圳是摩天大楼建设潮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对于高楼的青睐,已经延伸到二三线城市。根据美国高层建筑与城市住宅委员会CTBUH的数据,2015年以来,像深圳赛格大厦这种级别的高楼(350m-400m),南京、青岛、大连、武汉等均有建成,有的城市还不止一幢。
不过,这种趋势或将得到遏制。7月6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明确指出,严把超高层建筑审查关;并明确几点事宜,如对100米以上建筑应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等。
其实,不止是中国开始限制高楼,中国发展网小编梳理后发现,世界范围内,200米以上高楼的建设速度都在下降。从争建“第一高”到限制建高楼,某种程度上,既回归了建筑的理性,也体现了文化的自信。
城市最快被“看见”的方式之一
提起摩天大楼,你会想起哪座城市?
纽约的帝国大厦、世贸中心,吉隆坡的双子塔,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阿联酋的迪拜塔、上海的“厨房三件套”、香港的环球贸易广场……



由上至下依次为纽约帝国大厦、吉隆坡双子塔、迪拜塔(图片来源:网络)
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提到摩天大楼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不是它们的名字,而是其所在的城市、国家。论名称,这些高楼的起名规则通常很乏味,范围(如“世界”“全球”“国际”)、领域(如“贸易”“金融”)、开发商或客户名称(如“中信”“平安”“绿地”)、大楼别称(如“中心”“大厦”)……大概率这些词排列组合一下就可以得出高楼的名称。反而是它们所在的城市、国家,更容易脱颖而出。
摩天大楼,往往因其“高”而成为所在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因其“更高”而使得所在城市被更多城市所看见。这种“知名”方式看似简单粗暴,但背后其实需要有经济基础、技术能力、设计美学等一系列综合实力作为支撑,因此往往对应着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崛起、发展和繁荣。
香港,是我国最早建起摩天大楼群的城市。
香港岛北侧湾仔到中环一公里多的地段,堪称全世界高楼大厦最密集的地区。香港第三高的大厦中环广场大厦就位于这一带,于1993年建成,高374米,78层。2003年香港第二高的大厦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建成,楼高420米、88层,是恒基集团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总部所在地。国金二期成为香港财富的象征,是港岛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到2011年,位于九龙一带的环球贸易广场落成,与国际金融中心隔维多利亚湾相望,并以484米的实际高度成为香港至今为止的“第一高”。

从左至右依次为香港中环广场、国际金融中心二期、环球贸易广场(图片来源:网络)
深圳,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同时也是大陆的“摩天大楼之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这样描述深圳的摩天大楼群:“当你走过香港外围的荒地和鱼塘时,你的眼前仿佛出现‘海市蜃楼’景象:远处矗立着由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组成的大墙。这就是在不到40年内由小渔村变成主要金融和科技中心的深圳。”
根据CTBUH发布的报告,2017年,深圳建成12幢摩天大楼,比全美国的总数(10幢)都多。2018年,深圳建成14幢高楼,占全球总数近10%,连续三年成为世界上完成200米及以上建筑最多的城市。
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摩天大楼数量也很可观。
1999年竣工的上海金茂大厦曾经是中国大陆最高大楼,高达420.5米。而如今,在其附近,已经矗立起另两座摩天大楼——上海中心和环球金融中心。三楼比肩,外型酷似开瓶器、打蛋器和注射器,被网友调侃为“厨房三件套”。其中,最高的上海中心也是全国最高大楼、世界第二高楼,建筑主体119层,总高632米,于2008年动工, 2016年全部完工,历时将近8年,耗资148亿。

被网友戏称为“厨房三件套”的上海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图片来源:网络)
实际上,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比肩林立的写字楼和商业中心拔地而起,使得城市天际线被一次次刷新。现如今,中国已成为摩天大楼总量最多的国家。根据CTBUH公布的最新数据,包括在建、已经建成和有规划的超高层,我国300米以上的超高层有400多座,超过全球总数的1/3。
摩天大楼群的“下沉”
先来看一张中国摩天大楼排行榜:

而在CTBUH的最新排行榜中,小编发现,前10名中即将有3名强势插入:南京的绿地金融中心、苏州的中南中心和西安的丝路国际中心均已开工,理论上将在未来三四年内建成。它们的高度均在500米左右,超过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本图为Skyscraper Source Media截图,数据未纳入台湾地区,红框里的3个为在建状态。)
可以看到,不同于第一张排行榜中清一色直辖市、一线城市的布局,新进入的摩天大楼都分布在二线城市。这些城市正在接替一线城市,成为高楼建设的主力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宋晔皓教授认为,建设超高层建筑,对于今天建筑技术蓬勃发展的中国而言,实际上已经没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门槛;同时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足以支撑耗费巨资兴建高度超过500米的超高层建筑。除此之外,如前所述,500米超高层建筑本身具有一些独特优势,比如震撼的视觉冲击力、极强的地标效应,因此可以吸引到决策方投巨资兴建。
简而言之,如今中国已经发展到二三线城市都可以具备建设摩天大楼甚至是超高楼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了。但是,有“能力”就意味着“能够”吗?
超高层建筑的三个“不能够”
2009年,媒体就曾报道过当时全国各地争建高楼的“盛况”。

2016年,媒体报道再次发出“隐忧”之叹,认为各地的争建潮已更多偏向不计后果的面子工程。
“目前,国内二、三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的土地稀缺度和公司密集度,远到不了需要修建四五百米摩天大楼的程度。但现在三四线城市竟要建造超过500米的洲际金融中心,我认为这种摩天大楼竞赛,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建立地标,动机是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财经评论员陈东海在当时长江商报的一篇报道里说。
同一篇报道中,长江商报记者也发现,一些地方政府确实为城市天际线竞争设计了令人瞠目的优厚条件。2012年8月,广西某市下发了一份“促进超高层建筑项目建设发展的意见”。文件中称:若超高层建筑超过300米,按现行规定计算150米以下部分的容积率,并依此计算土地出让价款,150米以上部分不计土地出让价款。
这种盲目攀比、跟风建设,首先肉眼可见地造成了第一个“不能够”,即建设期的不能够——拖延、烂尾。
苏州301.8米的“东方之门”,从2003年招标、2004年奠基,一直到2008年开工建设,建设进度一拖再拖,其间一度传出资金断裂、出售股权、大楼易主的消息,投资从45亿增加到90亿,整体交付时间也从2013年10月不断延后,最终2015年8月才封顶,建设周期长达11年。
天津117大厦,以596.5米的高度号称打造中国第三高楼,总投资接近700亿,但从2008年开始动工至今,耗时十多年,竣工仍遥遥无期。

天津高银117大厦,在过去的12年中经历了几乎所有危机—停工,复工,资金短缺,转让等等。盛名之下,命途多舛。(图片来源:网络)
其实,对于超高层建筑来说,即便理论上、预期上能够,但由于建设周期较长,期间遭遇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建设风险也较大,甚至可能会遭遇经济危机或者资金链断裂等情况。
劳伦斯魔咒
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在1999年提出过一个概念——“摩天大楼诅咒”(亦即著名的“劳伦斯魔咒”)。他发现:“摩天大楼立项之时,是经济过热时期;而摩天大楼建成之日,也就是经济衰退之时”。他的判断是,建筑热是一个信贷过剩的信号,与信贷宽松、土地价格飙升和过分的乐观预期紧密相关。

4座摩天大楼与 “劳伦斯魔咒” 图片来源:GA环球建筑
如果闯过了建设关,那么接下来就该面对维护成本、消防隐患、安全风险等关卡了,从而造成了第二个不能够,即建成后的“不能够”——维护不起、安全堪忧。
有资料显示,建筑物高度超过100米后,不仅建造成本急剧增加,而且维护和管理费用巨大。
1999年投用的上海金茂大厦高420.5米,幕墙有0.8万平方米。2010年时有人做过测算,据说两架擦窗机连续工作,一年才能把所有的玻璃擦一遍,而且,由于建筑外形凹凸起伏太大,擦玻璃需要爬坡过坎,相当困难。除此之外,要维持其内部的正常运行,每天的管理维护费就达100万元。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根本无法驾驭这个庞然大物。

上海金茂大厦(图片来源:网络)
而消防隐患则是另一个日益突出的高楼难题。出于安全考虑,消防疏散是超高层最需要解决的设计难点。摩天大楼疏散路径、疏散宽度有限,很多时候得依赖建筑内部自动消防设施灭火,或者集中到避难层等待救援。但是,目前消防车的最高作业高度是100多米,这还是在确保作业场地以及承载前提下的数据,实际面对火灾时,消防车的有效扑救高度仅为50米以下。此外,还有诸多不利因素形成扑救障碍。例如,大面积玻璃幕墙在内部高温烘烤下,向外爆炸,玻璃碎片横飞形成的玻璃雨有如刀剑横飞,使外部消防战斗队伍无法靠近等等。
最后,如果有钱任性、胆大包天,那么高楼的体验感也是差强人意,从而造成了第三个“不能够”,即使用阶段的不能够——大风摇晃、交通不便。
今年5月深圳赛格大厦的摇晃并非个例。据新闻报道,我国上海、南京等地,均出现过摩天大楼晃动的情况。2013年2月8日中午,位于陆家嘴的上海信息大楼里,身处20层以上的人员感受到间断性的晃动。9月4日下午,江苏南京新街口一栋50层高的写字楼发生多次较为明显的上下抖动,断断续续持续1个小时左右。
超高层结构为高耸细柔结构,承受的风力载荷很大,因此会产生摇摆现象。虽然这种摇摆不会使建筑物本身发生危险,却会使大楼里的人产生类似“晕船”的反应。此外,超高层建筑使用期较长,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身抗力的衰减可能造成不可预料的突发事件发生。
交通方面,一座摩天大楼承载的人口之多,就像是一个空中社区。那么多人集体上下班,意味着不仅对外增加公共交通压力,而且对内也增加电梯承载与运行压力。一旦出现某一环节的“抛锚”,那么就只能选择感受爬楼心酸或者体验人肉饼干了。
摩天大楼热,有区别的降温
2018年之后,中国的摩天大楼热开始降温了。
根据最新数据,2020年,虽然中国的建造数依然超过全球半数(56座),但与2019年的57座和2018年的92座相比,已经有所下滑。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摩天大楼特别是超高层建筑的华而不实,对此,政策层面也有积极体现。
2020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其中提到: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而在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中,则由去年的“一般不得新建”继续收紧为“不得新建”,寥寥数字差别,却体现出国家对于超高层建筑建设的日趋严格。
当然,政策为500米以下的摩天大楼仍留了一个口子,要求对100米以上建筑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与城市规模、空间尺度相适宜,与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确需建设的,要结合消防等专题论证进行建筑方案审查,并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备案。
毕竟,在人口密集的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向天空要空间仍然是解决人地矛盾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摩天大楼更容易出现在北上广深以及香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那些人地矛盾不那么突出的二三四线城市,要不要建摩天大楼、建多少高度的摩天大楼,则需要审慎探讨。
“世界最高摩天大楼有一个‘肮脏的小秘密’”,美国《大众科学》杂志称,超高建筑很高,但未必是为了尽可能容纳更多人,有时只是一味追求高度,甚至为此在顶层部分做文章,也因此有了 “虚荣的尖顶”说法,用以形容使摩天大楼大幅增高但实际空置的空间。
当曾经的摩天大楼爱好者们(欧美发达国家)都在退出高楼之争,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摩天大楼:城市未来的模样,不应该只有高度;城市的高度,不应该只体现在“虚荣的尖顶”。(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 刘维综合报道)
参考资料:
《各地争建“第一高楼” 科学限高迫在眉睫》,中广网,2009
《华而不实的高楼竞赛:摩天大楼建造成本维护更高》,经济纵横,2010
《中国城市建“摩天大楼”热潮隐忧》,搜狐焦点,2016
《全球高层建筑报告》,世界高层建筑与城市人居委员会(CTBUH),2017-2020
《摩天大楼,说不尽的是与非》,环球时报,2018
《“劳伦斯魔咒”概念20周年,4座摩天大楼见证全球经济兴衰》,GA环球建筑,2019
《深圳赛格大厦355米,在深圳也排不入前五,中国到底有多少高楼?》,商业评说,2021
《不得新建500米以上高楼,大多数二线城市摩天大楼梦已碎?》,国民经略,2021
《告别摩天大楼,这些城市高楼梦碎,为何城市建筑要限高》,反手猴说房子,2021
《为何要严令“限高500米”?专家:应遵循城市环境科学决策》,中国科学报,2021
《消失的深圳“摩天大楼”》,湾区评房论市,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