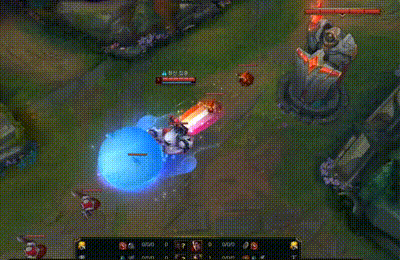“权臣”一般指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在金国除了皇帝拥有交聘决策权外,某些“权臣”也分享了交聘决策权。
金国这些拥有交聘决策权的“权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权臣”拥有的交聘决策权,来源于在特定历史时期,根据实际交聘活动情况由皇帝临时授予的权力。比如,在战时前线的将领会被皇帝授予便宜行事之权,从而拥有了交聘决策权。

天辅五年(1121),《以完颜杲为内外诸军都统率师伐辽诏》中便有“事有从权,毋需申禀”之语。天会四年(1126),宗望与宗翰两路大军攻北宋,“深入攻取,事无大小,皆委元帅府从长措置施行”。大定三年(1163),金世宗任命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前往南部边境处理与南宋的“和”“战”问题,金世宗“诏忠义度宜以行”,后又派遣苏保衡“与仆散忠义斟酌事宜”。

另一类是在皇权衰微的情况下,某些臣子的势力逐渐膨胀而在交聘事务上拥有决策权。最为典型的例子即为宗盘、完颜昌还河南、陕西地与宋一事。天会十五年(1137),刘豫的伪齐被废,随后,完颜昌就提出将河南、陕西之地还给南宋并与南宋议和。此时,完颜昌为左副元帅,附和完颜昌提议的宗盘是太师领三省事,一个有军事大权,一个掌全国政务,所以还地南宋的建议尽管“熙宗命群臣议,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干等争之不能得”。
最终在天眷元年(1138)与南宋签订议和协议,竟在众多反对声下将河南、陕西之地拱手让给南宋。正如金熙宗后来怒骂南宋议和使臣王伦“汝但知有元帅,岂知有上国耶”,这一时期的完颜昌、宗盘主导对外交聘决策,其身为手握大权的朝臣所具有的交聘决策权甚至在皇帝之上。皇帝的交聘决策权让渡给了“权臣”,而为皇帝交聘决策提供补充与监督的“垂询”“纳谏”也自然无法起到本应有的作用。

这两种分享交聘决策权的形式有所不同,实际获得的权力大小在具体交聘活动中的体现也有所差异,但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情况下,拥有交聘决策权。权臣拥有交聘决策权,基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与其他国家或民族进行谈判的权力,如成书于皇统元年的《元帅兀术遣使第三书》即称,“亲奉圣训,许以便宜从事,故因可与阁下成就此计也”,兀术也就是宗弼,宗弼在熙宗朝升任都元帅,在军事上统领军队与南宋作战。
而《第三书》所载“成就此计”,则是指兀术与南宋使臣就双方边界与岁币问题达成的协议,书中还指出了“圣训许以便宜从事”,可知在这次与南宋的议和活动中,皇帝把权力交给了宗弼,宗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南宋使臣就和谈内容进行商谈。“既盟之后即当闻于朝廷”,可以先有“盟”,后上达朝廷。“盟”即“誓约也”,又“信也”。

在古代“盟”的履行是有神明的监督的,“凡盟礼,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违,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所以在“盟约”“盟书”等交聘条约上都会有类似向神明起誓保证履行合约的内容。可见“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交聘协议,一旦成“盟”,就必须遵守。而在此次和谈过程中,宗弼被授予了与南宋“盟”的权力,就是被授予了交聘决策权的体现。
金章宗任命仆散揆为左副元帅,负责与南宋的作战事宜,并允许仆散揆在南宋“奉表称臣,岁增贡币,缚送贼魁,还所俘掠”的条件下,与宋罢兵议和,叮嘱仆散揆“机会难遇,卿其勉之”,后南宋二次遣使告和,仆散揆“以乞辞未诚”,认为南宋只是想拖延金军进兵,拒绝了议和请求。仆散揆在金章宗授予的“议和”权力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认为还不到时机,决定不在此时与南宋“议和”,也是行使了交聘决策权。

权臣拥有交聘决策权的另一表现为两国如果有需要解决的交聘事务或纠纷,有时也需要通过“权臣”来寻求解决的办法。例如,天会二年(1124),西夏李乾顺遣使“谢金誓诏,且以宋侵赐地告”,同时希望金国能够派遣军队帮助西夏抢回被北宋抢走的土地。
金太祖“命西南、北两路都统府从宜定夺”,当时西北、西南两路都统为宗翰,也就是说金太祖把是否为了西夏土地问题出兵北宋的决定权授予了宗翰。同时将“使人王阿海争仪物事”这一交聘活动中发生的纠纷事件也交与宗翰负责解决,命其通过“与夏通问”来“便宜决之”。

同年,童贯遣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马扩出使金朝见金将完颜希尹,希望按照盟约交割云中土地,完颜希尹没有同意。此时完颜希尹应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云中土地正在其管辖下,尽管有宋人所说的“议和”条约约束,但是完颜希尹还是没有将土地交予北宋。金军围宋都,宗翰、宗望还曾“移文开封府索军器”。

天会十五年(1137),南宋何藓奉使金国回,通过“大金国右副元帅书”“具报太上皇帝久违和豫,厌世升遐”,才获得太上皇帝宋徽宗讣音,这时双方交聘关系还没有达成议和协议,通过“权臣”进行信息交流。贞佑二年(1214),南宋天水军移文秦州,希望能重开榷场,宣抚副使乌古论兖州认为“如俟报可,实虑后时”,而金宣宗又曾“许其从宜”,所以在没有得到朝廷允许的情况下,便先行开设秦州榷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