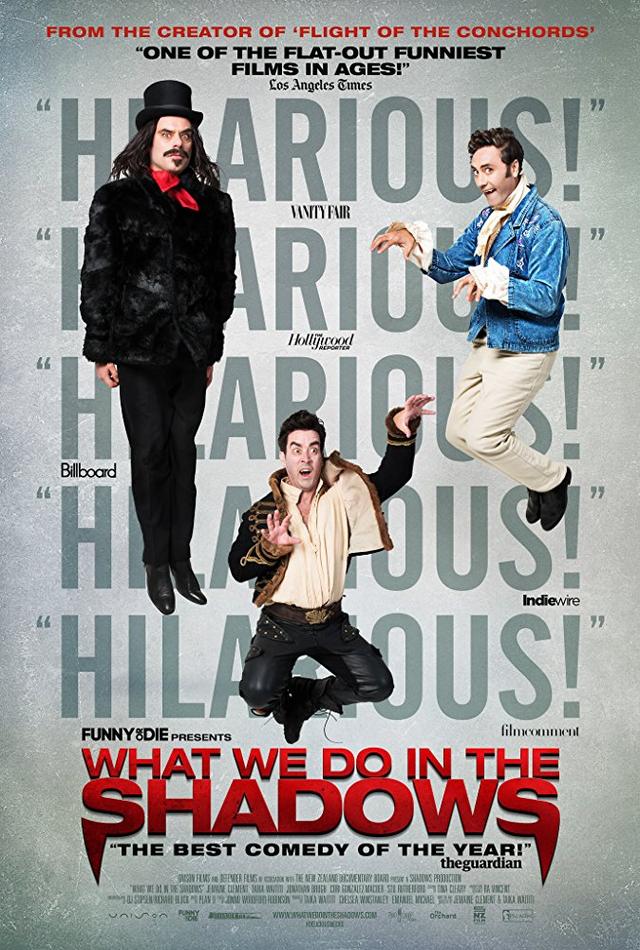许多人都知道,水泊梁山是宋江一伙哥儿们的根据地。

八百里的水域,浩渺无垠,深浅难测;水边芦苇丛生,港岔交错,舟揖往来,易迷路径;泊中梁山兀立,上有宛子城,中有黑风口,下有金沙滩,天生一处绿林好汉的逞强之地。
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汉,正是在此凭山曙水,扯旗造反,演出了一幕幕动人的水浒故事,梁山水泊也成了让后人向往的一处游览胜地。
令人遗憾的是,“八百里梁山泊”今已基本不存,宋江等人的遗迹也很有限,然而有关这里的山水变迁,却能引发一些值得研究的话题。
梁山是怎样一座山。

梁山,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的梁山县境内,属泰(山)沂山切割余脉,共七脉十一峰。主峰在梁山县城南五里处,海拔197.9米,占地面积3.5平方公里。
梁山看起来特立独耸,其势不险,然与北面的龟山、凤凰山、小安山、金山、银山等遥相呼应,又有浩荡水泊四周拱卫,形成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当年北起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市),西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一带),南至雷州(今山东菏泽市)济州(今山东巨野).东及泰安州,方圆百余里,大小十余城,即为水浒英雄们的纵横驰骋之所。

梁山,古名“良山”。因汉文帝第二子梁孝王田猎于此,乃名良山。据《史记·梁孝王世家》:
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徒淮阳王武为梁王”,其封地为梁国(今河南省商丘一带)。“三十五年冬,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良山……。六月中,病热,六日卒,溢孝王。”这是“良山”之名首次见于记载。
“良山”为何改名为“梁山”?有这样三种说法:
其一,据《汉书补注》、《寿张县志》等史料记载,良山所在县,春秋时名“良县”,秦汉改“寿良县”、“良汉县”,西汉时为梁国境域,梁王刘武曾在良山打猎,“良”、“梁”音同,遂改今名;
其二,梁孝王世家北猎良山,梁王死后又葬于此,为示纪念,因改“良山”为“梁山”;
其三,为避东汉光武帝叔父刘良的名讳,曾改“寿良”为“寿张”,“良山”不能例外,也改名成了“梁山”。
这三种说法中,以后一种说法为主,佐证史料也多。
如《汉书·地理志》、《东平县志》、《寿张县志》皆有记载。后来,“寿张”县在唐代又一度改为“寿良”县,但梁山之名一直到今。

小说《水浒传》对于梁山没有正面详细描写,但不难看出它的险峻广大。
如林冲被逼上梁山,“看见四面高山;三关雄壮,团团围定;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才是正门,两边都是耳房。”当时的梁山根据地尚是初创时期,其规模已很可观。
接下来小说又陆续提到梁山上有宛子城、黑风口、断金亭、忠义堂、六关八寨以及作为接待联络用的四个酒店,可谓高山大野,关隘重重,真是图王霸业的好去处。
另从梁山首领有一百零八将之多的情况来看,若算马、步、水军和机关后勤人员、随军家属等,活跃在梁山上的人数应有几万之多,否则怎能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的十多万兵马?
那么,梁山果真是“四面高山,三关雄伟”的险峻地吗?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如前所说,梁山是座海拔不足二百米的坟形小山,是泰山高度的九分之一,既无“四面高山”,也无雄伟的三关,如此弹丸之地,何谈图王霸业?又怎能盛得下几万大军?
再从“宛子城”来看,也难找出它的影子。据史料记载,宛子城是太行山西麓的一座山,四周诸峰环列,中间地势低凹,很像一只饭碗,故名“宛子城山”。元朝末年,有农民起义军在此结寨,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水浒传》的作者来个移花接木,把宛子城搬到梁山,以增加博大雄浑之感,其实子虚乌有。还有小说描写的六关八寨,也难找个影子,现在能看到的“忠义堂”、“断金亭”以及朱贵的小酒店等七十多处名胜景点,皆依小说作者创造,多是人造的“古迹”。

总之,此梁山非《水浒传》中之梁山,请勿按图索骥,只宜掩卷神思。
梁山泊到哪里去了?
梁山泊,又名“梁山泺”,据《尚书·禹贡》、《周礼》和《尔雅》等古籍
记载,梁山南面有一片水域,名“大野泽”。秦汉时称为“巨野泽”。至唐代又改为“大野泽”,《元和志》称“大野泽……,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可见其泽面十分广大。
后来,有些史料就把“巨野泽”(“大野泽”)称为梁山泊。如《宋史·杨晋传》就说:“梁山泊,古巨野洋”;《禹贡锥指》也用吴幼清的话说:“大野泽,俗称梁山泊”,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大清一统志》。严格地说两者并非一回事。大野泽是怎样出现的,史料不见记载,而梁山泊的形成,却有明确说法。

据元代于钦的《齐乘》记载:“汉水西南流,与济水合于梁山之东北,回合而成泊。”这种说法尚不完整,要真正弄清梁山泊的成因,不能不说到黄河。据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纪要》:
“后晋开运初,滑州(今河南滑县)河决,浸汴(今开封)、曹(曹州,今山东菏泽)、单(今山东单县)、濮(今河南濮阳)、郓(今山东郓城)五州之境,环梁山而合于泺,与南旺、蜀山湖相连,弥漫数百里。宋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滑州河复决,历渲(今河南濮阳西)、濮、曹、郓注梁山泺。”以上只记了黄河两次大决口,大水即“弥漫数百里”,梁山周围的水域已十分可观了。又过了五十八年,即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七月,黄河又“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泊……·
”。(引见《宋史·河渠志》)由于黄河的南迁,梁山泊也就成了这条大河的必经之地,水势旺盛,横无际涯,时人有“梁山泊八百里水”之说,可见面积十分浩大。
沧海桑田,河徙水迁。八百里梁山泊如同一位过客,停留了一段时间就不见了。现在能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阡陌良田,只在原东平州县辖区有一东平湖,面积不足二百平方公里,算是梁山泊的惟一现存遗迹。人们不禁要问:原先那片浩森的大水泊到哪里去了?

原来,黄河在进入这片巨大的低凹地后,流速变缓,大量的泥沙沉积于水泊,泊底渐渐增高,高成大块平地,这里的水势即减弱了。据《金史·食货志》: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黄河被迫南徙,夺准入海,“梁山泊水退,地甚广,已尝遗使安置屯田。”
然而,即使黄河改道,梁山泊并未很快消失。元朝时期,黄河多次泛滥,黄河曾在二十二处同时决口,复使河道北移,梁山泊水势再次大盛。
元代诗人陆友仁曾领略过当时的水况:“我尝舟过梁山泊,春水方生何涉漠”。可见那时的梁山泊仍然保留较大规模。但是,由于黄河北移,不再向梁山泊注水,尽管有汶水流入,这里的水面慢慢剩下十之二三

到明成祖永乐年间,皇帝决心治水,“筑戴村坝,遏汶南流”。这样,梁山泊的水源基本断绝,泊域越来越小。至景泰年间,明政府对梁山泊进行大规模综合治理,
“河水北出济漕,而(东)阿、鄄(城)、曹(州)、郓(城)间田出沮沏者,百数十万顷。”
原先的梁山泊退水为泥沼,泥沼又干涸成良田。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曾来这里实地考察,他在《日知录》中写道:
“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为川浸矣。”
可是,奔流不息的黄河仍难安分,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七月,黄河又在仪封县(治所在今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河水灌入山东东平县境,“纵横数十里,民田汇为大泽”,形成了一个山间平湖,即今日东平湖,可视为当年梁山泊的惟一遗迹。
《水浒传》上的八百里浩瀚之水,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消失了。
水泊梁山真是宋江的根据地吗?
联系《水浒传》小说的描写,不少人认为书中写的多为真人、真事、真地点,但不一定是在梁山泊。

《宋史》卷二十二说:“淮南盗宋江等犯准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人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这说明宋江的活动区域是在淮南,并末在水泊梁山结寨。
《宋史·侯蒙传》载有此人给皇帝的上书,其中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这就点明宋江的活动区域是从山东东部到陕西西部,区间长达两千多里,属于流动作战,不是结寨自守。
宋代学者方勺的《青溪寇轨》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宣和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天章阁待制歙守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出青、齐、济、淄间,有旨移知青社。”又说,“宋江扰京东,曾公移守青社。”
这就恰好证明了《宋史》所说“宋江起河溯,转略十郡”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的活动区域十分广大,并非结寨于鲁西的水泊梁山,否则,宋廷怎会让曾孝蕴去镇守鲁东的青州呢?
除去这些史料明显否定(或不载)宋江以水泊梁山作根据地外,其它如《宋史》中的《微宗本记》、《张叔夜传》,还有宋代李陲的《十朝纲要》、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王炎的《东都事略》等,都说宋江是流动作战,无一处提到他们建立过根据地。更没说宋江等人占据过水泊梁山。

不过,《宋史》中也确实载有水泊梁山被大量官兵光顾的时候;如《任谅传》、《杨戬传》、《许儿传》等,都提到宋江等人起事之际,水泊梁山遭官军清剿,但没有捉到所谓的盗贼,更未见宋江的踪影,说明这不是他们苦心经营的根据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元之际的画家龚开的《三十六画赞》中,多次提到宋江等人活动在山西太行山的梁山(今昌梁山),无一字说到山东的梁山,这种说法和《宋史·侯蒙传》中的说法趋于一致。、
总之,从以上种种官私史料来看,宋江等人大概实力有限,不得不流动作战,没有建立起根据地,他们在转战各地的过程中,有可能在水泊梁山一带活动过,但没有长期停留,更没有在这里建立根据地。
让人不解的是,在文学界、戏曲艺术界、美术界甚至还有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水泊梁山是宋江等好汉们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他们制造一系列水浒故事的重要舞台。特别是在梁山上还有诸多有名有姓的所谓遗址就更让人觉得“必确有其事,无可疑者”了。

历史的事实当然不是可以随意装扮的,正如历史小说的描写不是事实的本来面目一样。
那人们为何会把水泊梁山作为《水浒传》的实景写真呢?这要说到元代杂剧的宣传作用。在元朝至正年间,元大都(今北京)人高文秀、棣州(今山东惠民)人康进之等人组成了杂剧作家群,他们借古讽今,大写具有民族反抗精神的梁山戏,如《李逵负荆》、《黑旋风双献功》等,一时风靡朝野,妇孺皆详其情。
在这些戏里,把水泊梁山写成了宋江等人的“三十六座宴楼台,聚得百万军粮马草”的牢固根据地。
《水浒传》的作者后来创作小说时,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并大胆地加以艺术虚构。尽管书中有些人名、地名、事物名确为实有,但已被小说作者成功地进行了新的组合,结果是虚虚实实,似有非有,让人难辨真假,历史的本来面目不知不觉给忘掉了

《水浒传》作者对于水泊梁山的描写,看起来煞有其事,实则与山川地形大不相符。,因为作者心目中的故事原型并不是宋江一伙,而是元末张士诚的起义,故事地点不在山东的梁山,而在江苏兴化的梁山;水泊不在鲁西南一带,而在今江苏省大丰县的草堰、白驹两地。
这里当时是水网地区,内有河沟港又千条之多,同时张士诚也确实在这里的梁山安营扎寨,把它写成起义队伍的根据地很有道理。
《水浒传》的作者与张士诚有过交往,清楚了解他的斗争历程,明初时期不可能正面赞颂这股势力,于是变换角度写成子宋江起义,地点只好移到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