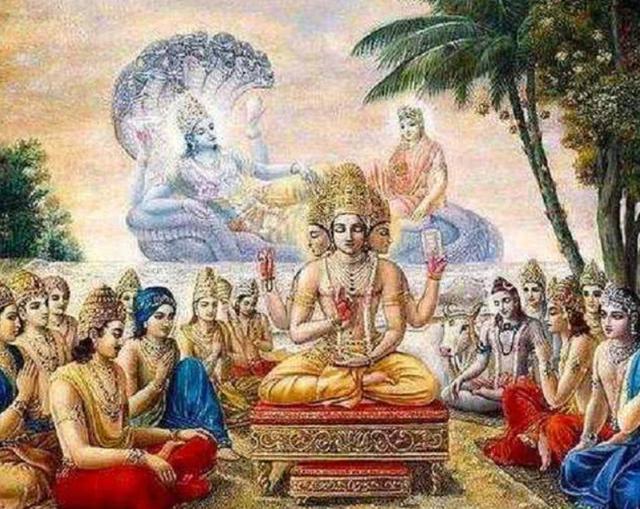文/郑焕章
石鼓庙座落在晋江市青阳镇的石鼓山上,启建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一1189年),后几经重修、重建和扩建,成为晋江一带一所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民间信仰庙宇,1991年还被列为晋江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石鼓庙系由顺正王宫、仁福王宫、福佑帝君宫和乡贤祠组成,所崇祀之神颇多,有顺正王、顺正王的父母、吴太尉、洪总管、仁福王、第二爷、池头妈、福佑帝君、观音佛祖、保生大帝、城隍爷、阎王爷、福禄寿君等等(另者,乡贤祠是专祀夏秦、李聪、蔡黄卷、李逢期、庄用宾、庄尚稷、庄国祯、李伯元和吴韩起9位乡贤)。这些神祇有的开初就有,有的是后来逐渐加进的,从而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神的群体。然而,在这个群体中心有一尊是主祀之神,而且从石鼓庙的历史来看,八百年来其主祀之神不是一成不变的。于是,本人拟论述石鼓庙的主祀之神及其演变,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从现在石鼓庙的顺正王宫、仁福王宫、福佑帝君宫这三座宫的命名和明李伯元《青阳志·祠庙》中所记述的情况来看,自始至今顺正王、仁福王、福佑帝君是为该庙的主要之神。但在这三尊的主要之神中,哪一尊又是主祀之神呢?从石鼓庙八百年来的历史考察,其主祀之神先是福佑帝君,后是顺正王,即宋代及元代的主祀之神是福佑帝君,明代及其以后的主祀之神是顺正王。

宋元时期,石鼓庙的主祀之神焉何是福佑帝君?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青阳蔡、王二姓之先世是因崇敬蔡襄而创建石鼓庙,所奉祀是南安丰州九日山通远王祠之神。《青阳志·祠庙》载曰:“石鼓神庙,蔡、王二姓先世所建,祀福佑真君、王太尉等神。”①即是青阳蔡氏九世孙蔡曼与凌云王氏先祖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所创建。《青阳志.祠庙》对石鼓庙所祀诸神有较详细地记载,现摘其对福佑真君、仁福王、顺正王这三尊主要之神的叙述以说明它们原是南安丰州九日山通远王祠所祀之神。其曰:
石鼓庙所祀诸神,东偏一届中立土谷神牌,福佑真君在焉,俗称“翁爷”。郡志:宋有蜀圣僧号员普,永春乐山跌坐二十年,邑今江公望扣梧而歌招之不至,绍圣二年蜕化,邑人塑像乐山祀之,敕封福佑帝君,以十月廿六庆诞。
庙之西偏仁福王,相传赵宋忠臣,姓陈名益。熙宁间西夏之警,辟为巡检,元丰间观南安九日山灵,舍身为佐,植杖立化,淳祐中累封元福王,载《南安县志》;或传说从南迁来,迟晓鸡追驾不及,化于九日山延福寺,有异水流入前沟,为里妪拾取,送入庙塑像,以正月初九日庆诞,祀忌用鸡。
右一庙左畔奉顺正大王,俗呼本官,相传姓黄名志,本潮州人,宋孝宗丙午年九月初五日诞降,为蔡宝谟门客掌簿,有道术能驱瓦瓮,自行入水,养鹅食草不越界限,宁宗嘉定庚辰正月初四日化于庙,塑为立身,雕木为神,辛已显化助国,封殿前太尉,恭宗德祐乙亥复助国有功,封江夏护国清远大将军。
据《丰州志·文化篇》记载通远王祠曰:“在丰州九日山延福寺侧,始建于唐咸通中(860-874),初名‘灵乐祠”,祀乐山隐士李元溥。宋封‘通远王’,政祠为庙,赐名昭惠。其从神有二:一名黄志,封‘辅国忠惠王’;一名陈益,封‘仁远王’,都是真人而成神封王的。陈益于元丰间,随太守陈偁祈风于延福寺,‘睹庙貌森严,显灵奇异,誓舍身为佐,遂植杖立化,僧泥躯奉之”(《泉州府志》)。这就是历史上九日山三十六奇之一肉身佛。尽管《青阳志》和《丰州志》的记载稍有出入,但亦可明白地看出石鼓庙这三尊主要之神都是九日山通远王祠所奉祀之神。其中福佑帝君和仁福王必是南宋淳熙年间建庙时从通远王祠分炉来的,顺正王则是后来从石鼓庙分香去的。
南宋淳熙年间,青阳蔡、王二姓创建石鼓庙为何会奉祀通远王祠这两尊神呢?我认为是跟他们崇敬蔡襄有直接的关系。蔡襄,字君谟,其先世居仙游,至他始迁莆田。他十九岁中进士,官至福建路转运使、端明殿学士,卒赠吏部侍郎,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植物学家,又居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至和、嘉祐间两知泉州时,更以主持建造完成我国第一座海港梁式大石桥洛阳桥而举世闻名,留芳千古;南宋乾道年间,朝廷还赐之谥曰“忠惠”。《青阳志·氏族》记载青阳蔡氏曰:
谱称莆阳仙游人,系出晋司徒文穆公模,与端明公襄同所自出。唐咸通间,有一翁名辉自仙游卜居青阳山吴店市,是为始祖。其子孙蕃衍,在青阳族指尤繁,可称巨族矣!
这说明青阳的蔡姓是与蔡襄同宗,于是他们必以有蔡襄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先祖为荣耀,从而倍加崇敬。据清嘉庆《惠安县志》记载,蔡襄在主持建造洛阳桥时于桥北(今惠安县洛阳镇万安街)建一庙(即后称之为“昭惠庙”),“以奉兹桥香火”③。张航《昭惠庙记》碑载曰:“传庙始创于唐,名‘镇海庵’,宋皇祐五年,蔡忠惠公筹建洛阳桥,原名万安桥,扩庵为会所,迎南安九日山海神祀于此。神即永春乐山白衣叟也。宋淳祐辛丑赐额“昭惠”,庙神封福祐帝君。”④又黄柏龄《九日山志》记载通远王祠(后亦称“昭惠庙”)曰:“宋嘉祐二年(1057),蔡襄任泉州太守时,泉州大旱,来‘通远王祠’祷雨,果然应验,就奏请朝廷加封为‘善利王’,……”⑤可见蔡襄对于九日山的通远王是颇为崇拜。所以,南宋淳熙年间青阳蔡姓创建石鼓庙而奉祀九日山通远王祠之神,可以肯定地说是出于对其先世蔡襄的崇敬。至于王姓为何也赞成此举并与之合作呢?因王姓有位先世叫王实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首先倡建洛阳江上这座大石桥,至和三年(1056年)蔡襄来泉上任后继续主持建造,王实等十五人又“职其事”,直到嘉祐四年十二月(1059年2月)竣工。⑥于是,王姓的先世王实与蔡姓的先世蔡襄有这段特殊关系,对建造洛阳桥也是贡献很大,而且在桥北建庙奉祀九日山通远王他也必定参与其事。正因如此,当时的青阳王姓肯定也是出于对蔡襄和王实的崇敬,才会与蔡姓共建石鼓庙,奉祀九日山通远王祠之神。由于通远王,即福佑帝君是通远王祠的主祀之神,又是蔡襄所崇信之神,所以,石鼓庙在南宋创建时的主祀之神自然是福佑帝君。

二、宋代是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辉煌时期,通远王作为海神备受崇拜,并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崇。由于泉州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气候温和,海岸线曲折,海域辽阔,港湾良多,所以,在唐代之成为我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到了宋代对外贸易进入繁荣发达的辉煌时期,成为世界东方的一个大港口。北宋时,泉州与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南宋时,泉州已发展到与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当时,因海上的运输工具最先进的只是帆船,其航行得靠风力驱动,远洋商船就得依赖信风的刮起。于是,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只有寄望于神明来保佑顺风航行,安全抵达。宋代,泉州正是为了适应海外交通发展的需要,将九日山通远王祠(属延福寺)的通远王奉为海上保护神来崇拜,每年春、冬两季往返的远航商舶都到此祈风或祷谢,香火十分旺盛。南宋初,李邴在《水陆堂记》中对这种盛况有较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他写道:
泉之南安,有精舍曰“延福”。其刹之胜,为闽第一院。有神祠曰“通远王”,其灵之著,为泉第一。每岁之春冬,商贾市于南海暨番夷者,必祈谢于此。农之水旱,人之疾病亦然。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际之物充其姐,成物命不知几百数焉!已而散胙饮福,觞豆杂进喧呼狼籍。 ⑦
于此记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宋代人们对于九日山通远王的崇拜是何等的热火!

宋代,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某种需要,对于九日山通远王更是极力加以推崇。上面已交代,北宋至和、嘉祐年间两知泉州的蔡襄主持建造洛阳桥后,就于桥北建庙奉祀通远王“以奉兹桥香火”;又到九日山通远王祠祈雨,以解泉州之大旱。还有,南宋嘉定、绍定年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亲撰《海神通远王灵著王祝文》到九日山通远王祠祈祷,以求神助王师扑除来自温州、明州的海寇的骚扰,保护海舶安全航行⑧尤其是,两宋政府为了鼓励发展海外贸易以增加财政收入,每逢中外远洋商舶(通称“蕃舶”)进出泉州港的夏冬两季,或一年一次,或一年两次,由泉州郡守或市舶提举司率领有关官员到九日山通远王祠祈风,以保佑“蕃舶”顺风航行,安全抵达。南宋泉州郡守真德秀就曾经率员到九日山通远王祠祈风,他在《祈风文》中很明白地写道:
唯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郡计之殚至此极矣,民力之耗亦既甚矣。引领南望,日需其至,以宽倒垂之急者,唯此而已矣。神其大彰厥灵,俾波涛晏请,舳舻安行,顺风扬帆,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是則吏与民之大愿也!⑨
南宋时,政府官员举行祈风典礼后有的还刻石纪念。现九日山的摩崖上尚保存着南宋淳熙元年至咸淳二年(1174一1266年)的十段祈风石刻,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北宋虽无祈风石刻保存下来,但据《九日山志》记载,通远王祠的仁远王(石鼓庙谓之“仁福王”)陈益,正是在北宋元丰年间随泉州郡守到通远王祠祈风而舍身为佐神的。⑩两宋封建统治者为了推动人们对于通远王的崇信,还一再给予赐额加封。清乾隆《泉州府志》载曰:
宋封神通远王,赐额“昭惠”。嘉祐中,泉大旱,守蔡忠惠祷雨辄应,奏加封“善利王”,寻加“广福、显济”。⑪
于是,其神号全称为“通远善利广福显济王”,“其灵之著,为泉第一”。处于这种态势之下,石鼓庙的福佑帝君作为九日山通远王的分神自然跟着红火,从而稳坐主祀之神之位。
从上述两方面的情况来看,在宋代石鼓庙的主祀之神当属福佑帝君。另者,宋代的封建统治者还直接推崇石鼓庙,使福佑帝君的主祀之神的宝座更加巩固。据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宋郡守真德秀祷雨于此。”⑫这无疑会提高石鼓庙的声望,推动人们对福佑帝君更加崇信,从而其主祀之神的宝座自当更加稳固。

臻至元代,由于封建统治者转向推崇女海神妈祖(下面会再详谈),九日山通远王已遭受冷落,其作为泉州海神之位几已丧失。这对石鼓庙福佑帝君肯定会有所影响,它的主祀之神的位置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但还未尽丧失。因为,一者,元代是泉州海外交通贸易最为辉煌的时期,已发展到与九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跃入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贸易港之一,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于是对海神的崇拜会更加热火。尽管封建统治者已转向推崇女海神妈祖,但人们对于原来的海神通远王的崇拜还不会完全放弃,而且妈祖的信仰也未尽渗入每个地方。元代,青阳就是没有建造妈祖宫,石鼓庙也无出现妈祖神像,这说明福佑帝君的海神桂冠尚未被完全脱掉;二者,福佑帝君是尊具有多功能的神衹,人们不仅祈求他保佑出海平安,而且天灾人祸也祈求他消弥,于是,即使其海神的职能被削弱,也还难于将其主祀之神的位置推倒。所以,有元一代,石鼓庙的主祀之神仍然是福佑帝君。
可是,进入明代以后,石鼓庙的主祀之神已是顺正王,而福佑帝君被降为从神。关于顺正王是何许人,清乾隆《泉州府志》、《晋江县志》和道光《晋江县志》都说是宋潮阳(潮州)人王志⑬,而明天启《青阳志》说是宋潮州人黄志⑭。《青阳志》系青阳人李伯元所撰,本地人写本地事一般来说是较为准确;又九日山通远王祠所祀的一位从神也标明是黄志⑮;另者,闽南话黄与王有种读音相近,极有可能是将黄志讹传为王志。因此说,石鼓庙的顺正王应是黄志而非王志。那么,在宋元时期黄志仅是石鼓庙的一位从神,焉何到了明代及其以后会晋升为主祀之神呢?分析起来,大概有这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元、明封建统治者特别推崇妈祖,通远王的泉州海神之位被取代。妈祖即天妃,莆田湄洲神女林默。北宋时,她成为其家乡一带信仰的海神,南宋时已传播到全国不少地方。庆元二年(1196年),泉州就开始建造顺济宫(今称“天后宫”)加以崇祀。然而,南宋时期正是泉州海神通远王最为显赫之际,妈祖尚无法取代于他。到了元代,“由于漕运在元朝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朝廷对保护海上航运安全的天妃特别崇敬”。所以,尽管元朝是泉州海外交通最为繁荣的黄金时代,但通远王已遭冷落,其海神位置几乎丧失,妈祖开始以“泉州海神”之封衔受人们的崇拜。进入明代,因传说妈祖累神助朝廷使节出使外国和官兵铲除寇患,更是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使之信仰更加广为传播,尤其在泉州的沿海一带已普遍建庙崇祀。于是,通远王的泉州海神之位完全被全国性的海神妈祖所取代。这样,尽管青阳没有直接崇祀妈祖,但石鼓庙的福佑帝君亦随之降为一般的地方神祇,其主祀之神的位置就难于保住。
二、明代泉州内乱外患连续不断,又海外交通贸易衰落,人们已祈望有着护国除寇功能的神祇来保境安民。从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起,在泉州接连发生色目人赛甫丁、阿迷里丁的成军叛乱和那元纳的市舶司叛乱,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1年)历经十年才被元将陈友定镇压;接着,陈友定又据泉负隅顽抗,妄图阻止明朝的统一,至明洪武八年(1375年)才被明将汤和平定。所以,“泉民先经回寇涂炭,继为友定茶毒”,苦难已十分深重。又洪武三年(1357年),泉州一带开始不断地遭受倭寇的骚扰,在嘉靖年间最为惨重,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才基本结束。还有,从明朝中期以后,泉州一带又屡遭盗贼和海寇的抢掠以及西方殖民者葡萄牙、荷兰的入侵。如此长期繁多的内乱外患,使泉州人民惨遭蹂躏之苦,给泉州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破坏。再者,从明初开始,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倭寇的骚扰和孤立盘踞海岛的元朝残余势力,就实行了“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制度,加之上述的内乱外患,促使泉州海外交通贸易急剧衰落,走私活动非常猖獗,泉州港已由世界性大港变为地方性小港。于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们已祈望那些具有护国除寇功能的神祇来保境安民。据载,石鼓庙的顺正王黄志恰是具备这方面的功能:南宋嘉定辛已(十四年,1221年)“显化助国(抵抗金兵),封殿太尉”;德祐乙亥(元年,1275年)“复助国有功(抵抗元军),封江夏护国清远大将军”;明永乐年间,显化助三宝太监“征琉球”有功,敕封“顺正大王”。当然,其所谓有这些方面的显化助国之功,都是当时人们意愿的一种反映。所以,在内乱外患繁多的明代,顺正王被晋升为石鼓庙的主祀之神是很自然的事。

三、顺正王黄志原系青阳蔡次傅家门客,又是在石鼓庙化身成神。《青阳志·祠庙》记载,顺正王黄志,“本潮州人,宋孝宗丙午年(淳熙十三年,1186年)九月初五日诞降,为蔡宝谟门客掌簿,有道术……宁宗嘉定庚辰(十三年,1220年)正月初四日化于庙,塑为立身,雕木为神。”蔡宝谟,即是宋理宗赵昀之师宝谟阁大学士蔡次傅,系创建石鼓庙的蔡旻之子;嘉定十七年(1224年)即黄志成神后的第五年,他又与其父和王氏弟子扩建石鼓庙。黄志原系蔡次傅家门客,又是在石鼓庙成神,说明他与蔡姓的关系非常密切,于是,在福佑帝君无法再作石鼓庙的主祀之神时,推他接任是顺理成章。
四、明朝封建统治者的推波助澜。《青阳志·祠庙》载曰:“至明永乐间,命内监三宝大人征琉球,战舰几危,永宁卒佩香火显应,纵火烧夷,凯奏上神灵敕封慈济显应威烈明王顺正大王,乃赐帽袍靴带剑印以旌殊勋。”明何乔远的《闽书》也载曰:“皇朝里人有从中官郑和下西洋者,奉其香火以行。和舟次恍惚,见其灵助,言状于众,人以神对。还朝奏闻,赐封曰‘顺正’。”@两者所记似乎不是一码事,但都是说明黄志神助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有功而受敕封为“顺正王”。郑和下西洋是明初一大盛事,也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因此,明朝封建统治者大力宣扬此举常得“神助”以证其是“顺乎天意”,既可博得朝廷内外的积极支持,又可使参与者增强冲破艰难险阻的信心,胜利完成任务。顺正王黄志则是有幸得其宣扬之一神祗,于是,在石鼓庙福佑帝君的主祀之神位置岌岌可危之际,正是他受永乐皇帝加封为“顺正大王”之时,这对他晋升为石鼓庙的主祀之神必然会起催化作用。顺正王取代福佑帝君在石鼓庙的主祀之神位置应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基于上述四方面的原因,毫无疑问顺正王是在明代登上了石鼓庙的主祀之神宝座,大概从永乐年间正式开始的。因此,《青阳志·祠庙》载他被“俗呼本宫公”。⑫
至于清代以来,由于清初泉州一带深受清兵蹂躏之苦,又饱经“海禁”和“迁界”之难,近代之后,还先后遭遇英军、日军的入侵,并且时代风云不断变幻,社会经常动荡不安,因此,人们对于能“保境安民”的顺正王是愈加崇信,他的主祀之神位置就一直延续下来。另者,从明朝中期以后,尤其是清代以来,随着顺正王的影响不断扩大,其信仰已传播到惠安、南安、同安诸县,而且随着晋江商人和移民的足迹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等地。
总而言之,神是人造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从石鼓庙主祀之神的演变完全可以证明之。然而,从某一侧面来看,它也是泉州历史的一种反映。所以说,石鼓庙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而且现在它对于团结联系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定当发挥出应有的桥梁作用。
注释:
①明天启四年李伯元《青阳志·祠庙》。
②《丰州志)第212页,南安市丰州镇《丰州志》编写组编写。
③清嘉庆《惠安县志》卷11“坛庙寺观”。
④此碑1984年立,竖于昭惠庙大门内东侧。
⑤黄柏龄《九日山志》第93页。
⑥蔡襄撰书的《万安桥记》石碑,立于洛阳桥南的蔡襄祠内。
⑦同⑤,第144页。
⑧《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50。
⑨同⑧。
⑩同⑤、第94页。
⑪清乾隆《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
⑫清乾隆《泉州府志》卷6“山川”。
⑬清乾隆《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乾隆《晋江县志》卷15“杂志”、道光《晋江县志》卷60“人物志”、明天启《青阳志·祠庙》。
⑭同①。
⑮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第12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⑯清乾隆《普江县志》卷15“杂志”。
⑰同①。
⑱同①。
⑲同①。
⑳何乔远《闽书》卷7“方城志”。
㉑同①。
(原载《闽台石鼓庙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晋江市历史文化研究总会、石鼓庙管理委员会董事会1998年11月编印)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郑焕章文史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