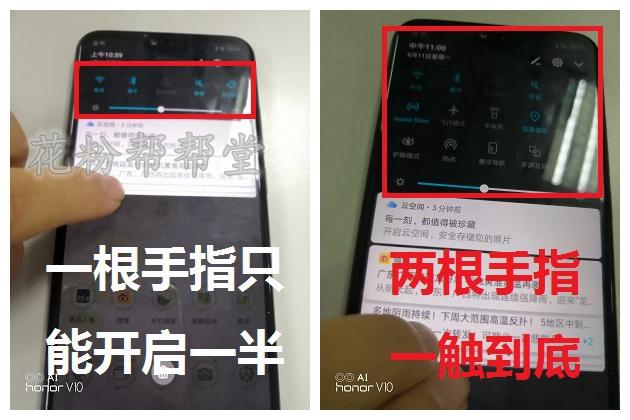1973年,我背着红色“语录袋”读完了高中。由于受“右派”父亲的影响,毕业后考学、参军均渺茫无望,只能回到所在的关门大队第三生产小队当社员。曾记得第一天出工时,生产小队长掐着腰对我严肃地说:“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你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是可以在这里大有作为的。……”
就这样,我当上了“人民公社社员”。每天除了跟社员们按所分配的农活,日复一日地准时上工外,还要按照小队长的指示,在休息时给大家读毛主席语录、念报纸,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让大山里的贫下中农,了解外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情况。很多新鲜事儿吸引了这些平时很少走出大山的父老乡亲,我也在劳动中逐渐与他们拉近了距离。每天看着他们配合默契的田间劳作、无拘无束的打情骂俏、到头不到两的谈古论今。作为其中一员,我苦中有乐,还真的一度忘掉了自己的“身份”。
领我们十几个社员铲地的陈组长,是一位典型的山东大汉,文化不高,但膀大腰圆、浑身是劲。无论干什么活儿,他都非常认真,不到钟点儿不休息,提前一分钟也不行。他在组织带领大家干活时,偶尔也会半生不熟地用上一两句流行的“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谁也不去较真,也不会笑话,反倒觉得他懂政治有水平、会“活学活用”。
陈组长住在我家的西沟里,是早些年从什么地方搬过来的下放户。他比我爸爸年长两岁,我管他叫陈大伯。印象中他很少关心什么政治运动,更不会讲什么大理论。他说那些对咱们种庄稼没什么用处,当农民种好地就行了。他也不管你什么身份,对待“成份”高的低的都一视同仁,谁遇到什么困难了,他见到了总会上前帮一把。
刚上工时,我还真的有些敬畏他,很少与他正面接触。可陈大伯用那满是老茧的大手,沉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跟我们干吧。当农民有什么不好呢?俺们都是贫下中农,虽然识字的不多,但都没有坏心眼子!”——我家的“成份”是“下中农”,那年月人们对家庭出身(成份)是非常重视和敏感的。
自从有了我这个会念报纸的社员,大家知道了不少大山外面的事儿。每天跟着这个十分务实的陈组长干活,实在是太累了,大家都盼着早点休息,好坐下来听我读报纸、喘口气。有时读到报纸上贴近农村、农民的内容,大家还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一会儿。可规定半个钟头的休息时间一到,也不等把一段文章读完,陈组长就立即招呼起来干活。用他的话说:“靠念报纸、讲大理论,地里能长出粮食吗?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的,不让你吃饭试试?毛主席还让我们‘抓生产’呢!” (
陈组长自己的农活做得非常棒,对别人的要求也很严格。跟着他干活藏奸耍滑是绝对行不通的。一旦被他发现了,返工重干不说,还骂你个狗血喷头。就拿铲地来说吧,他是带队的“龙头”,铲中间一条垅。两侧根据手把选好“贴摽子”的,然后十几个人“雁翅”似的左右排开。规定每人相距两步远,谁也不准超前,但也不能落后,整体呈“人”字形雁群式向前推进(图一)。

他快,两翼也要快;他慢,都得跟着慢。铲到地头,他拧上一袋老旱,还没等抽完又调转头,数好垄噌噌三步两步就穿了出去。其它人也急忙找到自己的垄紧跟上,一旦铲错了垄,给别人铲了,就白费劲了。
休息时别人休息他不歇,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挨个垄检查每个人锄地的质量。那些“盖扒锄”的、铲茬高的、铲坏苗的,是谁铲的他都一清二楚,无法狡赖。铲得质量不好收工后是要重铲的,否则就扣你当天的工分。由于他的活好,带头追求质量,弄得大伙既服气,又生气,有口难言。
爸爸给我精心制作了一把锄头,并叮嘱我:“咱和别人不一样,要好好跟陈大伯学农活,他的活儿好。年轻时吃点苦、挨点累不算什么,只要活儿赢人就会有饭吃。”陈组长也对我说:“好小子,就凭你的个头和聪明劲儿,是个好苗子,准能行!……但无论干什么,别性急,先要走稳了,再学跑。‘千万不能粗心大意’吗!”——这句“语录”用的有点儿意思。
我按照陈大伯的教诲与指导,仔细地观察老社员们铲地的方法,认真揣摩实践。经一个阶段的锻炼,铲地的质量和速度不断提高,排序也从最后的“雁尾”处,逐渐向前提到了“贴摽”处,即挨着领头雁——“打头的”陈组长了。我跟在他右后侧,一边铲地一边近距离观察学习。
但见他不慌不忙,一边铲一边教我怎样落脚、怎样下锄、如何过隔、如何打苗等;还严厉地强调:不准“盖扒锄”、不准骑垄铲、不准伤秧苗!产后的地垄要脚印少有规律、确保草死苗活地发暄(图二)。而他是那样有条不紊、准确无误。仿佛在表演娴熟的舞蹈动作,漂亮极了。

再回过头看,一些社员,有年龄大的,也有年轻的。大多数都如同陈组长一样,稳步向前,质量与速度均控制得恰到好处。但也有个别人不得要领,步伐混乱,下锄无序,显得手忙脚乱。后面跟着的社员还紧催促“铲脚后跟了!”越是这样,他越着急,不但速度快不起来,还累个够呛。好不容易铲到地头了,还没等喘口气儿,人家返程又窜出好几丈远了。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否则下次就要被调整到最后的雁尾处“打狼”了,那是让人瞧不起的,也是很丢人现眼的事。
我的表现很快赢得了组长和大多数社员的认可。生产队开会评工分时,我由原来的三等提高到了二等。每天比一些老社员还多挣一个工分。累是累了些,但我心里很高兴,为自卑的“身份”注入了一丝自信。你活儿做的好,组长、队长对你也刮目相看,分配活时还会有意无意地向你倾斜。某些好活、俏活不用去争,偶尔也会落在你的头上。比如跟大车拉脚、跑腿去大队办事、进城出差等等,令人羡慕和嫉妒。
不久,原先那个生产队小队长因“搞斗批改运动”表现好,被提拔到大队部当“造反派”头头去了,陈组长接替他当上了小队长。他开始抓第三小队的全面工作了,就很少再直接参与下地干活了。新接任的郝组长是纯贫苦农民出身的坐地户、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儿。他的农活也不错,但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平时只顾自己闷头干活,对别人很少像老组长那样严格要求、认真检查。打那儿一些社员也不再挨骂了,大家干活时似乎轻松了不少。
陈队长有时见到我,还常常告诫说:“做农活看似很普通,里面也有很多技巧。要认真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把活干扎实、干熟练了,自然就有窍门了,熟能生巧吗。但千万不要投机取巧,种庄稼是糊弄不得的,你糊弄它一会儿,它糊弄你一年。……”
“要记住,庄稼活儿都是给自己干的;掌握本领也是自己的,谁也偷不去、抢不走。毛主席不说吗:‘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庄稼活儿也是纸老虎。……”他这后一句话引用的似乎有点贴边儿。
那时我们第三生产队的一等劳力每天挣15个工分,二等挣14个,三等挣13个。仲夏农闲挂锄时,有些挣三等工分的社员不服气,和郝组长也讲不清道不白的。他们认为陈队长为人诚信正置,办事公平仗义,就去找他评理。陈队长听完申述后,二话不说,翻出记工本带上,领着大家来到他当组长时,领着铲的那块地。对大伙说:
“这块地是我铲的头锄,那天上工13人,左膀右臂谁挨着谁我都记着。你们看看吧,那些长满杂草的垄都是谁铲的?不服气的自己对对号!还好意思争工分吗?”
陈队长见大家都不说话,接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贫下中农更要讲认真!你若真的把活干好了,队里不给你涨工分,就用我的给你补上!”你还别说,陈队长这回引用的毛主席语录,还真的很恰当。
不服气的几个人这下也都泄气了,一个个低着头、无言以对。打那以后,三队社员再也没有谁再敢找陈队长争工分了。
……
再后来,由于关门大队山高路远,孩子们外出读书不便,经公社同意,关门大队在村小学开办了“戴帽”中学班。我被选去做代课老师,从此就离开了关门第三生产小队,结束了我为期一年多的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涯。听说我要走,那些勤劳淳朴的乡亲们都有些恋恋不舍,说再没有人给他们念“最新指示”、读报纸了。陈队长也说:“好小子,去吧,好好干,你会有出息的。”
附图两幅。 (作于2019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