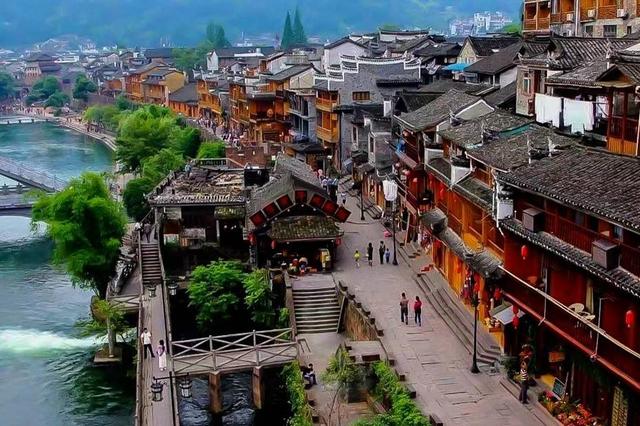(锦衣卫 形象)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杨安,是正统年间大明王朝的一名锦衣卫,官居百户。
官职如其名,明朝的百户属卫所兵制,统兵一百二十人,人,官衔在正六品。
六品官,听起来已经不能算是小官儿,但诸位别忘了,这个六品官是在锦衣卫系统里,而且还是京师的锦衣卫。
京城里高官云集,锦衣卫更是随处可见,所以像杨安这样的百户,一砖头下去,就能砸倒一大片。
杨安虽然在京师里声名不算显赫,但却家庭圆满,有一房娇妻,名讳不详,只知道叫岳氏。
这位岳氏的长相就别提了,明艳动人,貌美如花,是个十足的大美人。
锦衣卫分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对外开放,相对来说算是比较普通的执法部门,而北镇抚司直接由皇帝统领,专门负责皇帝安排的工作,所以权力极大,还拥有单独关押犯人的监狱(诏狱)。
北镇抚司实在是厉害得很,他们执法不必经过明朝任何一处法律部门的准许,而可以私自捉人,拿人,审案,断案,乃至不照会任何人处决犯人,属皇权特许,可先斩后奏。
杨安混得不好,所以只是在南镇抚司供事,而杨安的一位同僚,姓甚名谁已然不详,只知道是北镇抚司的一名校尉。
校尉虽然官阶还排在百户之下,但人家身居北府,身份自然不是杨安一个南府的锦衣卫能比的。
这名校尉心术不太端正,觊觎杨安妻子岳氏的美色,居然欲行不轨之事,想要侵犯岳氏。
没想到岳氏可谓贞洁烈女,誓死不从,校尉几度胁迫,却始终没能得逞。
杨安为人老实,面对同僚骚扰自己的老婆,多有忍让,寻思既然人家也没得逞,那就算了,我也不追究了,这事儿就算告一段落。
事情过去半年之后,杨安染了风寒,几经不治,居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领了便当。
杨安一死,这位校尉觉得自己机会又来了,于是他登门拜访岳氏,表示老杨死了,我也很伤心,留下你一个寡妇,生活实在艰难,既然如此,你不如跟了我,我大小也是个北镇抚司的校尉,挣的只比你前夫多,不比你前夫少,以后你跟我过日子,我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
校尉说了一大堆,但岳氏只说了两个字:
没门。
校尉十分恼怒,回家之后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第二天一早,居然跑到顺天府,控诉岳氏谋杀亲夫。

(顺天府遗址)
读者朋友们都看得出来,这是校尉求爱不成,恼羞成怒,他自己得不到,他就想把岳氏给毁掉。
但校尉的捏造可谓是煞有介事,有模有样,他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的状纸,内容如下:
这个岳氏呢,实在是个狠毒的妇人,我这位同事老杨活着的时候,岳氏就和自己的女婿邱永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两人通奸日久,生怕东窗事发,于是趁着杨安生病时,这对奸夫淫妇通过邻居郝氏的介绍,找来了江湖方士沈荣,这沈荣更加歹毒,献出一条毒计,将烧成灰烬的符纸混入杨安治病的汤药中,杨安饮下,顷刻之间就毒发身亡。
朋友们,这一顿编造,可是把岳氏,邱永,郝氏,沈荣四个人给整惨了。
我们知道,明代的法律,较前代不能算残酷,但也是十分严苛的。
杀人在明代法律中是重罪,而谋杀亲夫更是重罪中的重罪。
《大明律》中,更是专门为谋杀亲夫量身定做了一条罪名。
“其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凌迟处死,奸夫处斩。”——《大明律》
也就是说,如果岳氏伙同剩下三人谋害杨安的罪名成立,那么他们即将统统面临凌迟处死的结局。
校尉告状的地方,是京师顺天府。
顺天府掌京畿之刑,是大明首都最高级别的行政机关,顺天府的最高领导人,顺天府尹,更是朝廷的正三品大员。
府尹大人专管法律,大案小案也办了不少,平时如果碰到这种民间杀人案,可能直接就交给手下人去办了。
但这次非同寻常,因为告状的不是平头百姓,而是个锦衣卫。
府尹大人不敢怠慢,亲自督办,随即将涉案的四人暂时收监。

(《大明律》局部)
岳氏,邱永,郝氏,沈荣四人下了监牢,当然大呼冤枉,因为这事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完全是那位怀恨在心的校尉捏造出来的。
但奈何当时顺天府的执法实在不是很人性化,动辄就严刑逼供,四人在监牢里结结实实地挨了几顿揍。实在挺不住,纷纷屈打成招。
犯人认罪了,案件到这儿也差不多就算是结案了。
但我们知道,明朝在刑法方面的问题上,是十分慎重的,尤其是对死刑极为慎重,所以如果顺天府要结案,要把这四人处斩,还需要经过明朝另外三处法律部门的同意才行,且,必须是这三个部门都同意了,都点头了,犯人才能处斩。
这三个法律部门分别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
这个流程是十分复杂的。
顺天府要先将案件的卷宗移交到刑部,刑部查验过后,扣了公章再呈送都察院,都察院看过之后,觉得没问题,再移交大理寺,大理寺如无异议,再交还刑部,但这还没完,刑部拿到卷宗,不能耽搁,需直送到天子案前,皇帝看了没意见,这才算完事儿。
府尹大人十分照章办事,亲自将卷宗送到刑部,刑部的侍郎草草看过,没有异议,卷宗又送到都察院,都察院的御史翻阅卷宗,也无异议,于是卷宗又被送到大理寺。
案件到了大理寺的时候,是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
这一年,正赶上大理寺人事调动,一个叫做薛瑄的人正好来此任职。
薛瑄,字德温,山西运城人氏,永乐十九年进士,时任大理寺少卿。
大理寺少卿,即大理寺的二把手。
这位新官上任的二把手拿过卷宗,翻来覆去这么一看,认为疑点重重,应该再审。
怎么个疑点重重呢?
我们知道,明代审理犯人,是要有供词的,犯人口述罪状,由当堂的师爷写下,最后再叫犯人亲自画押,这就算是认了罪。
卷宗中的供词共有五份,其中两份是岳氏的,剩下三份是邱永,郝氏和沈荣的。
后面这三位的供词倒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仨顶多算是从犯,所以只在打了一顿之后就草草认罪,然后签字画押。
但岳氏是案件主谋,所以刚到顺天府的时候审了一次,在牢里打完之后又审了一次,便多出一份证词。

(薛瑄 画像)
薛瑄拿过岳氏的两份证词一看,发现初审时的岳氏证词大呼冤枉,死不认罪,而收监之后的证词却是唯唯诺诺,什么都认。
薛瑄也算是官场上的老油条了,从宣德三年,即公元1428年就开始做官,干得一直是和法律相关的工种,所以他一眼就看出来,岳氏前后供词不一,很显然是被逼供之后,屈打成招的。
既然是屈打成招的,那么此事必有冤情,容不得马虎,必须再审。
薛瑄看罢卷宗,并未盖章签字,卷宗又被送回刑部。
刑部一看,大理寺没签字,十分疑惑。
咋地,都察院,顺天府都认为没有问题,就你们大理寺搞特殊呗?
于是刑部又把卷宗移交到大理寺,结果没过两天,又被大理寺给驳回,原封不动地把卷宗送了回来。
刑部和大理寺的梁子算是结上了。
刑部的官员们一口咬定,案件没有问题,请大理寺快点走个流程就算完事儿,而大理寺少卿薛瑄也十分倔强,认为人命关天,由不得半点马虎,必须发还重审。
卷宗送来送去,搞得夹在中间的都察院很不耐烦。
因为案件毕竟在都察院也经了一手,案子一日不结,都察院的大小官员们也要跟着一起折腾。
都察院有位御史,名叫王文,对薛瑄一根筋的行为十分不理解,于是多次拜访大理寺,找薛瑄理论。
王文表示,大家都是朝廷命官,都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混口饭吃,你那么较真干什么?老兄你就别倔强了,早点结案,大家也好早点收工。
没想到薛瑄并不买王文的账,反而讥讽王文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按说薛瑄是个读书人,知书达理,平时和王文也没什么恩怨,并不应该对王文的态度如此之差,之所以薛瑄态度不好,其实是有原因的。

(王文 画像)
我们知道,正统皇帝朱祁镇十分宠信一位叫做王振的宦官。
王振,河北蔚县人,永乐年间进宫,几经摸爬滚打,终于在正统一朝混成了皇帝跟前儿的红人,极受皇帝信任。
这位宦官手握大权,结党营私,势力非常庞大。
朝廷里的官员们一看王振得势,纷纷攀附,但薛瑄却十分不以为然。
这帮趋炎附势的大臣们,有给王振送钱的,有给王振送礼的,甚至还有认王振当干爹的,唯有薛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根本不把王振放在眼里。
他对宦官干政专权的行为十分深恶痛绝,恰巧王文正是王振的党羽。
所以薛瑄对王文恶语讥讽,倒也十分可以理解了。
薛瑄只是单纯的反感王文,反感宦党,但在王文眼里,这事儿可就变味了。
自己这个都御史,全靠王振公公提拔,而薛瑄卡着这个案子不放,明摆着就是在跟王振叫板。
非但王文这么想,朝廷里的另外一位仁兄,锦衣卫都指挥使(锦衣卫高级领导)马顺,也是这么想的。
马顺同样是王振的死党,在他看来,这个案子的始作俑者,是锦衣卫的校尉,薛瑄跟这么个小小的校尉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这个都指挥使过不去,和自己这个都指挥使过不去,就是和王振公公过不去。
薛瑄当然也知道案子这么悬着不是办法,刑部和都察院的官员们整日来催问,搞得他压力很大。
这个时候呢,薛瑄手下一个叫张柷的官员,为薛瑄提供了一条解决思路:
既然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意见不统一,那么案子也别在咱们这儿压着了,咱们直接交给皇帝,让天子来审理不就得了吗?
薛瑄一听是个办法,于是也不再耽搁,带着卷宗就奔皇宫去了。
到了皇帝跟前儿,薛瑄扑通一跪,表示我这有个案子,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意见不同意,我们实在搞不清楚,还是请皇上圣裁吧。

(明英宗朱祁镇 画像)
正统皇帝朱祁镇不是傻子,他眼珠一转,一寻思不对啊,你们三个部门联起手来都解决不了这个案子,你让我圣栽?我怎么圣栽?这不是成心让我下不来台么?
朱祁镇不想圣栽,但案子已经送到自己面前,自己必须得处理,于是他表示,不是我不处理,是你们连案件都没搞明白就让我来决定,这不是闹着儿么?我看这样好了,我在都察院里选一名御史,亲自下去查案,查出原委,我再做决断。
皇帝这一脚皮球踢得实在是巧妙,他是绝对不趟这个浑水的,自己插手案件,断对了皆大欢喜,要是断错了,到时候史书记载自己是非不分,岂不是遗臭万年?我才犯不着冒这个风险呢!
于是,皇帝下旨,着都察院御史潘洪全权负责,彻查此案。
皇帝把这件事交给潘洪,还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
因为这个潘洪,一来并非王振余党,二来也不是薛瑄故交,属于是两边都不靠,因此用起来十分放心。
结果这个潘洪还真没辜负皇帝的期望,他下到民间,细细查访,先是跑到杨安家的左邻右舍里打听了一番,发现这对夫妻在坊间口碑甚佳,一直很恩爱,这说明岳氏跟邱永通奸这事儿很有可能是谣传捏造,岳氏根本没有什么杀人动机。
之后,潘洪又找来当初替杨安治病的郎中,以及查验杨安尸身的仵作,从两人口中得知,杨安并无中毒迹象,死因乃是身体虚脱,泻痢而亡。
最后,潘御史又陆续查访人犯郝氏和沈荣的亲故,询问他们在案发前后的行为是否有异,结果得出的结论都是两人平时遵纪守法,从来没干过什么作奸犯科的事儿,而郝氏找来沈荣,也并非是岳氏串通,行谋害之事,而是岳氏托邻居郝氏请来方士沈荣,给自己的久病不愈的丈夫做做法事,驱邪消灾的。
潘御史一顿查访,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不久之后,他将所了解到的情况一一回禀皇帝,并且附上了自己的意见,即杨安为病逝,自然死亡,岳氏四人则是含冤入狱。
皇帝拿过潘洪的奏疏一看,事情简单明了,证据属实,的确是冤案,没啥可说的。

(潘洪 画像)
既然没啥可说的,皇帝当即下旨,释放岳氏四人。
但皇帝前脚下完旨,后脚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区区一桩刑事案件,你们有关部门不能自己解决,还得折腾我来来回回下两回旨?
这么点小事儿就得麻烦我,朝廷白给你们这帮人发俸禄了?
朱祁镇十分不悦,随即又下了一道旨意:
刑部率先经办此案,查案不实,以至百姓蒙冤,经手此案的官员,实属工作不力,罚俸三月,以儆效尤。
刑部当然不肯自己背这个黑锅,他们向皇帝上表,表示造成这桩冤假错案,我们刑部的确是有责任,但都察院也经手了,他们也有责任,要罚我们,都察院也得跟着受罚。
结果都察院一听刑部跑去找皇帝告状,他们也跑来找皇帝诉委屈,御史们认为,都察院固然失职,但此案首告是锦衣卫的校尉,锦衣卫也有责任,要罚我们都察院没问题,必须连锦衣卫一块处罚了。
锦衣卫当然也不干,我们是首告不假,但刑部失职在先,都察院失职在后,要是罚我们三个月,得罚他们半年才合理。
这回热闹了,刑部咬都察院,都察院咬锦衣卫,锦衣卫再咬刑部,三个部门来回攻击推诿,谁都不想让谁好受。
朱祁镇一看这不行,这要三个部门都罚了,实在是打击面太广,于是又把罚俸的旨意给撤销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按说大家也算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结果,案件也应该告一段落,但朝堂之中,仍然有一个人愤愤不平,心里始终有股气儿撒不出去。
这个人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

(马顺 形象)
马顺可以说是恨极了薛瑄,这个不识抬举的大理寺少卿不仅拿着杨安案跟锦衣卫,跟自己处处做对,还惹怒皇帝,差点把锦衣卫一整个部门也拖下水。
但记恨归记恨,薛瑄严正执法,坐的端行的正,马顺就算想要对付薛瑄,一时之间还真没什么办法。
但不久之后,一件如出一辙的案子,又把马顺和薛瑄引到了一个十分对立的位置。
锦衣卫中有位指挥使病逝,留下一位正妻,一位妾室,正妻咱们按下不说,先来讲一讲这个妾室
这位妾室芳龄十九,生的妖娆妩媚,是个尤物。
朝中权势最大的宦官王振有个干儿子,叫做王山,这个王山心思不轨,想要把这位指挥使的遗孀弄到自己府上来做小妾。
这事儿本来无可厚非,改嫁也绝非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但王山想要迎娶小妾的行为却被这位指挥使的正妻贺氏阻挠了。
贺氏表示: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王山和这位小妾都很诧异,你又不是我爹我娘,你不同意有什么用?你算哪儿根葱?
但贺氏很快搬出了传统礼法,她指出,按乡约习俗,丈夫病逝,妾室需得服丧三年,如今三年未满,你就想改嫁?没门!
结果王山恼羞成怒,居然指使这位小妾诬告贺氏请方士施法,谋害亲夫,应当下狱处死。
这剧情是不是很熟悉?
是的,和前不久发生的杨安案如出一辙,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王山是有靠山的,他干爹是权宦王振,他上下打点一番,案件直接绕过了顺天府和刑部,到了都察院的手里。
都察院的官员们估么也是受了王山的恩惠,草草结案,判处贺氏死刑。
卷宗从都察院出来,送往大理寺,结果又被薛瑄给拦下了。

(大理寺)
薛瑄拿过卷宗一看,案情似曾相似,认为铁定又是一桩冤案,于是予以驳回,要求发还重审。
并且,薛瑄不仅驳回了案件,还向正统皇帝朱祁镇上了几道折子,弹劾都察院的御史们审案,断案实在荒谬,应以渎职之罪论处。
都察院也不是吃干饭的,一看薛瑄弹劾自己,立刻咬出幕后黑手,他们表示,不是我们都察院渎职,而是上交卷宗的锦衣卫部门说案件已定,让我们走个流程就得了。
经过这么一闹,锦衣卫又成了众矢之的,广受非议,还在朝堂上被皇帝臭骂了一顿。
马顺实在是太生气了,合着这个薛瑄,就是和锦衣卫过不去了是吧?
他怒火中烧,心里想着如果不是当初那个告假案的校尉,自己也不会落到这么被动的境地。
于是,马顺把这位校尉叫来,绑在树上,狠狠的用鞭子抽了一顿。
没想到这位校尉十分嘴硬,死活不承认自己捏造事实,而是一口咬定,是御史潘洪调查不实,包庇真凶。
校尉的一句话点醒了马顺,他认为杨安案还不算完,自己还能做做文章,替自己扳回一城。
皇帝都已经下旨结案,还能怎么扳呢?
马顺自有他的办法。
他把杨安案的涉案人员,即岳氏四人抓到午门,挨个绑在树上抽,这四位平头百姓实在遭不住这罪,于是又在马顺的逼迫之下再次翻供,又在状纸上写下来本不属于自己的罪行。

(午门)
拿到岳氏四人的认罪状词,马顺算是有了底牌,他拿着状词跑到朱祁镇面前去告御状,皇帝一听居然还有这等隐情,十分震怒,于是着马顺统领锦衣卫,再度彻查此事,务必水落石出。
马顺这回算是翻盘了,他得到了皇帝准许,立刻带着锦衣卫到大理寺抓人。
理由很简单:岳氏四人既然再次认罪,就说明他们的确是命案真凶,既然他们是命案真凶,你们大理寺屡屡说这是冤假错案,岂不是集体贪赃枉法,包庇凶手?
于是,大理寺少卿薛瑄,以及大理寺中有头有脸的官员,如顾惟敬,贺祖嗣,周观,费敬都被擒拿,整个大理寺几乎被马顺一锅端了。
而审理这帮官员的工作,则落到了都察院的身上。
该说不说,负责此次案件的都察院官员,正是那个之前和薛瑄一直不对付的御史王文。
王文这算是捞着了,一顿严刑拷打,这帮大理寺官员们都是文臣,哪儿能经这么收拾,于是纷纷招供。
当然,还是屈打成招。
但就算是屈打成招,这事儿也实在是很难办。
枉法必然贪赃,大理寺的官员们如果想要帮助岳氏四人脱罪,必然是要收受他们的好处的。
但岳氏四人都是平头百姓,平日里素无积蓄,所以都察院愣是一分钱赃款也没查出来。

(都察院)
当然了,肯定查不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收受贿赂这回事儿。
坐实大理寺官员们的罪名,是需要人证物证的,但现在既无人证,也无物证,要惩处这些人,实在是难以服众。
最后,御史王文居然十分滑稽的想出了这样一条大理寺官员们包庇岳氏四人的犯罪动机,那就是:
方士沈荣是苏州人,而大理寺官员们大都也是苏浙一带人士,这帮官员们为了营救同乡,所以才行包庇之事。
滑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此裁定之后,这帮人的供词又打包成卷宗,送往刑部审阅。
刑部官员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来,他们清楚的知道大理寺的这帮官员们是被冤枉的,这一切都是马顺搞的鬼,但二来,大理寺树大根深,况且被马顺给收拾成这样,区区一个刑部,又怎么敢和马顺作对?
或者说,又怎么敢和马顺背后的王振作对?
所以思量再三,刑部选择了缄默。
他们照章办事,不闻不问,扣上公章,送交皇帝御前。
此时的朱祁镇,已然被马顺捏造出来的事实蒙蔽了,他御笔亲批,责成有关部门把大理寺的官员们依罪论处。
结果,大理寺的官员们,处斩的处斩,流放的流放,免职的免职,真叫是一个死走逃亡伤。
忘了说,那个当初彻查冤案的御史潘洪,也累受牵连,流放到了山西。
被马顺诬陷为罪魁的大理寺少卿薛瑄,则被处以死刑,择日处斩。
而行刑官,还是薛瑄的死对头,都御史王文。
不过薛瑄毕竟是主角,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关押他的监牢幽深黑暗,潮湿阴森,但他却丝毫不惧,每天拿着本《易经》捧读,十分气定神闲。

(《易经》局部)
老实说,我想除了皇帝被蒙在鼓里之外,大明王朝的所有官员都应该清楚,薛瑄是被冤枉的。
封建王朝并非时刻冷漠,各扫门前雪,不管瓦上霜,一众大臣们实在看不惯马顺的行径,纷纷伸出援手,设法营救薛瑄。
想要翻案?
估计是翻不动了。
这一桩原本简单明了的杨安案,被大家来来回回这么一折腾,已经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步,所以大臣们的诉求很简单,那就是希望皇帝可以宽恕薛瑄的罪过,留他一条命。
这件事儿看似是皇帝说了算,但其实,是宦官王振说了算。
朱祁镇向来宠信王振,国之大事,他不找内阁商量,专门找王振研究,所以王振在这件事儿上,是有着一定的话语权的。
王振,在介绍他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加上一句:大明王朝第一代专权宦官。
是的,这事儿要是让魏忠贤这种老谋深算的权宦摊上了,别说是薛瑄,就连替薛瑄求情的大臣们,魏忠贤也不会放过。
但王振毕竟是初代权宦,实在没什么工作经验,他觉得事已至此,该打压的也打压了,该收拾的也收拾了,实在没有必要和这帮大臣们过不去,于是便向皇帝说了两句求情的话。
皇帝一看,既然王振都松口了,那这事儿就算了吧。

(王振 画像)
最后,薛瑄免死,但一撸到底,被贬为了平民。
薛瑄虽然活了下来,但岳氏,邱永,郝氏,沈荣这四个无辜蒙难的百姓却早就被砍了头。
这真是四个可怜人。
他们终其一生,也没能洗刷掉自己身上的冤屈。
史书上对他们罕有记载,但对朝廷各部门之间的较量,记录的倒是非常详实。
他们眼见得救又重新坠入深渊是一种什么感受?
他们如何蒙冤,他们遭受了什么样的耻辱,他们遭到过什么样的毒打,作者查无史料,不得而知。
杨安案到此,终于尘埃落定了。
但故事还没有讲完。
所谓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不久之后,土木堡之变爆发,即正统皇帝朱祁镇带着五十万大军出征瓦剌,结果被瓦剌人俘虏,景泰皇帝朱祁钰临危受命,成为了新皇帝。
朱祁镇被俘虏了,跟着朱祁镇一起出征的王振也身死乱军之中。
愤怒的朝臣们请求新皇帝清算王振的余党,而锦衣卫马顺则成了他们发泄愤怒的对象。
马顺同志的故事值得再写一篇文章,但篇幅所限,我只能告诉大家,他死的很惨。
这位一手酿成冤假错案,害人无数的锦衣卫都指挥使的最终结局是——在朝堂之上被大臣们徒手群殴至死。
而那个曾经作为马顺帮凶的王文,下场也没好到哪儿去。
朱祁镇一被俘虏,他立刻对新皇帝朱祁钰投怀送抱,成为了新皇帝的心腹,但没想到之后又爆发了夺门之变,朱祁镇又干掉了朱祁钰,重回帝位,那么王文这个墙头草当然会被清算。

(明代宗朱祁钰 画像)
他被人诬告谋反,这一回,冤假错案落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但这回没有人再来营救他了。
值得一提的是,负责前去王文府上捉拿他的,正是后来从平民提拔起来又重新做官的薛瑄。
我想,薛瑄去捉拿王文的时候,两人一定是有过短暂接触,乃至交流的。
而当他们四目相对之时,会不会各自在内心里想起多年前的这桩往事,想起这四条无辜的人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