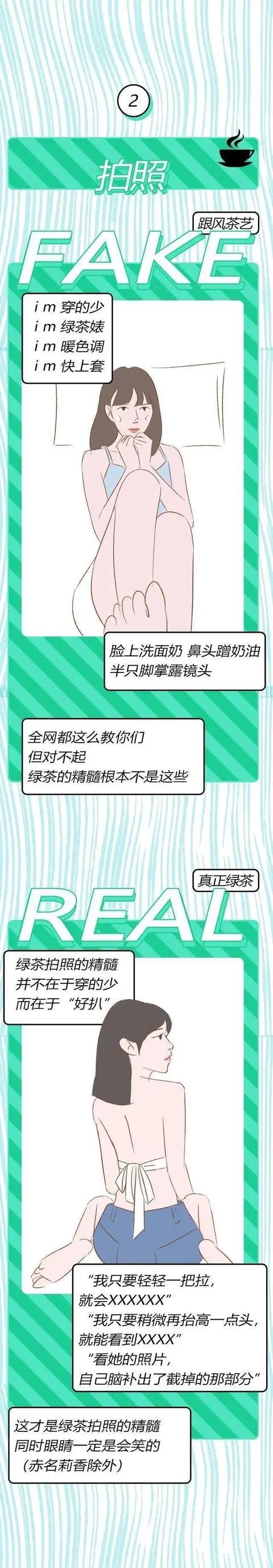《图形、技术、人文——郑晓华学术论文随笔集》封面
关于书法,中国书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郑晓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实用和审美本来是两条线,但依托于一个共同的母体,审美书法对实用书法实现全覆盖,使人们无从分辨哪些书法是表现性的,是纯艺术,哪些是实用性的,是‘非艺术’。这样的艺术‘生态形式’,在世界艺术史上不多见。”
对书法艺术“生态形式”的发现与认知,是当代书法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尽管传统书法理论以它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植根儒释道的价值观念,典雅丰赡的语言魅力,阐释了文字结构的文化属性和文字书写的艺术规律,进而引发文字书写的审美之辩,然而,文字书写的实用与审美的关系,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其中涉及艺术的发生学,涉及中国书法的艺术定位,涉及当代书法艺术的社会影响和国际传播。一句话,中国书法的复合型结构,从一开始就给我们留下了一道难题。尤其是文言文退出公共文化领域、硬笔的普及、电子计算机汉字处理系统的广泛应用,严重挤兑了毛笔书写的社会空间,也对书法的“生态形式”做出了历史性调整。
于当代书者而言,这是文化挑战,还是一个乱摊子?
当我们深陷书法的历史谜团,一批有历史责任感、学术担当和国际视野的学者,试图从源头开始,寻找中国书法的最初形态,梳理中国书法的发展变化过程,确定中国书法的审美原则。郑晓华就是其中之一,他新近出版的《图形、技术、人文——郑晓华学术论文随笔集》就是证明。
作为60后学者,郑晓华拥有学术优势。1979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后去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在书法家欧阳中石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长期的高校教学经验,扎实的学识积累,丰富的书法创作实践,助推郑晓华深入传统书法的历史深处,从多维视角,观察书法的人文形态,以新的哲学角度考辨书法的理论原理,以现代精神聚焦书法的艺术魅力。于此,郑晓华对书法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书法的当代处境和国际困境,做出了当代学人的沉思和回答。
首先,郑晓华从“生态形式”上高度概括书法的特殊性。他说:“书法是汉字——中国书面语言的副产品。书法为文字服务。换言之,书法艺术,为文字而产生,为文字传播而繁衍。”进而强调:“书法和文字,共生、共进、共荣,相为表里,不可分解。”显然,书法是有实际用途的,书写的最初时刻是为了展示文章的意义,其次才能提及书法的高下。王羲之在《兰亭序》中讲得明白——“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他看中的是自己的文章,至于书法,是下一个环节的事情。苏东坡的文学代表作,也是书法代表作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是中国书法实用与审美的集大成者。《洞庭春色赋》写于1091年,他被程颐等人构陷,贬到颍州任职。苏东坡对政治沉浮似乎习以为常,但心情还是郁闷,有了“追范蠡于渺茫,吊夫差之惸鳏”之叹。1093年,苏东坡又一次宦移,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总管,出知定州军州事。不久,又到定州任职。此间,写了《中山松醪赋》。其中“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的表白,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刻画。《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的文章草稿没有存留,我们所看到的书法,是1094年2月,苏东坡再一次被构陷,自定州赴英州,途经河南睢县,以他“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的笔调“乃取李氏澄心堂纸,杭州程奕鼠须笔,传正所赠易水供堂墨,录本以授思仲,使面授传正,且祝深藏之。传正平生学道既有得矣,予亦窃闻其一二。今将适岭表,恨不及一别,故以此赋为赠,而致思于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从也”。重新抄写的“二赋”手卷即是中国书法史经典之作。这也是中国书法从实用到审美的“生态形式”的演绎过程。
基于对中国文化史与书法史的考察,郑晓华对书法“生态形式”的演绎过程作了总结和剖析:“由于书法艺术以中国书面语言形式体系为载体,与实用书法同体、同步发展,这就造成世界艺术史上也难得其匹的罕见现象:汉字书面语言体系的功能区域,几乎全部被艺术样式所覆盖。”
以往,我们对书法的定义过于笼统和模糊,其中的原因就是不能厘清书法的实用与审美的关系问题。作家郑振铎在《哭佩弦》一文中忆及与朱自清谈论书法的往事,当年有几位青年怀疑书法的艺术属性,起于对书法实用与审美关系的混淆。其实,这种特殊而微妙的关系,是对“世界艺术史上不多见”的书法艺术的背书。这样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书法的实用功能减弱,审美价值提高,有的人开始鼓噪书法的点线结构是书法的核心,书法与文字无关,与写什么无关,笔墨的客观呈现,便是书法的根本,这种认知经不起推敲。但是,这种浅陋的认知具有欺骗性,如果缺乏引领,不敢批驳,假李鬼就会变成真李逵,危害性不言自明。郑晓华有文化使命感,他在传统书论和经典书法作品中寻找依据,再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符合历史实际与文化常识的解析,还原书法艺术的本来面目。郑晓华在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的论述中,体会到书法的本质规律,张怀瓘在《书仪》中说:“昔仲尼修书,始自尧、舜。尧、舜王天下,焕乎有文章,文章发挥,书道尚矣。”在《文字论》中又说:“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古人的精辟论断,铺平了中国书法从实用到审美的通畅路径,也揭示了中国书法的美学特征。为此,郑晓华讲道:“书法艺术以文字为母体,因文字书写而产生。它的所有语言样式,所有繁纷复杂的‘语法’、技术、规则,都傍依文字而产生,离开文字而无从立其身,这就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特性。”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特性有了基础的认知,对中国书法作品的高下也就有了符合艺术真相的判断。一些人煞有介事地说,书法艺术作品的标准很难界定,进而悲观地表白,书法艺术作品没有标准,至少没有统一的标准,好与坏、强与弱、高与下,难以把握。对艺术作品而言,有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姑且不论,对艺术作品一定存在美学共识,也就是遵循传统的艺术规律,对书法的“语法、技术、规则”有结构性的理解,自然能够找到欣赏书法、理解书法、判断书法的钥匙。郑晓华的著作以严谨的学风、犀利的目光,从繁杂、迷乱中理出一条简明、清晰的线索,让我们看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书法,如何作用于中国文化和审美。难能可贵的是,郑晓华的理论研究依托改革开放的宏大背景,他大胆汲取新的思维方法、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研究手段,赋予传统书法理论研究更多的活力和可能性。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立足于中国书法雄厚的文化基础,郑晓华以拿来主义的勇气,直面强势的国际文化,辨清其中奥义,拓展当代书法走出去的可行性路径。郑晓华对传统书法的研究,思路清晰,成果丰硕,他熟知书史书论,也谙熟临池实践,了解书法艺术的生命表现过程,能够听到书法的呼吸和呼唤,他对书法的艺术魅力有着强大的自信。
聚焦书法的理论原理是为了发现书法的艺术魅力。《图形、技术、人文——郑晓华学术论文随笔集》的第一部分“从国际学术视野看书法”,到第二部分“书法的艺术形态学研究”,再到第三部分“古典书学浅探”,郑晓华构筑了一个三角图形,其中一端以主观性和国际性的视野,基于古今中外的知识坐标,审视中国书法的过去、今天与未来。正如郑晓华所讲,书法艺术的“生态形式”,在世界艺术史上不多见,因此,他必须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人生经验,艺术创作实践,还有改革开放以来观察、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收获,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书法,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书法。一端进入书法的内部,从本土文化的实际,摹写书法的事实。他从“线条论”“结构论”“墨韵论”的维度,透视中国书法的艺术构成,对“世界艺术史上不多见”的民族艺术,做出了开放性的阐释。另一端回归中国书法理论原型,通过重温传统书法理论的思想形态、文化特征、美学观念,紧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法理论家所关心的重大书法问题,一步步揭开了蒙在书法头顶上的神秘面纱。他说:“书法的情况特殊,它是始终和生活原型‘捆绑’在一起——所有的书写场合(不管是实用还是审美),都可以用书法。我想这可能是书法艺术最特殊的地方。他确实挑战了世界学术界原有的对‘艺术’概念的界定,也挑战人们对艺术特性认知的极限。这也是国际学术界较长时间不能认识到中国书法不仅仅是‘文献档案’而且更是‘艺术品’的原因。”
从“文献档案”到“艺术品”,又从“艺术品”到“文献档案”,也许就是中国书法的“生态形式”,在世界艺术史上的确不多见。既然是艺术品,它的魅力何在?这也是郑晓华关心的问题。
在郑晓华的心目中,书法以汉字为载体,通过具有特殊笔情墨韵的汉字形象的创造,表达书法家思想情感和审美理想的艺术。他强调:“立足于这一基本概念,好书法,应该是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充分个性化、富有感染力的表现形式的统一。”至此,中国书法艺术与其他艺术样式有了共同的人文特征和美学张力。
以往,我们愿意在书法的“闲情”与“趣味”上停留,似乎书法是极端私人化的有限表达,不具有刻画“生命形象”、陈述“现实情节”的能力。其实,这是我们的短视,是因为我们不肯或不能进入书法的核心地带,自然感受不到中国书法的艺术辐射力。郑晓华看到了这一点,他要超越,他拥有新的思想资源,站在新的时代制高点,掌握了中外相关文献,指出中国书法的历史约定。首先指明,书法是汉字单一时空的有序书写,其次指明,高端书法,都是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完美笔墨形式的高度统一,最后指明,实用书法、纯艺术书法,两者同体共生,不可分离。郑晓华旗帜鲜明地告诉我们:“由于书法艺术既有抽象形式,又有文字的语义这样的特性,那也必然带有思想内涵。这使书法艺术拥有其他视觉艺术不具备的双重性;它既是视觉的‘铺叙’,又是思想的‘言说’;它既能讲道理,又能讲故事;既能叙事,又能抒情。”如果说,这是郑晓华对中国书法的结构性定义,那么,他提出的书法艺术的三重境,即世俗境、艺能境、哲人境,则是对书法的艺术魅力所做出的细致说明。他认为,世俗境靠的是技术,是书法家的本色,可以满足世俗需求;艺能境是把书法当作艺术,表现审美理想;哲人境是把书法当作“道”,它是人生智慧对笔墨个性的征服。这个三重境的后面,就是“彼岸”,在郑晓华的心目中,彼岸就是“直抵满天花雨之梵界”。基于历史传统和当下思潮的中国书法的三个历史约定和三重境,展开了当代书法理论研究的新面目。
作者:那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