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声明:本文为新华网客户端新媒体平台“新华号”账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华号的立场及观点。新华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文/马库斯·瓦尔茨(Markus Walz) 德国莱比锡应用技术大学理论与历史博物馆学教授。

德国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 Rufus46/CC BY-SA 3.0
德意志是首批博物馆学术语——博物馆展陈学(museography, 1727)、博物馆学(museology, 1830)和博物馆学家(museologist, 1845)的发源地。作为专业博物馆工作经验和指导的博物馆学含义出现在1845年,第一份以博物馆学这个词为标题的期刊于1878至1885年在德累斯顿出版。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论述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宣布博物馆学学科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强调博物馆实践是唯一的学习之道。有经验的博物馆从业者当时似乎是唯一可被接受的教师,因此,卡尔·柯特韶(Karl Koetschau)馆长成为首位德国博物馆学教授(波恩大学于1922年任命他为名誉教授)。有关博物馆助理资质的讨论牵涉到了适合女性从事的工作这个问题,德国首个培养女性记者、图书管理员、博物馆管理者的学院于1899年开幕。
冷战时期,西德经历了两次博物馆学理论研讨会和两场有关设立博物馆学教席的讨论——虽然二者都没有结果。东德与当时发达的苏联和捷克博物馆学有紧密接触,但仅仅找到了一些权宜之计,例如设立自然史博物馆学教席(1980)和一个为无大学文凭的博物馆从业者设立的学院(1954年以来)。如今,统一的德国给人非常不同的印象——上述学院继续作为研习项目存在,另有44个博物馆相关的研习项目在发展中。并不存在一个“博物馆学高地”,因为这45个研习项目分散在37所大学,整个德国仅有四个博物馆学或“博物馆科学”教席。
产生首批术语:
博物馆展陈学、博物馆学、博物馆学家

德国新绘画陈列馆/1880 © 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德意志是藏品描述和藏品理论建设方面的先驱。塞缪尔·奎谢贝格(Samuel Quiccheberg, 1529–1567)是富商汉斯-雅各·富格(Hans-Jacob Fugger)的图书管理员,后来成为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Albrecht V)的顾问,负责组织公爵在慕尼黑的图书馆和艺术收藏。1565年,奎谢贝格用拉丁文发表了他对普世收藏(书籍、版画和各种器物)结构的设想,“收录珍宝和宇宙异象的庞大手册的记载或标题”(Inscriptiones vel tituli theatri amplissimi, complectentis rerum universitatis singulasmaterias et imagines eximias ...)。
德意志也是首批博物馆学术语博物馆展陈学和博物馆学的发源地。有关的德国文献(18和19世纪出版)被彼得·范·曼施(Petervan Mensch)和弗朗索瓦·梅来思(François Mairesse)重新发现。博物馆展陈学这个术语于1727年作为一个装饰标题出现。汉堡商人卡斯帕尔·弗里德里希·延克(Kaspar Friedrich Jencquel)用德文写了本书,但以巴洛克的方式为其起了古希腊和德语的双语标题,极长的德语标题详细描述了内容,而仅仅一个单词的古希腊语标题则提纲挈领:“博物馆展陈学,或用于博物馆的正确理解和有效结构的指导(Museographia oder Anleitung zum rechten Begriff und nützlicherAnlegung der Museorum, oder Raritäten-Kammern)。”作者从未在正文中使用“博物馆展陈学”这个术语。
博物馆展陈学和博物馆学的首个确切意义是德国古典考古学家创造的。萨克森王室古物收藏主管卡尔·奥古斯特·伯蒂格(Carl August Böttiger) 在1806年讲授了一门课程,并在同年将其印刷。他将其中对有关博物馆收藏的古典器物的描述称为“现存美术馆的一份调查或所谓博物馆展陈学的一份总结”。全球首份古典考古学手册于1830年由哥廷根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卡尔·奥特福利特·穆勒(Karl Otfried Müller)出版。他阐发了艺术的测绘学,从而延续了伯蒂格的博物馆展陈学理念:原始地点(尤其是对于建筑或其废墟)、发掘地点、一件艺术作品目前的保存地点——穆勒把这第三种测绘学称为博物馆展陈学或其近义词博物馆学。显然,穆勒(以及伯蒂格)的博物馆展陈学是艺术史和考古学的补充。这一博物馆展陈学意义在德国存在到了20世纪早期。

德国柏林旧国家美术馆 Mathias Krumbholz/CC BY-SA 3.0
1845年,德语再次引领了博物馆学论述。慕尼黑巴伐利亚王室自然屋的保管人亚历山大·赫尔特(Alexander Held)出版了他的《展示自然史》,并在书中的一部分呈现了他“有关属于动植物和矿物王国的器物的收藏、准备、分类、展示、保存和演示的经验和指导”,并称此内容为博物馆学。赫尔特似乎也是“博物馆学家”(museologist)——这一指博物馆从业者的衍生新词的发明者。
作为被宣布但不存在的科学的博物馆学
第一份以博物馆学为名称的期刊在1878年至1885年间出版。那是德累斯顿萨克森王室宝藏“绿穹珍宝馆”馆长约翰·格尔格·西奥多·格莱瑟(Johann Georg Theodor Graesse)私人发起的《通用博物馆学与相关科学期刊》(Journalfor general museology and related sciences)。格莱瑟一篇文章(1883年出版)的开头经常被引用:“如果三十或乃至二十年前有人谈论或著述论述作为一门学科的博物馆学,很多人恐怕会以同情、轻蔑的微笑回应。如今,局面确实不同了。”而下文并不与开头数行文字搭调。格莱瑟通过引用当时的例证,探讨博物馆从业者的必要知识。
这种矛盾态势在数十年中塑造着德国的论述。艺术史专家、博物馆馆长、德国博物馆协会联合创始人卡尔•柯特韶曾在1918年协会第二届全会介绍了他有关博物馆学的思想。在他看来,博物馆学已经取得了“拥有独立重要性的特殊学科”的地位,尽管“这一学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博物馆实践捆绑,可能会消失在博物馆实践中”。从1905年开始,柯特韶编辑《博物馆学》(Museumskunde)期刊。在第一期中,艺术史专家尤里乌斯·莱申(Julius Leisching)也有类似论述:“这一(博物馆)科学存在吗?可惜,还没有。”但几行字之后,他强调,现实生活即博物馆本身就是博物馆从业者最好的学校。在他看来,最有效的学习途径不是读书也不是讲座,而是在资深专家指导下对丰富藏品进行认真的研习。
柯特韶对博物馆学的制度化有几点想法。他描绘了一个由德国博物馆协会组织的、为年轻博物馆从业者设立的暑期学校。他还提议把博物馆学纳入艺术史课程——但有个特别条件:一名博物馆馆长应该加入教学团队。自1920年1月,他自己在波恩大学艺术史研究院组织讲座,与此同时还引领着杜塞尔多夫市的艺术收藏活动。1922年,哲学系任命他为“美术技术与博物馆学”名誉教授。柯特韶代表了德国最早的博物馆学教授教席,但实际上,他的(总共)26次讲座中仅有3次涉及博物馆学层面。

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 Jörg Zägel/CC BY-SA 3.0
通过操作还是通过念专门学校来
学习博物馆工作?
19世纪晚期出现了一种为德国文化机构培养未来从业者的典型模式,即所谓志愿制(volunteering)。一个有大学文凭(如果是人文学科需要有博士学位)的人在一段时间(半年到两年不等)内在一家那种类型的重要机构(例如一家大学图书馆、一所州立博物馆)参加一个全职受训项目,以学习如何将其课本知识用于实践。虽然志愿制得名于志愿兵,但与志愿兵不同,受训项目没有报酬,且没有之后得到一个有报酬工作的愿景。由于要招募免费工作的学者,志愿制青睐富有的年轻男性。
直到20世纪早期,多数高阶职位不向德国女性开放,而巴登大公国是首个在大学招收女大学生的德意志邦国(1891年开始招收自然科学女学生,1901年全面放开),而普鲁士王国是最后一个,到1908年才开放。这一局面酝酿了一种特定的论述,这种论述交织了女性适合何种工作的问题以及对拥有学术团队的机构的非学术出身助理(早在19世纪晚期就针对图书馆进行了讨论)的思考。
在这一背景下,1899年出现了一次私人创举。退休的斯特拉斯堡帝国图书馆管理员克里斯特里珀·哥特赫尔特·霍廷格(Christlieb Gotthold Hottinger)自1895(1896)年住在柏林附近。他与一个亲戚——当地贸易商的遗孀安娜·里本斯坦(Anna Liebenstein)一起,计划成立一个女性学院。首座校舍于1899年秋在柏林-苏特安德(Südende)街区落成,包括一座有5000本藏书的女性图书馆,报业、图书馆和博物馆工作的示范材料以及一个供20个学生使用的教室。霍廷格首先开始对图书馆员、记者和博物馆管理者进行职业培训,因为他看到这些职业间很多相似之处和改变的机遇。但霍廷格的学生中无人进入博物馆工作。1905年,前女性学院被宣布改为女性图书馆员学校。学校在霍廷格1914年去世后关闭。
霍廷格的教材似乎是1915年在莱比锡成立的更为人所知的德国图书馆员与博物馆官员学校的完美模板。这个机构是作为德国书籍出版、书籍贸易与写作博物馆的一个部门成立的,而这个博物馆本身又是德国出版商与书商的私立组织的一部分。馆长阿尔伯特·施拉姆(Albert Schramm)设想了一个档案管理员、图书馆员和博物馆从业者的学校,但他缩减了计划。他创立了一个为期四个学期的夜校,包含讲座期内举办的一个从周一到周五或周六的每日讲座,每学期还组织一个远足周。施拉姆也把讲座作为深造的契机。
规划的课程让图书馆员和博物馆从业者都感兴趣,五位博物馆馆长、六位主任图书馆员和四位莱比锡大学教授充任教师。当时规划了三个博物馆领域的专门讲座:博物馆技术、“作为普遍教育机构的博物馆”和博物馆系统的历史。由于是夜校,其课程可以与图书馆或博物馆受训项目(无薪志愿制)和(或)莱比锡女性学院的补充讲座结合。
萨克森州当时组织对外招生考试,但仅就图书馆助理工作发布了考试条例。学校于1915年开始制定博物馆官员的考试条例,但详细流程的文件已经散佚。1917年,首批报考者是一位书商(唯一男性)、三位博物馆助理、一位艺术中心助理、两位博物馆或图书馆助理、两位图书馆秘书和三位其他女性;1918年,报考的是九位图书馆秘书(其中三位为男性)、三位图书馆助理和两位其他女性。莱比锡的这间学院并非只有女性,但女性占主导。
校长施拉姆和莱比锡应用艺术博物馆馆长共同在1918年德国博物馆协会第二届大会上介绍了这个学校方案,但并未提起与会者更多的兴趣。校名改成了德国图书馆员学校。而在此后几十年,职业培训或博物馆学理论的新想法就乏善可陈了。
冷战时期的联邦德国:无结果的博物馆学探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博物馆学这个词重新出现在重要讲座中。1971年,德国博协组织了一场名为“博物馆学”的讲座,并邀请法国博物馆馆长、国际博协顾问乔治·亨利·里维耶尔(Georges Henri Rivière)举办了一场讲座;德国博协主席赫尔曼·奥尔(Hermann Auer)以“博物馆学概念导论”开场却并未给出任何定义。1988年,奥地利博协、德国博协和瑞士博协联合组织了一场博物馆学会议。布尔诺大学(捷克斯洛伐克)的茨比内科•斯坦斯基(Zbyněk Stránský)是唯一把博物馆学看作独立学科的人。这些讲座未产生任何可见的效果。
1978年,由于要探讨在一所巴伐利亚大学建立博物馆学科的问题,巴伐利亚博物馆协会设立了一个“博物馆学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宣布,博物馆学仅可被认为是其他(与博物馆相关)学科的补充学科。他们提议成立一个独立机构,以拓展研究规划,这一机构应由资深博物馆从业者和大学教授构成。但此事却无下文了。1980年,法兰克福大学考古补充学科教授玛利亚·拉德诺蒂-阿勒佛尔蒂(MariaRadnóti-Alföldi)就博物馆学学习规划为黑森州制定了一份专家报告,但没有落实。她断然认为博物馆学不能成为独立学科,因为“只有某些基础知识和技术是置之四海而皆准的”。阿勒佛尔蒂的博物馆学仅把“抽象博物馆理论、博物馆历史但尤其是博物馆工作使用知识和经验”作为博物馆相关学科。
1971年,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一个重要的国家提供资金的研究资助组织,提到了一个“博物馆的危机”并呼吁成立一个重视参观者研究的“博物馆方法论中央跨学科研究院”。1980年,国立“博物馆学研究院”(Institut für Museumskunde)在西柏林成立,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所有联邦州提供资金。研究院起先既重视博物馆史,也重视搜集联邦共和国的博物馆统计数据。
冷战时期的民主德国:专门博物馆学与
“博物馆学家”的职业描述
1964年到196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办了首次有关博物馆学的讨论。此次讨论主要涉及实践层面,也颇受争议:正式承认博物馆是个科学领域,能够有利于文章出版或创办学术期刊,因为这样能减少国家审查系统的盘问并能确保纸张配额。中央政府仅仅在国立博物馆咨询机构设立了一个科学顾问委员会,作为象征性的回应。
茨比内科·斯坦斯基阐发的博物馆学理论的地位微不足道。1981年,一家国立研究院发表了其《博物馆学研究导论》(Úvod do studia muzeologie, 1979)的译本,但到了次年,颇具影响力的博物馆馆长克劳斯施莱纳(Klaus Schreiner)批判了斯坦斯基“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可疑的接近”。他指出,斯坦斯基的思想已经“传染”了很多东德博物馆学家。
1980年,东柏林大学同时也是东德最重要的自然史博物馆的所有者任命伊尔瑟·扬(Ilse Jahn)为自然史博物馆学讲师。1988年,东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与苏联合作伙伴共同推出了一本(历史)博物馆学手册。因此,中央集权的东德存在两种不同模式——自然博物馆学和历史博物馆学,其对学科结构和方法的部分看法相互矛盾,但并未开始进行任何论述。
这些人包括大型博物馆的助理和小型博物馆中的独立工作的从业者。因此,就需要第一份德国博物馆从业者的职业描述,以及一个正式的职称。文化部最初称之为“博物馆助理”,后来在1957年选择了“博物馆学家”。从一开始,博物馆学家学院的所有博物馆相关内容都由博物馆从业者和外部讲师讲授。1965年,学院将文化史讲师海因茨威克斯(Heinz Wecks)的职称更改了,于是有了第一位全职博物馆学讲师。1986年,博物馆学家学院的主导教师们提出了一个称为“历史博物馆学家”的新职业描述。直到1990年东德终结,这个想法都未实现。
统一德国的混合传统和新学习项目
在这一德国年表的末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项古老传统:博物馆志愿者制度已历百年但仍然存在且在继续扩张。众多种类的博物馆为毕业生提供超过400个两年期全职受训岗位。无薪的情况不复存在;薪资水平达到半薪程度。有关质量标准的讨论仍在继续;在某些地区设立了补充的学习要素(只有在柏林自由大学作为深造存在)。
仅有一家东德博物馆相关机构幸存到了统一以后:1992年,博物馆学家学院被改组为莱比锡应用技术大学的“博物馆学”学习项目(平行于两个图书馆员学院和“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习项目)。“博物馆学家”(museologe)职称变为了博物馆学家文凭。“博物馆学”的主要话题是博物馆文献整理和藏品管理。
“博物馆学”如今的学术规模很晚才出现,且与历史上的发展有别。37所大学运营着45个至少拥有一个与博物馆工作有关的学习单元的不同项目。类似“博物馆学”(5个)或遗产研究(同为5个)这样的完全的博物馆工作项目是少数,大部分项目涉及展览/策展(21个)或是艺术管理(8个)。称为博物馆学或“博物馆科学”的德国教席不超过四个,很多种类的大学为这个未知的整体贡献微薄之力。这45个项目的源头教学学科非常多样(共分析了135份简历):艺术史占主导地位(54人),之后是地位大大降低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和建筑(各13人),历史(6人)和各学科的双学位(5人)占据最末席。40%的艺术史家都与仅在德国博物馆中占10.6%的艺术博物馆无关。
另一边的视角也很有趣。对博物馆相关的博士论文的分析让人了解到其就业选项。1987年至2011年,德国国家书目包含148篇此类博士论文,通过网络能找到108份简历。多数人的工作去向是大学。(32名全职和1名半职人员,其中有13名教授)博物馆相关职业占第二位。(20名全职和1名半职人员,其他11人承担博物馆服务工作,例如作为自由职业者)6名学校教师证明,对博物馆教育的兴趣对其他教育也很有帮助。剩余的39人则从事非常多元的“其他工作”——一篇博士论文能够开启一段与研究话题有关的职业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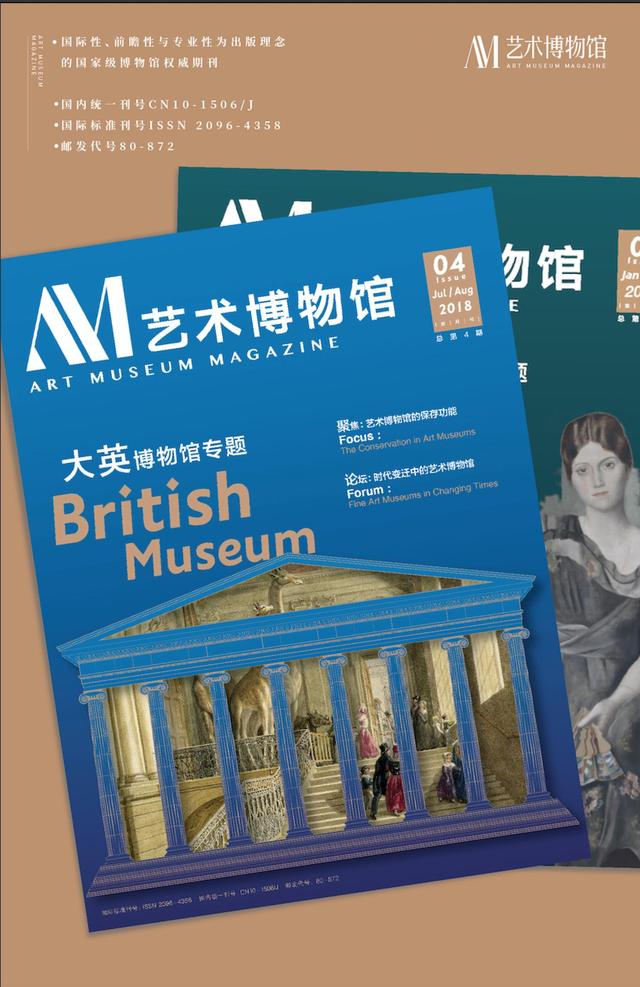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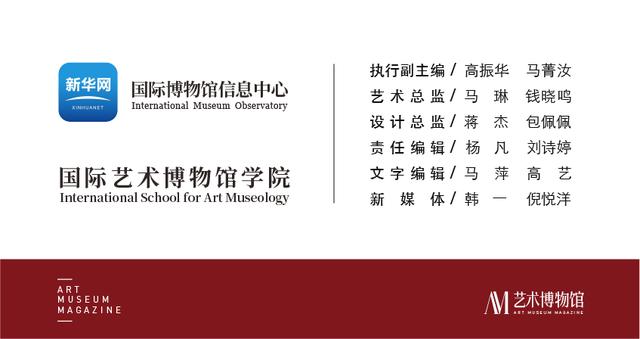
来源:新华号 《艺术博物馆》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