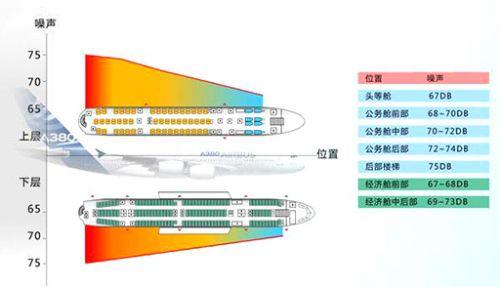看画哦诗重慨慷,百年翰墨付微茫。
已怜挥洒如摩诘,可忍悲歌似子昂?
名世几人称妙手,旧游随处搅愁肠。
云林故事惟文藻,遗迹偏多在远乡。
这是明初韩奕《奉次云林画上诗韵》对“斯世与斯人,邈矣不可攀”(亦韩奕句)的一代高士倪云林(1301—1374)的缅怀念想。今年是倪云林诞生720周年,不由想到“云林故事”及“遗迹偏多”与上海松江的甚深因缘。
在元代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以松江为枢纽的浙西(钱塘江以北、太湖以东、松江以南地区)是当时文化艺术的中心,尤以云间曹知白、昆山顾阿瑛、无锡倪云林以招徕四方文艺之士闻名天下。但曹、顾均为谦谦君子,彬彬长者,待人处世,既清操自守,又温柔敦厚。倪云林却年少轻狂,恃才傲物,尤多怪癖。在当时传得沸沸扬扬者有二,一是洁癖,每次洗脸、洗手,“易水数次”,院中树石,亦常洗拭。二是“避俗如恐浼”,“见俗士索钱,则置钱于远所,索者自取之,恐触其衣也”;“客非佳流,不得入”门庭。曾有外人(估计是中亚人)入关,闻其名而专诚来访,以沉香百斤为贽,云林明明在家,却命家人说是“适往惠山饮茶,明日再至”;至,“又辞以出探梅花”。其人徘徊数日,不去,乃密令开“云林堂”使登,“堂东设古玉器,西设古鼎彝尊罍,其人方惊顾间,问其家人曰:‘闻有清閟阁者,可一观否?’家人曰:‘此阁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入也。’”其人望阁再拜而去,终不得一面。云林之不近人情如此!

倪瓒《虞山林壑图》
不仅对“俗客”极尽歧视,就是对同为高雅而名声与其相埒者他也不无傲慢。1342年题曹知白《溪山无尽图》卷:
吴淞江水碧于蓝,怪石乔柯在渚南。
鼓舵长吟采萍去,新晴风日更清酣。
松瀑飞来到枕边,道人清坐不须弦。
曹君笔力能扛鼎,用意何止让郑虔。
脉脉远山螺翠横,盈盈秋水眼波明。
西北风帆江路水,片云不度若为情。
至正二年春三月,偶过廉夫杨君斋头,得观曹贞素卷,别有会心,爰题三绝于左方。时扁舟欲西,因草草也。
“廉夫杨君”为杨维桢,“曹贞素”即曹知白。曹知白的“玉照堂”与顾阿瑛的“玉山草堂”、倪云林的“云林堂”,当时并称浙西的三大风雅渊薮,且曹氏长其整整三十岁,算得上是他的长辈。但题诗不称“曹公”而称“曹君”,跋语更直呼“曹贞素”,其迂傲的个性可见!是否他真的不懂长幼之序的礼仪呢?并不是的,就在上一年他题黄公望《霅山图》:
霅上溪山也自佳,黄翁摹写慰幽怀。若为剩载乌程酒,直到云林叩野斋。倪瓒题大痴翁写《霅山图》以赠山甫卢君,至正元年十月四日。
黄公望年纪与曹知白相当,止大曹2岁,而其当时的社会地位远逊于曹。倪云林对之一口一个“黄翁”、“大痴翁”,两相比较,他对曹知白的态度,正如法坤宏的评价郑板桥:“惟不与有钱人面作计。”可见倪云林除“避俗”之外,还有一个怪癖“嫉名”,亦即“文人相轻”。这样的性格,在待人处世中肯定引起不少人的不爽,如杜甫的论李白“众人皆曰杀”。用《颜氏家训》之所诫,则所谓:“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人们之所以容忍他们,不忍“捶楚”他们,甚至还把他们捧得很高,实在是因为爱才而护短,而绝不是肯定他们的怪癖为高标。
当然,在倪云林还因为有一个厉害的哥哥。
倪云林兄弟三人,二哥子瑛弱智,不论。大哥文光则是道教中的重要角色,又善治生产,上至朝廷官府,下至地方百姓,不仅人脉广,而且人缘好。倪家的万贯家产以及社会特权,都是靠文光打拼得来的,为云林呼朋引类、诗酒书画的风流文采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1328年秋,文光突然病逝,云林却只知挥霍,不事生产,不过20年的时间,兄长留下的家财渐为耗尽,人脉的余荫也不复留存,终于1350年前后宣告破产,流落江湖以乞食为生。其中到得最多的地方,便是松江和吴江,即《明史》等多种文献所载的“扁舟箬笠,往来震泽、三泖间”。事实上,倪云林在最后的20年里,到过的地方有宜兴、常州、太仓、昆山、吴江、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多处,但是,为什么众多文献不约而同地单取吴江、松江两地呢?我想,吴江是因为他呆的时间最久,而松江则于他文化上的意义更大。
吴江与无锡相近,在倪家巨富时,得到其照顾的人家应该是不少的。云林有子二,长孟羽,早卒;次季民,应该仍生活在这一带;女三,长适徐瑗,次适陆颐,幼适母舅蒋氏子,亦皆生活在附近。亲友既夥,则投桃报李,落魄后找上他们,也可以说是人情相抵。但松江的朋友,当年的倪云林显然是不太看在眼里的,这从前引倪题曹知白画诗便可见出。而现在,松江的朋友们竟然仍然对他若无前事地以礼相待,这对他的触动实在是极其震撼的。
众所周知,倪云林的传世作品,在清閟阁中时所作者甚少,绝大多数都是破散家财流落江湖后所作,这就是“遗迹偏多在远乡”,且以在松江者为尤夥。

上海博物馆藏其《竹石霜柯图》(上图),疏笔渴墨,极秋意之萧瑟淡泊,似园林的一隅,又似江渚的边角。画面自题:“十一月一日灯下戏写竹石霜柯并题五言:久客令人厌,为生只自怜。每书空咄咄,聊偃腹便便。野竹寒烟外,霜柯夕照边。五湖风月迥,好在转渔船。云林子。”应该便是在松江所作,只是不知具体的年份。因为上方另有钱惟善、杨维桢的题诗,而钱、杨正是长期寓居松江的两位大名家,又是倪云林的好友。钱惟善的题诗:
去年溪上泊轻舟,笑弄沧波狎海沤。
云去楼空无此客,寒林留得数竿秋。
是回忆与倪云林同游松江小金山(今属金山区)入海口时的高兴不可一世,眼空四海而目中无人,如今却脱胎换骨般地变成了似乎是另一个人。变成了怎样一个人呢?再来看杨维桢的题诗:
懒瓒先生懒下楼,先生避俗避如仇。
自言写此三株树,清閟斋中笔已投。
是说当年的倪云林可是清高得很,对俗人简直就像对仇人一样,严划界线绝不亲近!而现在,终于放下了清閟阁中的架子,入乡随俗了。

倪瓒《丛篁古木图》
而倪诗自述的“久客令人厌,为生只自怜”,也正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当年的讨厌别人,实在是很不应该的;倒是如今的自己,老是赖在朋友家里打秋风,吃白食,不会引起别人的讨厌吧?所以,为了回报朋友的招待,从此便“投”下了清閟阁中的绝俗之笔,不再鄙夷他人,而是提起了另一枝从俗之笔,恭维他人。从此,倪高士的形象也就不再是“令人厌”的敬而远之,而是令人亲的“大众情人”,一时江南人家,竟以有无倪画为清浊。
不过,他的这一洗心革面也引起了别人的不满。同样也是流寓松江的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提到,有一位陈云峤,时在杭州,以清高名世,云林慕其名来见之,张宴湖山间,罗设甚至,酒终为别,云林以一帖为谢,云峤馈米百石,命从者移置近所,举巨觥,引妓乐、驺从,悉分散之,斥倪云:“吾在京时,即熟尔名,云南士之清者,它无与比,其所以章章者,以米沽之也。请从今日绝交。”且骂诸曾誉之者。时张伯雨亦在坐,不胜跼蹐。谢稚柳先生当年给我讲起这个故事,对比以当年清閟阁中的避俗如仇,认为是“角色反转”,并戏和杨维桢诗:
谀辞诗笔信堪投,高士何时懒下楼。
宴罢殷勤重餽米,当筵真见俗成仇。
回过头来看这张《竹石霜柯图》,长期以来并未为美术史和倪云林的研究者所特别地关注。但是,从作品中所包涵的倪瓒、杨维桢、钱惟善三人关于倪氏人生和艺术思想转换的对话,我称之为“松江对”,则是任何一幅倪画所无法取代的。

倪瓒《筠石乔柯图》
倪迂画为元人逸品第一,然世以避俗如仇视之则非。盖避俗如仇,清閟阁中懒下楼时事也。至破产散家,乞食江湖,久客人厌,为生自怜,于是到处应酬,遗迹偏多,“清閟斋中笔已投(扔弃)”而“谀辞诗笔信堪投(回报)”矣。山谷道人论不俗有二,平居无异俗人,此不俗人也;平居大异俗人,此真俗人也。大异俗人者,清閟阁中之云林也;无异俗人者,三泖水畔之云林也。故观倪画,宜以从俗处见其不俗,方得逸品之致;避俗观之者,去逸品转远。
这是我拟云林笔意时常用的一段题跋,也是我对“云林故事”和“遗迹偏多”中“松江对”的见人所未见。当然,这一认识的来源是谢老。1991年,无锡市文联编《倪瓒画集》,请谢老撰序,谢老命我代笔。文章完成之后,谢老亲自在结尾处加了一句:“明清之际学他画风的人不少,但却没有一个能得到他的精髓。”这个“精髓”,正是指其“从俗”的“不俗”。
作者:徐建融
编辑:吴东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