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财产?财产又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形塑作用?财产权的边界该如何界定?美国法律史学家斯图尔特·班纳在其新作《财产故事》中,借由美国故事的叙述,向我们呈现了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本书收于田雷主编的雅理译丛中。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现与读者朋友们分享部分章节。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声音是转瞬即逝的。一旦被生产出来,它就无法被存储或复制,而是永远地消失了。销售声音的唯一方式是现场表演,已有的财产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欣赏声音的权利可以以演奏厅门票的形式被售卖。而这一点随着19世纪末录音技术的发明而被改变。当声音可以被储存时,它可以以新的方式被销售。此时,建立一套对声音的财产权制度就变得有利可图了。但这些财产权利应该归属于谁?财产权的边界在何处?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技术变革的收益将如何分配。
固化形式的音乐
19世纪的作曲家通过销售活页乐谱取得版税收入。19世纪50年代早期,斯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销售了超过13万份《故乡的亲人》(Old Folks at Home)的乐谱。《沃巴什河畔》(On the Banks of the Wabash)是作曲家保罗•德莱塞(Paul Dresser)在19世纪90年代的巅峰之作[这首歌的歌词由其弟弟——小说家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所作],这首歌的乐谱卖了超过50万份。当然,很少有歌曲如此流行,但是,如果作曲能够获得收入,那么,收入主要来自于出版活页乐谱。
音乐出版产业的法律基础是著作权法,该法禁止对音乐作品的复制。美国早期的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保护音乐作品,因此音乐作品通常以书籍、表格或雕刻的形式受到著作权法保护。1831年法将音乐作品作为一种可以受著作权保护的独立作品类型加以规定。然而,即便在此时,作曲家也仅仅可以阻止他人对活页乐谱进行复制,不能阻止对音乐作品本身的表演。只要购买了印刷乐谱,音乐家就可以在演奏厅里自由地演奏音乐,无须经过作曲家的同意,也无须与作曲家分享收益。

斯蒂芬•福斯特
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偶尔有关于著作权法是否应当修改,以赋予作曲家公开表演权的争论。剧作家在1856年获得这一权利。在此之前,剧作家和作曲家处境相当:他们可以阻止对剧本的复制,而剧本一经出售,获得所有售票收入的则是剧院经理和演员们。一位社论家在法律即将修订时抱怨道:“如果莎士比亚是美国人,那他生产纽扣会比写作戏剧更有利可图,除非他变成一名经理,让自己的脑袋停止思考,依赖他人的头脑营生。”但1856年的著作权法修正案,并没有为作曲家提供类似的权利,原因很可能是戏剧产业与音乐产业的经济模式不同。剧作家从来都不可能销售成百上千份剧本。如果戏剧能够带来收益,这一收益必然来自表演。
剧作家和他们的出版商们有充足的理由推动法律的变革。相反,19世纪的音乐产业中,利润主要来自于活页乐谱的销售,而在大批观众面前表演音乐作品,恰恰是活页乐谱最佳的促销方式。一位观察家指出:“总的来说,作曲家和出版商都乐见其音乐作品被演奏,如此,对音乐作品的需求就被激发出来,他们也将售出更多的复制件。”音乐出版商还担心,如果购买活页乐谱时不包括表演的权利,那么顾客将不愿意购买活页乐谱。辛辛那提市一家音乐杂志的编辑论证道:“如果人们必须为一首歌曲付两次费用,一次是为了购得其印刷复制件,另一次是为了获得演唱它的许可,那么,这首歌曲的流行度和销售量肯定比不上那些人们可以自由而免费地演唱的歌曲。” 基于这一考虑,国会在1897年之前都未将公开表演权延及音乐作品,而1897年的法案之所以保护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主要是为了保护歌剧、音乐剧中作曲家们的权利。
此时,音乐产业已经到了剧烈变革的转折点。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已于1877年制造了第一台留声机。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有相互竞争的留声机公司销售着录有音乐的圆筒(cylinders)和碟片(disks)。唱片的销量急剧上升,从1897年的50万份上升到两年后的280万份。与此同时,发明家尝试将键盘音乐固定在穿孔纸带上,结果制造出自动演奏钢琴(player piano),这一产品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进入市场。消费者再也不用自己演奏乐器来享受钢琴音乐;他们可以直接购买钢琴卷(piano rolls),将之插入自动演奏钢琴中。1900年到1930年之间,几百万台自动演奏钢琴被销售出去。它们如此的流行,以至于有人担忧,“几年内,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在家中进行的钢琴演奏将成为一项失传的艺术”。声音曾经是转瞬即逝的,但现在它却变成可以销售的商品。

爱迪生与滚筒留声机
声音因此可以成为财产,但是,它应当属于谁?音乐出版商及他们代表的作曲家们认为,声音应当是属于他们的。纽约律师保罗•富勒(Paul Fuller)——音乐出版商协会(the Music Publisher.s Association)是他的客户之一——论证道:“如果有人将我的音乐镌刻在活页乐谱上并将之销售,他是一个仿冒者,我可以从他那里获得赔偿并惩罚他。如果他做的事情更为严重——他通过复制作曲家脑海中的声音本身来完成这一仿造”,那么他销售录音的行为是“盗版的终极形式”。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观点。音乐盒自18世纪晚期就已经出现。有些音乐盒演奏着流行的音乐,但没有人会认为它们侵犯了作曲家的著作权。有人指出,如果自动演奏钢琴和留声机只是复杂版的音乐盒,那么很难看出为什么著作权法要对它们区别对待。其他人则注意到著作权法仅仅禁止制作复制件。根据词语的一般含义,一个蜡筒(wax cylinder)或者一个穿孔纸带卷并不是活页乐谱的“复制件”,所以,如果严格地解释著作权法的文本,录制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活页乐谱上的音乐作品,并没有违反法律。毫不奇怪,唱片和钢琴卷制作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他们在录制歌曲前并未取得作曲家们的同意,在获得利润后也不与作曲家分享。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一问题三次出现在美国的法庭上。作曲家在每次交锋中都落败了。第一个案件是针对发明家约翰•麦克坦慕尼(John McTammany)的诉讼,1881年,他获得了一项自动演奏钢琴的前代技术的专利。麦克坦慕尼发明了一种制作音乐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使穿孔的纸卷经过一种叫作便携式手风琴(organette)的乐器,便携式手风琴是一种带有小手杆、无键盘,能将空气抽进簧片的乐器。麦克坦慕尼的纸卷中有一款播放的是19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的歌曲——《摇篮空空,婴儿走了》。
1887年,这首歌的曲作者哈里•肯尼迪(Harry Kennedy)在波士顿提起诉讼,但法官毫不犹豫地驳回起诉。法官解释道:“我无法说服自己,在著作权法的意义上,这些穿孔的纸卷是活页乐谱的复制件。它们不是制造出来给肉眼看的乐谱,而是机器的一个部分……它们的用途更接近于手摇风琴或音乐盒的金属管。”若干年后,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法院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原告是约瑟夫•斯坦恩(Joseph Stern),他享有19世纪80年代两首歌曲——《拿回你的金子》(Take Back Your Gold)和《轻声呼唤母亲的名字》(Whisper Your Mother’s Name)——的著作权。被告是乔治•罗西(George Rosey),他为留声机制作蜡筒。法院再一次将问题表述为“蜡筒是不是活页乐谱的复制件? ”而后再一次得出否定的结论。法院判决道:“这些事先准备好的蜡筒既不能替代受著作权保护的活页乐谱,也不能实现在活页乐谱范围内的任何目的。在这些方面,蜡筒和更古老、更为人们熟悉的音乐盒中的金属圆柱体,并没有实质区别。”
第三个案件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在怀特史密斯音乐出版公司诉阿波罗公司(White-Smith Music Publishing Company v Apollo Company)案中,最高法院一致判决:钢琴卷不是活页乐谱的复制件,因此生产自动演奏钢琴及钢琴卷的阿波罗公司,没有侵犯怀特史密斯公司的著作权。威廉•戴伊大法官(William Day)宣称:“从广义上讲,再现旋律的机械乐器复制了音乐作品,这也许是对的。但是,这是一个勉强的、人为的含义。按照通常对‘复制件’的理解,不可能认为通过听觉触及我们的音乐是复制件。”著作权法不禁止钢琴卷的制造或制作他人音乐的录音制品。在同意意见中,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敦促国会修改法律。他论证道:“音乐作品是声音的有序排列,原则上讲,任何机械地再现这一排列的事物都应当被认为是复制件。”但是,该案仍没有如此判决。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判决对作曲家是不公的。《纽约时报》的社论称:“很显然,音乐作曲家可能或者已经被抢夺了财产权,这种财产权至少与其他类型的财产权一样有效,他被剥夺了本该对他最有利的市场。”这些判决引发了修改法律的呼声。《美国律师》(American Lawyer)杂志宣称:“如果著作权法真的没有为目前这类案件提供保护(在这些案件中明显存在完全复制的盗版行为),那么这样的法律越早修改越好。”随着钢琴卷和录音制品市场的成长,在19世纪80年代经济上不显著的问题,到了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却变得对音乐产业意义重大。于是,在1906年到1909年之间,这一问题反复在国会中争论:谁应当享有对声音的所有权?
其中一方的明星证人是那一时代最著名的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萨(John Philip Sousa)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将著作权法扩大到禁止他人录制其乐曲作品。他在1906年时坚称:“我和每一位受欢迎的作曲家都是侵权行为的受害者,它们严重侵犯了我们的精神权利。本年度最受欢迎的华尔兹或进行曲的作曲家必然发现,他的作品被攫取,被任意复制在蜡筒、铜碟或者穿孔纸卷上,被无限地复制,并在全国范围内以巨额利润销售,却没人为使用该作曲家大脑中的原创产品向他支付一分钱的报酬。”苏萨花了好几个小时,向国会委员会汇报他因未能从作品中获酬而遭受的损失。他回忆道:“去年和前年夏天,我去了世界上最大的游艇港口之一。每一艘游艇上都有一台唱片机(gramophone)、一台留声机、一台伊奥利恩(aeolian,自动演奏钢琴的一个品牌),或者其他同类设备。它们都在播放苏萨进行曲,从艺术的角度看,这是没问题的[此处委员们笑了],但是他们却没有为之付费。”苏萨坚持认为,他的歌曲应该是属于他的,“我希望他人为使用我的财产而付费”。
在华盛顿,维克特•赫伯特(Victor Herbert)加入了苏萨的行列,赫伯特创作的作品类型丰富,其受欢迎的程度在当时达到了顶峰。赫伯特作证道:“他们正在复制我们大脑的一部分,在复制我们的才华。对每一张唱片,他们付给卡鲁索先生(Mr Caruso)每首歌3000美元。他唱的可能是苏萨先生的歌,也可能是我的歌,但作曲家却收不到一分钱。我说,这不可能是公平的。” 雷金纳德•德•科文(Reginald de Koven)在过去二十年间创作了不少成功的喜剧歌剧作品,他声称,他从伊奥利恩自动演奏钢琴公司的职员那里得知,伊奥利恩仅仅在一年里,就销售了价值12.5万美元的载有其音乐作品的钢琴卷。德•科文估算,如果能够获得许可费,他大概可以赚得约两万美元。他质问道:“人们购买钢琴卷难道是将这个纸卷看成工艺品,或者把它裱起来挂在墙上吗?不是的,先生们,人们是为了欣赏音乐——请把接下来几个字加着重号,是‘为了听音乐’——而他们确实听到音乐了,这个音乐是作曲家们的财产。”商业上最成功的作曲家和他们的出版商,正是可以从著作权法改革中获得最多收益的人群。

阿图尔·鲁宾斯坦Artur·Rubinstein(1887-1983) 美籍波兰钢琴家
他们也担忧,如果法律不改革,他们的损失将最惨重。如果顾客购买唱片或钢琴卷,而不购买活页乐谱,那么作曲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将枯竭。维克特•赫伯特主张:唱片“和活页乐谱服务于相同目的。这些设备销量的增长必然导致活页乐谱销量的相应下降”。作曲家阿瑟•潘恩(Arthur Penn)担心“人们如今只购买唱片、碟片和纸卷,不购买活页乐谱。所以我损失惨重”。作曲家和出版商最糟糕的担忧被一位快乐的音乐爱好者所印证,他告诉《纽约时报》,他是多么享受留声机和自动演奏钢琴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他坦言:“在这两者出现之前,我可以称得上是活页乐谱的长期购买者——实际上可以说是活页乐谱狂人,但随着纸卷和再现声音的唱片的改进,如果我想要一个新的音乐作品,我要么购买一个纸卷……要么更经常地是购买一张碟片。”他知道很多人跟他一样,“过去习惯于购买活页乐谱的人,现在都转而购买固化形式的音乐”。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指出,如果新技术削减了活页乐谱的销量,这正是授予他们权利,从而从录制声音(recorded sound)中获利的又一个理由。
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与美国著作权联盟(American Copyright League,一个书籍和杂志出版商的组织)之间是强大的同盟关系。著作权联盟的主要兴趣在于加强对作者的著作权保护(由此也将增加出版商的收入),但联盟还看到了当时仍未浮出水面的一项收入来源。如果作曲家无法获得控制唱片的权利,那么书籍作者也无法获得,尽管当时对作者没有损失,但谁也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的编辑和出版商理查德•罗杰斯•包克(Richard Rogers Bowker)解释道:“有一天,对作品的有声复制可能变成像音乐唱片一样重要的产业,这一产业将像影响活页乐谱生产一样,影响纸质书籍的生产。” 包克注意到,“录制音乐”已经是一个大产业,那么“录制讲座和录制书籍的朗读也可能随之出现”。因此,著作权联盟向国会游说,争取承认作曲家的权利。著作权联盟在写给国会议员的信件中指出:“在摄影技术发明之后,国会及时立法将照片复制件作为著作权的保护对象。国会似乎应当像对待摄影作品那样,特别将音乐作品的机械复制件纳入到著作权保护的范围。”
辩论的另一方是正在迅速成长的自动演奏钢琴、钢琴卷、留声机和留声机唱片生产商——批评者将他们称为“机械音乐盗版者”(“the mechanical music pirates”)。他们主张,著作权法的改革将使这一新兴产业在方兴未艾之时就惨遭毁灭。维克•托金机器公司(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的律师作证道,在经过仔细考察,认定销售可在其设备上播放的唱片不构成著作权侵权后,该公司已为其厂房和专利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他争论道,在公司已经做了这么多不可逆转的投资后改变游戏规则,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自动大钢琴公司(Automatic Grand Piano Company)总裁质问道,如果音乐卷的供应危在旦夕,谁还愿意继续生产自动演奏钢琴?
这些反对授予作曲家声音所有权的人们是受到自我利益驱使的,正如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一样。但是,一如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他们也精明地将他们的论点改造得符合大众的公平观念。他们预测道,唱片和钢琴卷不会削减活页乐谱的销量。相反,唱片作为一种免费的广告,可以促进活页乐谱的销售。唱片公司指出,事实上,活页乐谱产业从未如此景气过。1890年到1905年之间,活页乐谱的销量翻了近三番,如果作曲家的悲观预测有任何基础,那么这几年应该恰好是活页乐谱销量骤降的时期。一位评论者解释道,有人担心人们会抛弃他们的乐器,投奔录制音乐,但“在我看来,结果恰恰是相反的”。
能够欣赏到杰出的演出,反而会激励业余音乐家更多地进行练习。这位评论者预测道:“对于真正有音乐天赋和能力的人,大量好音乐的出现将变成一种激励。”事实上,许多新唱片公司注意到,它们被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寄来的活页乐谱淹没,这些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乞求唱片公司将他们的音乐作品录制成唱片,不求补偿,仅仅希望听众因此会出去购买他们的活页乐谱。唱片公司的代表告诉国会,约翰•菲利普•苏萨和维克特•赫伯特也许不需要广告,但美国大部分作曲家和出版商“都乐于获得其音乐机械复制的广告效果。在行业中,它被认为是促进音乐作品销售的最有效的广告形式”。音乐产业正在转变中。从长远来讲,录制音乐到底将促进还是取代活页乐谱,这还是不清楚的。最成功的作曲家的经济利益,与那些较不出名的作曲家的经济利益并不相同。
允许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收取许可费,可能使唱片和钢琴卷变得更加昂贵,这提供了又一个反对法律改革的理由。纽约钢琴交易商的商业期刊《音乐时代》(Musical Age)指出:“对人们的欢愉征税,这不是符合现代精神的做法。这些许可费将从人民手中获取,并流入少数人手中。”音乐富有教育意义,它使流行感知变得更有教养。“限制廉价音乐的生产将妨碍这一工作,这是一种倒退。”在纽约出版商爱德华•舒伯特(Edward Schuberth)看来,这是反著作权理由中对国会议员影响最大的一条,国会议员们“经常担忧因抬高娱乐的成本而受到选民们的批评”。扩大著作权的保护是需要成本的,要接受这一点,人们不需要走得像《音乐时代》那么远,它相信“所有音乐都应当如鸟啼声和微风拂过树叶的低吟声那样,是免费的”。录制音乐可能变得更昂贵,产量也可能减少。评论者指责道,如果著作权法的目的在于鼓励创造性作品的生产,那么作曲家要求的正是一项反生产性的改革,这一改革对他们自己有利,却以听众们的利益为代价。
而且,为什么法律要给予作曲家特殊关照?唱片产业迅速指出,作曲家并不是录制音乐的唯一创造者。从印刷的音符到唱片之间有很多步骤,每一步都需要同样多的才华与艰苦工作,每一步对于最终产品而言都至关重要。美国留声机公司(American Graphophone Company)的律师主张:“我用苏萨先生的乐谱,然后我选择某个人——在这群观众中可以称得上音乐家的某个人——我把留声机交给他,让他制作一张唱片。这个唱片在市场上很可能是一文不值的!为了制作一张有市场价值的好唱片,需要有苏萨般的天才来对着喇叭演奏,需要优秀歌唱家的嗓子对着喇叭演唱,还需要操作留声机的机械师的技巧。”作曲家只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员。而且,为什么仅仅考虑以上人员?为什么不把留声机的发明人包括进来?不把生产者包括进来?还有为钢琴卷穿孔的熟练技术工人? 如果在制作过程中必不可少就足以使之成为声音的拥有者,那么有许多主张权利的人似乎也有资格成为所有权人。
作为最后的一招,唱片产业求助于《宪法》。《宪法》授权国会制定著作权法,授予“作者”对其“(书写)作品”(“writings”)的排他性权利。产业代表们主张,钢琴卷和唱片显然不是“(书写)作品”,所以国会无权创造对它们的财产权。爱迪生留声机公司(Edison Phonograph Works)的弗兰克•戴尔(Frank Dyer)宣称:“留声机唱片不是(书写)作品,因为它是不可阅读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精密性和极大的复杂性”,也因为其可变化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播放一首曲子的留声机唱片,第二天在留声机上也播放相同的曲子,但两块唱片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戴尔坚持说:“(书写)作品”意味着可视性和一致性。由于无人可以通过查看留声机唱片,就推测出当它被放在留声机上会播放出何种音乐,所以唱片绝对不是“(书写)作品”。戴尔问道,如果可视性不是必备条件,那么国会的权力将止于何处?一缕怡人的气味能否受著作权保护?一个从未被写下来的思想能否受著作权保护?“(书写)作品”这个概念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否则任何东西都能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但这并不是最有力的论点,甚至其支持者也非常清楚,因为它与一个世纪来的实践不相符。图表和地图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写)作品”,但它们在1790年第一届国会就被授予著作权保护。随后,著作权保护延伸到版画、雕刻,而后又延伸到照片,这些都显然不是“(书写)作品”。在国会将著作权扩大到包括公开表演权(先是1856年戏剧作品获得这一权利,后是1897年音乐作品获得这一权利),而没有受到以宪法为依据的任何反对之后,人们很难再辩称“(书写)作品”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书写作品。代表约翰•菲利普•苏萨和维克特•赫伯特的纽约律师南森•布坎(Nathan Burkan)总结道:“法律或宪法中并未要求一个对象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是,它是可以被阅读的。唯一的标准是,它是否承载着一个智力产品?”根据这一定义,《宪法》允许对声音的著作权保护。
几乎所有留声机和自动演奏钢琴公司,都反对将法律修改得对作曲家有利,唯独一家公司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惹人注意。纽约的伊奥利恩公司是一家最大的、最成功的自动演奏钢琴生产商。在其巅峰时期,伊奥利恩及其下属公司在美国、英格兰和德国的钢琴工厂雇用了5000名员工。如果人们期待由一家公司来领导这场战役,反对导致钢琴卷提价的议案,这家公司必定是伊奥利恩。然而,在国会三年来陆续进行的听证会中,伊奥利恩公司始终未发一语。
原来,伊奥利恩公司静悄悄地准备将它的竞争对手逐出产业。该公司与大部分主要的音乐出版商签订协议,以钢琴卷销售的许可费换取生产钢琴卷的独占权利。只有当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延及钢琴卷时,这些合同才生效;而如果这一情况出现,伊奥利恩将非常接近于一个垄断组织。因此,与唱片产业相比,该公司的动机与音乐出版商更加一致。事实上,人们从听证会上得知,伊奥利恩资助了1908年最高法院审理的怀特史密斯案,努力促使最高法院宣布钢琴卷侵犯音乐作品的著作权。聘请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律师查尔斯•伊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来代理怀特史密斯公司的,恰恰是伊奥利恩公司,而不是怀特史密斯音乐出版公司。(休斯后来将成为纽约州州长、国务卿以及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伊奥利恩公司成为垄断组织这一前景成为了反对修改法律的另一个理由。约翰•奥康纳(John O’Connell)代表美国全国钢琴生产者协会警告道:“你们正在扶持一个强大的集中势力。”协会的150个成员担心,一旦伊奥利恩公司控制大部分版权音乐,它们将濒临破产。“数百万美元将进入伊奥利恩及其子公司的保险柜。而最终的结果是公众必须为此付费。”
在所有反对修改法律的理由中,这是收到广泛反响的唯一一个。作曲家应当从其作品的录音制品中获利,这一点很多人在直觉上感觉是公平的,因此,留声机和自动演奏钢琴公司很难再继续免费使用那些作品。这一点甩了盗版者狠狠一巴掌,使之无法长期存在。但是,允许一家公司垄断正在成长的钢琴卷市场,这看起来一样糟糕。陷于这两个不太美好的结局之间,国会除了多召开几场听证会外,几年内什么事情都没做。
这一僵局最终被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查尔斯•华氏本恩(Charles Washburn)协调的一个折中方案打破。1909年的《著作权法》授予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禁止他人制作录音制品的权利,而一旦他许可了一个唱片的制作,其他任何人只要向著作权人支付每一复制件2美分的许可费就可以制作唱片。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因此从留声机唱片和钢琴卷的收入中获得了一定的份额,但这个份额不如他们能够自由议价时那么高,至少对最知名的作曲家是如此。伊奥利恩公司运作已久的垄断局面被阻止了。唱片产业继续成长。作曲家获得了生成声音的权利,但他们只能按照法定价格销售这一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价格显得越来越低。
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一强制许可是个好主意。《世纪》(Century)杂志的社论宣称:“这就好比说,除非克莱门斯先生(Mr. Clemens)将他给予哈珀兄弟公司(Messrs. Harper & Bros.)的权利也卖给其他所有出版商,否则他不能获得著作权保护。这是政府父爱主义原则发展到荒唐的地步。”事实上,如果国会尝试在其他产业中通过立法定价,必然招致一大片反对声。在解释对议案的反对意见时,威斯康星州众议员亨利•库珀(Henry Cooper)质问道:“农民希望法律为他能从一蒲式耳小麦中获得多少收入确定价格吗?发明缝纫机的人会希望法律为其行使权利定价吗?” 但是,总体的感觉是,对于一端是盗版行为、另一端则是垄断的局面,强制许可是唯一可行的替代性方案。
一个世纪后,强制许可仍然是美国著作权法的一部分,但如果伊奥利恩公司当初没有企图垄断钢琴卷的销售,这一规定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制定出来。许可费价格本该由作曲家(由音乐出版商代表)和唱片公司之间协商确定。最成功的作曲家本来可以获得高于法定许可费的收入,而不那么成功的作曲家们可能还得央求着唱片公司录制他们的作品,不敢要求任何费用。这个故事的更大启示是随机事件在分配科技变革所带来的收益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早期阶段,作为一个阶层的作曲家,能否从唱片产业中获利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使结论日渐清晰(即他们可以从中获利),他们应该获取多大的收益,在从以苏萨、赫伯特为一端到以无数不知名者为另一端的光谱间,这些收益该如何分配,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微小的决策带来了巨大的后果。
表演的财产权
1909年《著作权法》为作曲家提供保护,他人未经许可不得制作作曲家音乐作品的唱片,但它是否保护任何人——不论他是作曲家、表演者还是唱片公司——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唱片呢?换言之,当声音被录制后,有谁对其享有所有权?还是说,已经录制的声音就此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复制?
这一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因为到1909年时已经有非法翻录唱片(bootleg recordings)的灰色产业存在。例如,在纽约,大陆唱片公司(Continental Record Company)购买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唱片并制作复制件,该公司通过对买来的碟片进行反向工程,制作金属模具,然后用该模具压制复制件。除其他业务外,皇家音乐卷公司(Royal Music Roll Company)也发现了一种复制成功的钢琴卷的方法。由于不须向音乐家支付费用,这类复制者可以以低于原创唱片的价格销售其产品。导致1909年《著作权法》制定的争论还未尘埃落定,唱片产业就又面临新的问题。
在涉及这一问题的早期案件中,法院未经过多考虑就认定复制录音制品是违背新著作权法的行为。因此,1909年一位法官宣称,唱片公司应当注意申请著作权保护,不仅仅为印刷的音乐作品,而且要通过申请对“保存有音乐作品表演的碟片”的著作权而为“歌曲的原创表演”提供保护。若干年后,另一位法官赞同:新著作权法保护钢琴卷生产者的权利,如同保护作曲家的权利一样确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律师们开始发现,这一立场——用一位法学教授委婉的表达——“有点难以理解”。1909年《著作权法》没有任何关于录音制品是否可受著作权保护的规定。
实际上,国会拒绝了特别为录音制品提供著作权保护的许多项提案,而成为《著作权法》议案的最终版委员会报告,明确否认有任何将著作权保护延伸到录音制品的意图。因此版权局拒绝接受录音制品的著作权登记。几年之内,法院不再认为翻录唱片是违反著作权法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识是,录音制品不能受著作权保护。
录音制品无法受著作权保护,于是唱片业转向一个不同的策略。在新著作权法颁布前几年的一个案件中,法院判决复制碟片的人必须为普通法上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复制者不仅复制由维克特•托金机器公司生产的碟片[包括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歌手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的碟片],而且还通过在碟片上添加相同颜色的标签,甚至在标签上加入维克特公司的分类号,试图将其碟片伪装成维克特公司的产品。法院判决道,不论复制碟片是否非法,通过将产品虚假陈述为他人生产的产品,仿冒产品、欺骗公众的行为显然是非法的。
随后的案件中,在不存在仿冒要件的情况下,法院也认定存在不正当竞争。大陆唱片公司也复制了维克特公司的碟片,但大陆公司并未试图让公众相信其碟片是由维克特公司生产的。大陆公司用了与维克特公司不同的标签,并在广告中明确表示其销售的是维克特碟片的复制件,而非原创碟片。尽管如此,1909年,法院还是判决大陆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它利用了维克特公司在唱片上所做的投资,正如投机交易所利用了证券交易所维护的自动收报服务。如果所有竞争者都可以轻易复制和销售唱片的复制件,那么将没有人会为录制卡鲁索的作品付费。法院判决道:“通过优质音乐的传播教育公众,这是一个值得保护的目标。如果原创唱片的生产被阻止,这一结果显然很难实现。而不须支付获取原始唱片的费用就能生产音碟的人,对产品和收益的非法窃取恰恰阻止了原创唱片的生产。” 复制录音制品,即使没有任何欺骗公众的企图,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当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于1915年开始运作时,它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制止不正当竞争。联邦贸易委员会很快就确认翻录唱片属于其管辖范围。该机构在1916年出版的一份备忘录中宣称:“一种特别微妙的竞争形式,就是占用由其竞争对手投入成本而创造的价值。” 一个例子就是“利用其他公司的商业唱片制作留声机唱片”。因此,联邦贸易委员会命令东方音乐卷公司(Orient Music Roll Company)停止复制其竞争对手生产的音乐卷。当法官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官员用他们的正义感填补著作权法的空白时,复制录音制品尽管不违反著作权法,但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它仍然被视为非法行为。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唱片产业多次尝试说服国会修改著作权法,将录音制品纳入保护,但这种努力从未走得很远。20世纪20年代,产业界显然没有非常努力推动这一改革,因为既然已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来阻止复制、获得保护,著作权法的改革也不会带来更多好处。20世纪30年代,当通过许可电台广播获得可观收入的可能性出现时,唱片公司加强了它们争取录音制品著作权保护的力度。然而,到那时,它们遇上了一个强大而坚决的对手——电台产业,后者成功阻止了著作权法的任何扩张。
当20世纪20年代电台开始广播后,声音的财产权问题又被另一项技术变革所改变。电台广播的大部分是录制音乐,但最开始,它们并没有向原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支付费用。此时,著作权人们刚刚组建了“美国作曲家、作者和出版商协会”(ASCAP,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ASCAP极尽全力地向电台发起挑战。就像作曲家和出版商过去曾担心留声机和钢琴卷可能消灭活页乐谱产业那样,此时他们也担心电台将消灭留声机和钢琴卷产业。如果顾客可以免费从电台欣赏到相同的歌曲,他们为什么还要购买碟片呢?协会总干事于1923年抱怨道:“情况非常严峻,收音机被放置在留声机上面,后者从此被尘封。”ASCAP的解决方案是敦促国会通过一项议案,每年向听众征收每台收音机5美元的税金,以作为对使用作曲家和出版商作品的补偿。
这个提议最后无疾而终。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由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发起的针对广播电台的法律诉讼。《著作权法》授予著作权人营利性地表演其音乐作品的专有权利。当电台播放唱片时,这是否构成“表演”?有的法院认为是,有的法院则认为不是,理由在于,“表演”指的仅仅是对物理上在场的观众的表演,而不包括对电台听众的表演。如果确实是“表演”,那当听众可以免费收听时,是否仍是“营利性”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这些不确定性最终被消除,结果对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有利。电台广播是一种营利性的公开表演,因此电台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不得播放录制音乐。
因此,广播电台为了使用音乐出版商的歌曲必须支付费用。《著作权法》已经规定了唱片产业应当支付的许可费费率,但在1909年时仍没有电台,所以对于电台广播没有可比的法定费率。全国广播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NAB)多年来一直游说国会,希望通过法律设定广播许可费费率,但国会一直没有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来自ASCAP的反对。于是,广播费就通过ASCAP和NAB之间反复的、日渐尖锐的谈判来确定,两个准垄断组织被锁定在一个双方都无法避免的关系中。同时,使用录制音乐的成本使电台将广播的时间转向其他节目,例如新闻、体育赛事和广播剧。
当作曲家的录制作品在电台播放时,他们可以获得收益。但是,表演者呢?音乐表演家对声音享有财产权吗?这一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由两位当时最有名的乐队主唱——弗莱德•魏尔灵(Fred Waring)和保罗•怀特曼(Paul Whiteman)——对电台提起的一系列诉讼中被提出。魏尔灵和怀特曼都担忧电台的反复播放会对其唱片销量带来影响。两者还都在电台节目中做现场表演,所以他们有理由担心,如果与之竞争的电台可以播放其唱片,其电台节目的听众将会流失。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魏尔灵出席每档节目的费用是13 5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超过20万美元)时,其他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当然有理由在完全相同的时段播放他的唱片。魏尔灵后来回忆道:“我觉得他们通过播放我们的唱片来和我们的节目竞争,这是不公平的。这对所有表演者都是一个日渐严重的威胁。”因此,根据魏尔灵和怀特曼的唱片合同,他们的唱片上印有“不许可电台广播”的字样。当电台播放其唱片时,两者都提起了诉讼。
在魏尔灵的案件中,宾夕法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法院都禁止电台播放其唱片。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论证道:录制音乐的表演者“毫无疑问参与了产品的创作,他对该产品享有财产权。无论如何,这是一项与作曲家对音乐作品的权利不相重叠、不相重复的权利。” 法院解释道:这一财产权必须通过某种形式加以保护,“否则, 杰出的音乐表演家将不可能为录制留声机唱片而做表演——除非可以获得高得惊人的经济补偿。当音乐表演家为录制留声机唱片做表演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唱片被用于广播的不利和损失”。魏尔灵因此有权决定将其表演用于何种用途。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案件中,法官同意魏尔灵“对其表演享有财产权”。
然而,在怀特曼的案件中,一个更知名法院的另一位更有影响力的法官做出了相反判决。在为坐落于纽约的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撰写的判决书中,勒尼德•汉德法官判决道,不管音乐家在录制表演上可能享有何种财产权利,这一权利在唱片被销售的那一刻就终止了。汉德在给他的同事的备忘录中写道:“说一个人可以对其大脑的任何产品享有‘财产权’,这是荒谬的。法律中从未有这样的或相似的规定。”如果怀特曼可以获得对录制表演的财产权,为什么他的唱片公司RCA不能?“对于录制怀特曼的表演而言,该公司的技术和经验也是同等重要的。”法院应如何衡量两者的相对贡献?汉德总结道:“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胡扯。我认为他们是一群自私贪婪的小人,如果您明白我的意思的话。”而他的法官同事非常理解他的意思。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解释道:“我从不怀疑托斯卡尼尼(Toscanini)们,甚至怀特曼们的才华,但是,为了他们所创造的美好事物,这个世界已经给他们的个性以充分的回报。”
现在,怀特曼还想要更多的东西。克拉克论证道:“保证艺术家过上舒适的生活是一回事,把他和他的开发者变成财阀则是另一回事……法院没有理由发明一项新的财产权。”审判庭的第三位法官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的语气更加强烈。他宣称:“我认为乐队主唱的这些诉讼请求是毫无道理的,艾尔•史密斯(Al Smith)艾尔•史密斯(Al Smith)系美国政治家,曾四次当选纽约州州长,并于1928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此次竞选过程中他使用了一款印有“Al Smith for the President”(“竞选总统的艾尔•史密斯”)标志的褐色圆顶礼帽。——译者注也可以主张自己有佩戴褐色圆顶礼帽(brown derby)的权利,因为佩戴褐色圆顶礼帽是他的财产权。”
几年内,弗莱德•魏尔灵的胜利已无迹可寻。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唱片产业说服了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州的立法机关立法明确规定,当一张唱片被销售时,其上的所有财产权利都归于购买者。如此,只剩下宾夕法尼亚州有限制电台播放录制音乐的规则,而即使在该州,也没有人尝试建立向电台广播收取许可费的收费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电台除了向代表作曲家(而不代表音乐表演家)的ASCAP付费外,都免费地播放着唱片。
乐队主唱对广播产业诉讼的失败,激发了人们对录音制品著作权的更多诉求,并使表演者和唱片业为实现此目标做出加倍的游说努力。一位律师回忆道:“碟片制作曾经是非常好的产业,但随着电台的出现,这一繁荣终止了。”声音著作权的支持者们强调,允许电台让公众免费欣赏唱片,将使一首歌在唱片生产者能够销售它之前就丧失了新意,这是不公平的。他们指出,许多其他国家的法律——包括大不列颠和加拿大的法律——都已经为录音制品提供著作权保护。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之间,这一问题反复在国会中被提及,但广播电台成功击退了所有改革的努力。
表演者和唱片生产者本可以从声音著作权中获益,但由于双方无法就著作权到底归属于谁达成共识,其游说努力因而大打折扣。音乐表演家[在国会中通常由美国音乐家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Musicians)代表]主张著作权应当属于他们。他们毕竟是音乐的创造者;如果著作权法的目的在于奖励艺术创造,那么录音制品的著作权应当属于表演者。但这一提议带来了一些明显的管理难题。如果一个乐团录制一首歌曲,是否每一位乐团成员都对著作权享有一定的份额?在唱片被复制或电台播放唱片前,是否需要得到所有团员的一致同意?如果将著作权授予乐团指挥而不是整个乐团,那么,对更小的、组织层级较少的乐团有无其他著作权归属原则?将录音制品的著作权授予音乐表演家将带来一系列法律问题,危殆整个产业。
将著作权授予生产录音制品的公司在直觉上缺乏感召力。录音的技术流程确实涉及一些技艺,但大多数人似乎相信,这种技艺不如歌唱或演奏乐器所需要的技艺那么多。但是,将声音的所有权集中在一个单一的主体上,能够解决试图在音乐表演家之间分配所有权时所带来的所有管理难题。将著作权授予唱片公司是英国、加拿大和所有其他迈出这一步的国家所采取的解决方案。这也是美国自己在授予电影作品著作权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案——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制作电影的公司,而不是在所有演员和其他参与制作的创作人员之间分配。即使音乐表演家们自己不享有著作权,他们也可以与唱片公司就许可费问题事先进行协商。表演者们最终就这一问题做出让步,但许多年来,这一问题使他们无法在国会与广播电台的持续斗争中,和唱片公司形成统一战线。
无论如何,授予录音制品著作权的收益很快将被进一步的技术变革放大。多年以来,唱片业的主要对手是电台。反不正当竞争法使翻录唱片的老问题在经济上变得不太重要。但1948年慢转密纹唱片(long-playing record)的出现使翻录唱片变得更加有利可图。过去,唱片的一面只能录入3到5分钟;现在,两面加在一起总共可以播放45分钟的音乐。消费者愿为新的慢转密纹唱片(“LPs”)支付更多,但唱片复制的成本并未因此成比例地增长。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早期,主要的唱片公司都为翻录问题所累。他们极尽全力反击。他们组建一个贸易协会——美国唱片业协会(the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并为制定一部明确禁止翻录唱片的立法而游说。这一努力仅仅在洛杉矶取得了成功,该市制定了一个条例,规定未经复制权人书面许可而复制留声机唱片是非法的。纽约立法机关两次通过了能达到类似效果的议案,但两次议案都被州长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以该问题由联邦立法规定更合适为由加以否决。由于在立法机关中的努力未能取得成功,唱片公司针对翻录者提起了一系列不正当竞争诉讼。大多数案件都取得胜诉,但对于唱片产业而言,这并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将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翻录者,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州普通法,它在不同的州,甚至在不同的法官那里都是各不相同的。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将联邦著作权法扩大到为录音制品提供保护。
当录音磁带进入美国市场后,翻录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变得更加严重。复制唱片变得更加容易、更加廉价,因为复制者不再需要压制唱片的设备,一台录音机足矣。一位律师在1966年时说道:“未经许可的复制者很快就进入生产汽车和家用录音磁带的行业。复制者甚至可能为磁带翻录提供大规模的唱片库,在广告中声称他能提供所有最新的热门歌曲。”唱片公司再次发起反击,不过这次他们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们发起了另一波诉讼,还说服10个州的立法机关立法禁止翻录唱片,其中包括4个人口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亚、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德克萨斯。最终,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他们说服国会在1972年生效的法律中,将著作权延及录音制品。复制声音终于成为违反著作权法的行为。
唱片的生产者享有声音的所有权——真是这样的吗?对于翻录者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他们赢得了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广播电台仍是强劲的对手。广播电台没有任何理由支持翻录行为,但他们有强大的利益避免在广播歌曲时必须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结果,唱片业确实赢得了著作权,但著作权法明文规定,录音制品的著作权不包括公开表演权。电台可以继续免费播放音乐。为了使用音乐作品,电台必须向作曲家支付著作权费,但表演者和唱片公司无法从电台处获得收益。由于“公开表演”包括播放歌曲唱片、演奏厅表演和广播,因此当歌曲被他人录制或者被他人向观众表演时,表演者和唱片公司一无所获,而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则有权获得许可费。
毫不奇怪,作曲家们对这样的一套激励规则做出了反应。过去,作曲家和表演者大体上是两个不同的人群。一直到1950年,只有7%的最流行歌曲是由其表演者自己撰写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唱片销售收入越来越成为音乐家收入的绝大部分,创作型表演者的百分比相应地增加,因为音乐表演家们意识到,比起单纯的歌唱,写歌可以获得更多的许可费收入。1960年最流行的歌曲中,唱作型歌手的作品占22%;1970年这个数字是50%;1980年是60%;1990年是64%;2000年是68%;2004年是88%。流行音乐的性质由此发生变化。当音乐表演家表演的是自己的音乐作品时,流行音乐更可能被理解为个人表达的工具,而不仅仅是(或者同时也是)商业产品。
到20世纪末期,声音的财产权在一群参与者之间——作曲家、音乐出版商、表演者、唱片公司与广播电台——以复杂的方式分配。这种财产权的分配不是任何理性设计的结果。它是一个世纪以来,在立法机关和法院里,关于谁应获得技术变革收益的权力斗争的产物。
(文章节选自田雷主编雅理译丛·斯图尔特·班纳《财产故事》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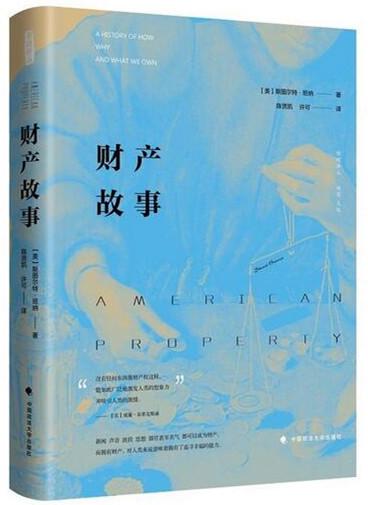
斯图尔特·班纳著,陈贤凯等译:《财产故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