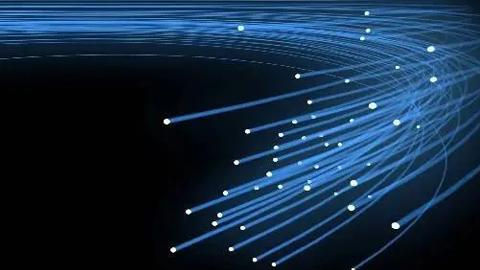日暮归家,倦极。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只见一英俊小生,面色苍白,左手扶墙,右手捶腰,做弱不禁风状。一妙龄少妇,含情脉脉的用双手环扣男子之腰,用脸颊贴其后背,一副小鸟依人模样。这时,画外音幽幽响起,“汇仁肾宝,他好,我也好。”
大乐,汇仁肾宝这句经典台词,至少响彻神州大地二十余年,堪与之相比的看来也只有脑白金了。我以为,这句台词道出了,几千年来潜藏在中国男人骨子里深深的焦虑。
直白点,中国男人是怕女人的,尤其是在床笫之上。颠鸾倒凤之后,绝大多数男人都怕自己的女人一脸惊诧的问,“这就完了“,然后换做不屑的语气道,你也不行啊”。哪个男人不幸听到这句话,上吊的心都有了。
手头里恰好有两本书,一本是潘绥铭的《性的社会史》,一本是王溢嘉的《中国文化里的情与色》,前者学术,后者通俗,这一深一浅的两本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男性的权力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自己脐下三寸的“那话儿”。
那话行,男人就无限自信,乃至于狂妄,那话不行,男人就萎靡不振,畏畏缩缩。如此说来,男人的焦虑还是“性”的焦虑。

男人对某方面的能力信心十足,先是征服了女人,然后建立家庭,最后打下一个大大的帝国。用儒家的话套用,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性的社会史》中说,性有三种存在:“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
理论上说就是男人生物上的性的能力强了,心理上也有自信了,最后表现在社会上就是攻城略地,无往而不胜。男人的权力欲是建立在某方面能力的基础上的。
可是在《中国文化里的情与色》中说:
“我们不得不说,男性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是社会学上的强者,但却是生物学上的弱者,准确的说,是生殖学上的弱者。”
实话实说,在某方面的能力方面男性是不如女性的。这已经在医学上得到了证明。男人在很早以前对此久心知肚明,在《素女经》中说:“女子胜男,犹如水之胜火。”在阴阳五行的观念中,女子属水,男子属火,水是克火的。男人的能力低于女性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男人就用了两种焦虑,一种是对自己某方面能力的焦虑,一种是对女性能力的焦虑。前者是根本,后者是前者的延伸。怎么办呢,在《中国文化里的情与色》(简称情色)中说给出三种解决之道,
“一是药物法,一是器物法,一是功夫法。”
药物显而易见,《金瓶梅》中的胡僧药,如今的伟哥,汇仁肾宝大概也算吧。
器物也是一望便知,不需多说。
前两者确实有效,但用多伤身。特别是中国人信奉是药三分毒,弄不好,就一命呜呼,比如西门庆。功夫虽好,但也需要假以时日,而且一不小心就容易走火入魔。
因此,很多男人觉得既然解决不了自己,那就解决女人吧。他们借助自己在社会的优势地位,制定种种规则来约束女性,进而希望通过这种约束来束缚女性的能力,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就比如“三从四德”、“女德箴言”,前一阵子被千夫所指的“女德班”,就是明证。这算是文的,如果压制不住,就开始污名化,妖魔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淫妇妖娃,也只不过某些女性不想被社会压制,被道德规训而已,她们只是想保持自己的原始活力而已。
面对这些“淫妇”,男人当然希望先进行收编,比如《金瓶梅》中的李瓶儿,她从荡妇成为了贤妻良母。而反过来,如果收编不了,压制不住,要么就如同潘金莲,被武松一刀结果性命,杀掉了事。要么,就如同《水浒传》中的孙二娘、顾大嫂,被改造成男人,让她们成为自己的兄弟,众兄弟其乐融融,这天下还是男人的。
追根溯源,男人的不自信和巨大的焦虑,还是对自己某方面能力的不自信。正如《情色》中所说的,
“在人类权力社会里,某器官虽然是男人欢乐、权力与好运的根源,却也是他们痛苦,焦虑与噩梦的渊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