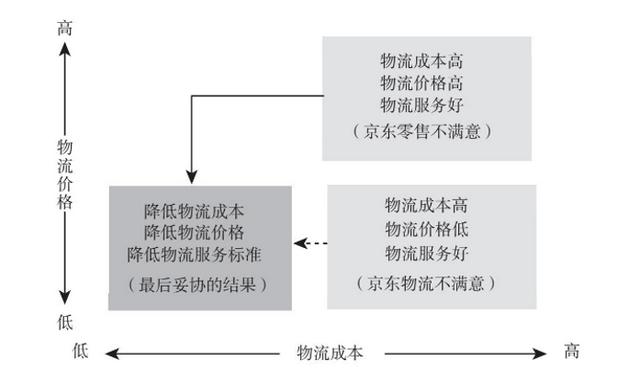李霄峰

看《风平浪静》是跑着去的。6日晚出差回来,三里屯美嘉,晚上近十点的一场。
看完好些人不走,一直听完片尾曲。我走路回家,看着月亮,又泪又笑。2003年11月去青海冷湖探班《可可西里》,认识了在组里拍纪录片的李霄峰,还有摄影指导曹郁。2020年,曹郁当摄影指导拍了《八佰》;李霄峰拿出了《灰烬重生》和《风平浪静》,他是导演。时光啊,岁月啊,我们啊……
“霄峰成了。”发朋友圈就说了这一句。7日下午在苹果社区访谈,很讨嫌地我问:“你第一部《少女哪吒》,我是努力去喜欢;第二部《灰烬重生》疫情期间在网上看的,看得不知所谓;到了《风平浪静》,感觉一下子顺了,都对了,是因为有黄渤(监制)吗?”
我跟一杯外卖“星巴克”一同到达。霄峰家有点儿凌乱,猫爬架、酒、男用香水,看不见的书房里有钢琴。墙上挂着三部导演作品的海报,还有路边捡来的硕大一个路牌。到处是书,沙发上是《蛤蟆的油》。猫很乖、聪明灵动,叫“姐姐”。
李霄峰1978年生人,写过一个被毙掉的剧本叫《无法无天》。第一个成功投拍并于2009年上映的剧本叫《达达》,片中男主,一个失手惹下祸事、不得不远遁他乡的少年,出演者是霄峰本人。2015年他的导演处女作《少女哪吒》,里面“剔骨还父”那种决绝,我在《风平浪静》中又看到了。《灰烬重生》里有罪案,《风平浪静》中也有。
天晴风大,窗外叶黄叶落。霄峰依然说着说着就按捺不住站起来走动,手的动作大且丰富。我喝着茶,对他的好奇十数年如一日:“那种对底层生活的敏锐感知,还有强烈的道德感,是打哪儿来的?”
我们希望一个父亲是什么样的?
北青报:电影最后,我很惊讶你会让宋浩把父亲也捅了。我之前以为他会就是自尽,用哪吒那种方式。
李霄峰:我比较自豪的恰恰是,它比哪吒多走了半步。原来宋浩的台词是:“我还!你也还!”
北青报:现在是到“我还”为止。
李霄峰:对。
我小时候看的《哪吒闹海》里,哪吒是自尽以谢天下。面对托塔李天王那样的一个恶劣、虚伪和懦弱的父亲,他是用自刎来“把骨肉还给你”,那么一种方式。但是这个电影它多走了半步。我们古代讲“君臣父子”嘛,这种权力关系是同构的。过去是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其实父亲对于儿子来说,同样,除了爱以外。爱是有权力的,尤其是亲情里面的爱,它是占有的、有支配权的,尤其对孩子来说。
北青报:这种弑父的情结怎么会有这么强烈?
李霄峰:其实我觉得倒不是弑父的情结重。中国还是一个父权社会,而且我觉得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我在《灰烬重生》里面放了一幅画,罗中立的《父亲》,那是一个很经典的中国父亲。我们其实在父亲这个层面是有希冀的。我们希望一个父亲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一个事。
你看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边,有“国民岳父”、有“国民女婿”、有“国民闺女”,还有“马云爸爸”。这个很奇怪,对吧?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向往的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很复杂,难以一言蔽之。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在的,我自己这么认为。
所以《风平浪静》中宋建飞这个父亲,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的另一面。过去说“虎毒不食子”,这个电影里面实际上是一个“虎毒要食子”“不得不食子”的父亲。在创作面上这个父亲其实比儿子更重要。
他毫无疑问有情感的一面,自己的亲儿子谁不动感情呢,是吧?但是感情里面又有利益的成分——“我儿子保送名额刚刚没有,现在又伤了人。如果叫救护车、报警,我儿子就完了,我维护了十几年的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一切都完了”。
这个还跟人物性格有关。这个父亲,我们总结为“杀伐决断”。我觉得跟中国这40年里头30多年的那种高速发展,也是有紧密的联系。高速发展中谁不像草莽?为什么选王砚辉来演?因为他身上带着天然的那种草莽气。从这个人物的性格来讲,他是完全可以把这件事立刻执行。“行,你要报警是吧?”赶紧补一刀。
北青报:还有他看见儿子从家里出走他没拦,这个是我不太理解的。他让孩子就这么不知前路地走?
李霄峰:走吧,你留下来,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会查到你头上,对吗?我现在刚刚升职,保住我这个官职,我还有机会保你宋浩一条命、保我宋家的血脉。我干吗要拦?是吧?
这个人物身上,他既有人之常情,又有超出人之常情的部分。他其实还有一部分是一个戏剧人物。我觉得这么理解可能相对会通畅一些。
为什么每个人见面都叫老师呢?
北青报:《风平浪静》比你之前的两个片子,我要喜欢很多。
李霄峰:之前的片子作者性太强。
北青报:这个片子,能感觉到掌控它的这双手,是有力量的,能够收放自如了。之前曾经认为你是因为文艺气息,和“文青们”对于文艺片的有些“迷信”,以及当年你在网上写影评、写专栏时那些小伙伴,他们在你做电影后对你的爱和支持,认为你靠的是这些。看完《风平浪静》我觉得你是靠自己,扎实了,已经可以了。这个成长是因为有黄渤吗?
李霄峰:也不完全是。我也42岁了,你知道年轮啊,我多多少少还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
还有一点,本来不想说这个话,但我觉得也到这个份上了,还不如说呢。我觉得我们对导演的那种迷信啊,张艺谋拍完《英雄》其实说过这个话——“电影不是一个人拍成的。”
我觉得咱们这边对电影的理解,有时候过于把导演的身心和电影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倾向。另外一个倾向,干脆导演就不在了。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认知。电影是一个工业,如果没有大家伙在这劳动,摄影、美术、导演组、录音、配乐,哪来的电影啊?从根本上来讲,导演实际上是成了商业市场的一个标签,是市场准入的一个入口,这个入口比较方便。
今天我在这个体量的电影上所能达到的成绩,当然很开心,很高兴。作为导演,我也更放松了,比我头两个电影,身心上非常放松。我也不太较劲了,实际上反而是放松、没有什么压力的时候,人能把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是我们这帮人,没有谁是一蹴而就的。摄影指导朴松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之后头5年,他都在拍纪录片。他是一个非常扎实的摄影指导。章宇1982年生人,也不小了,今年38岁了。制片人顿河,1982年的,也是在姜文那儿工作了很长时间,出来以后自己做制片人,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
那这样一帮人聚到一起,气场完全是合的。不需要用导演和演员的身份来沟通,而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就比较靠谱了。我去过美国的片场,现场Jack、Mike,都是直呼其名,没有人叫导演。
我们的行业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有的时候把人的身份看得更重要,而把人看得更轻。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每个人见面都叫老师呢?
北青报:那你们这帮人是怎么凑到一起的?编剧我看是余欣。
李霄峰:他1991年的,非常优秀的一个小孩,现在是张献民老师的研究生。高二就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冠军。高三的时候他闲着没事,“我再参加一届吧”,又拿了冠军。被保送上厦门大学中文系。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是顿河和余欣他们想开发一个少年犯罪的项目。
北青报:这一直也是你喜欢的。
李霄峰:对。正好我那时候拍完《灰烬重生》,其实挺累的。在一个探讨人性的电影里面,如果你过于地投入,过于地较劲,实际上到最后自己的身心会有损伤。我拍头两个电影时,可能不像今天这么职业。今天算是职业了,我能够跟我的作品之间拉开距离。
顿河看完《灰烬重生》觉得挺喜欢,我说那我们就再去聊聊天,看看有什么可做的,然后他聊到这个项目。
今天能不能用严肃的方式
来靠近纯真?
北青报:听说他饭桌上一句“成年人只讲利弊,小孩子才讲对错”,让你大光其火。
李霄峰:这些年来,我们经历过很多,我到今天还认为是错误的说法,比如说“消费者就是上帝”,所以有段时间我们的消费者就像螃蟹一样,任何时刻都可以颐指气使,都可以横着走的。还有一个比如说“认真你就输了”,认真跟输赢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认真地生活,认真地去思考,这有什么问题呢?还有一段时间就号召大家要宽容,要有格局。我特别讨厌“格局”这个词。格局不是说不讲善恶,不讲对错的。“格局”应该是知道什么是善恶对错的情况下,有一个开阔的心胸,而且你要经过这个东西,你才可以去讲。如果说一个人20多岁就很有格局,我是感到怀疑的。我会觉得可能是成功学的一种。
实际上我们今天,有一个我还挺喜欢的词叫“修复”。我们是需要修复的。不是说你受了伤你需要修复,而是你的价值观、道德观。当然,道德可以用来自律,不太好用来要求别人。但道德到底是什么?爱情有没有道德?我就觉得有很多问题是需要重新探讨的。那为什么小孩子才讲对错呢?
小时候,成年人给你的教育是“你不要撒谎”,但是稍微长大一点,我们为什么要设置“三天朋友圈可见”呢?我们到底在隐藏什么?真、善、美,如果我们还向往过这种东西,这现在还在吗?
北青报:他们可能认为那是策略吧。
李霄峰:实际上大部分时候,就连保持谦卑都成了一种生存策略了,它不是一个从内而外的过程。那我们还在追求什么?我们追求的难道不应该是从内而外的一个过程吗?我们难道不追求人格上的完整吗?对吧?小时候还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像我们现在不追求这个了。
北青报:可能他们是觉得教小孩要教原则,然后成人了要讲策略。
李霄峰:为什么一个人有钱,你就可以叫他“国民爸爸”呢?难道人格上的平等不是我们追求的吗?我们难道是追求“我要踩在别人脑袋上”吗?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他的理想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这个才是《共产党宣言》的最高的理想。
别说我们,俄罗斯,在托尔斯泰的时代,也是一样的。他能够看到当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精神出了很多问题,人们已经不再古典了,不再追求一种更崇高的人格。
张一白推荐我看过一篇小说,《当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叫礼平。那里面就有对上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探讨。其实说白了,王朔实际上是用一种毁灭的方式来靠近纯真。我们今天还要用这种方式吗?我们能不能用严肃的方式、浪漫的方式来靠近纯真?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电影很根本的,想要试图去追索的那么一个路径。
你经历了什么
拍出这么个电影?
李霄峰:过去太宰治说“能扮演小丑的人都是严肃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很多小丑,但是看不到严肃。美国人拍《小丑》,你还能够看到严肃的东西,是吧?我们过去的鲁迅,他是用严肃的方式在探讨严肃。当然他很讽刺,也很尖锐。我们今天能不能不再“挂羊头卖狗肉”?
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包括我们的电影营销,都是在“挂羊头卖狗肉”。里面有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但他要用别的方式吸引大家进来看一个以为是娱乐的电影。但其实不是啊,它里面是严肃的。
我这次其实还挺感谢顿河他们,还算用一个严肃的方式在推广电影。这个是我们在追求的。
北青报:不容易。看那些公号的推送,比如说跟韩国犯罪片联系,还有评价章宇的表演是“性感”。我觉得这已经很努力了。
李霄峰:说回这个电影,有很多对情节的探讨、对剧情的质疑,这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包括他们说演员的表演好,或者这个好那个好,也都不重要。这个电影是新的,它做了一些拓展,这个拓展它已经留下来了。我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看电影的方法,可能在文化上,其实需要更加尊重自己了。不能老是去尊重别人,尊重美国人,尊重欧洲人,尊重日本人,尊重韩国人,人家当然值得尊重。但是在内里,我们到底是在讲谁的故事?我们尝试着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故事的时候,需要一些对自己的尊重。
北青报:我现在能够体会到顿河说的那个,你“在自毁底下有特别纯粹的东西”。好多人其实觉得到成人了,就“不必了”,可以放弃对这个的紧抓不放。
还有一点,我很高兴你没有把这片子只是拍成一个爽片。这种爽片现在也是一种套路,都要像冯小刚拖着大军刀冲过昆明湖冰面。最后这个结局我个人感觉更高级,一个底层小人物被欺负、碾压到无力承受。
其实我最想问的,还是章宇问过你的那个问题——“你经历了什么拍出这么个电影?”
李霄峰:有很多我非常看不惯的事。我这些年脾气好多了,我也不想跟自己置气。
说白了,我觉得我还算与时俱进的,真的。但是我就觉得很多事都不对,文学作品也不太对,电影也不太对,都不对。
北青报:那怎么样是对的?
李霄峰:你有你尊敬的东西,如果你尊敬的东西你自己不维护……我也不是不随波逐流,我也爱世俗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电影、文学作品,在鼓励什么,在呼吁什么,这个挺重要的。
托尔斯泰难道不是最好的例子吗?你永远知道他心里有一个东西是超越他自己的,他永远如夸父追日一样,他永远达不到,但是他永远在追逐那个东西。他不面对自己的伪善吗?他面对啊,他知道自己是伪善的。他很有钱,我参观过他莫斯科的庄园,过的那个日子,大餐桌底下铺着熊皮,他自己打来的。他很努力地想做一个劳动者,他还自己用皮做靴子送给自己的女婿。70岁去学骑自行车,拽着契诃夫去河里捞鱼。他知道自己是为啥,他也做过努力。他年轻的时候尝试着把自己家的土地分给农民,后来发现越分越不对。就是在这种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他还在追求他认为对的东西。他这是一个精神性的状态。
顿河说我有自毁倾向。我不是自毁的人,我其实过得还挺舒服的。说白了,导演费拿着,各种事儿做着,对吧?但我自省是有的。只不过有的人的自省,他不放到作品里。我可能是把自省放到作品里面去了。谁不犯错?但你犯的这个错会跟别的错误联系在一起,它本质上都是罪过,本质上都是你需要去反省的东西。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摄影/陈琢
,